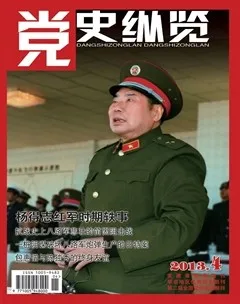浴血长征路的“御林军”:红军干部团(下)




飞渡金沙江
金沙江由青藏高原飞流直下,穿越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奔腾千里注入岷江,成为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天险。
29日当天,中央红军兵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北并进,分头抢占金沙江之龙街渡、皎平渡和洪门渡。
由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纵队,负责夺取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最北端的皎平渡。占领皎平渡比占领龙街渡和洪门渡的意义更重大,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能否渡江脱险。
自打撤离中央苏区以来,红五军团始终为全军殿后,损失甚重。此时虽然番号没变,实际上只有3个团的兵力,正与尾追而至的敌10个团激战,掩护主力渡江。因而,中纵队抢占皎平渡,能用上的部队也只有干部团了。
由于此战事关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中革军委非常重视。5月1日上午,周恩来亲自从翠华乡界牌村赶到干部团驻地,当面向陈赓和宋任穷交代任务,说:你们务必于4号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或找到渡船;军委派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担任渡江先遣司令,带军委工兵连和一部电台随干部团先遣营行动。
接着,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又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干部团,亲自做战前动员。他指出:渡过金沙江对实现党中央北进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他鼓励干部团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争取时间,迅速抢占渡口,以保障全军安全过江,胜利北上。
5月2日清晨,干部团整装出发。刘伯承和宋任穷率三营先行,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直指皎平渡。
当天,干部团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在野草丛生、乱石嶙峋的山间走了60多公里。晚上,部队就在一片小树林里露营,睡到半夜爬起来,又以急行军的速度接着走。
本来,干部团各营营长、政委以上干部都配有马匹。然而,这一路上,十几匹马都用来驮伤病员了,连刘伯承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进。每个人都在和闷热、饥渴、疲惫做搏斗,生理承受力都绷到了极限,队伍里一片呼哧呼哧的急促喘气声。
在一营的行进队伍里,一个走在丁秋生身后的战士拖着哭腔说:“政委,我胸闷得像要炸裂了。”
丁秋生说:“我也胸闷。”
那战士说:“我要走死了。”
丁秋生严肃地告诉他:“你不一定会走死。但如果你不往前走,敌人肯定会追上来把你打死。”说罢,他转身拽下了那战士身上的米袋,背在自己的背上。
背上多了这么个两三斤重的米袋,丁秋生顿时感到额头虚汗流得更欢了,穿过眉宇直往眼里淌。他觉得脑袋一阵阵晕眩,但两条腿仍在机械地快速运动着。忽然,他一脚踏空,掉进一个长满剑茅的沟裂里,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天已经黑了。
也就在这时,前面传来通报:还有30公里就到江边了。
丁秋生精神为之一振,扭脸朝身后的一营队伍用力喊了一嗓子:“快到了,同志们再加把油啊!”
果然,摸黑又走了将近一小时后,他听见远处传来江峡中那闷雷般的涛声,还隐隐看见星空下那一弯如带的银灰色江水。
这时前面传来命令:就地做饭休息。
此刻,先遣营前卫连在皎平渡江边找到两条小船,随后偷渡过江,消灭了对岸厘金局里的几十个民团团丁,又击溃刚刚开来扼守渡口的一营敌军,未伤一兵一卒,夺取并控制住两岸渡口。
靠这两条木船,先遣营不顾疲劳分批抢渡,连夜登陆金沙江北岸;然后沿江向两侧派出警戒部队,继续搜寻船只。
至此,这支中央红军精锐团队,创造了两天连续急行军140公里无一人掉队的奇迹,比军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完成抢占金沙江南北渡口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陈赓接到刘伯承转来的军委电报,令干部团主力即刻出发渡江,占领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
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时,先遣营已搜罗到6条船,刘伯承亲自指挥分批渡江。
等候渡江时,宋任穷告诉走在身边的丁秋生:“昨天刘总参谋长很兴奋地对我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160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呐?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你说说,我们靠的是什么?’我说,主要靠同志们高度的政治觉悟,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靠人民群众帮助。你说是吧?”
丁秋生连连点头:“政委你说得很对,没有这些根本办不到。”
后来丁秋生才知道,他们干部团日行80公里,只是平了红四团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后奔袭道州和红五团从遵义老鸦山追敌至乌江大渡口的记录。
仅仅20多天之后,这三个奇迹般的日行军速度,又被红四团在泸定桥头给打破了。
中午时分,干部团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过江后,干部团一刻不敢耽搁,留下三营警戒渡口,主力立即沿着盘旋陡峭的山道向通安州攀援疾进。
激战通安州
所谓通安州,其实就是金沙江西岸25公里处的一个镇子、川南边界上的小商埠。小镇位于山顶,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据此可直接控制皎平渡口。
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第二十四军第一旅旅长兼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瑭。此人自作聪明,认为红军主力不会从皎平渡过江,走通安至会理的正道,而可能由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还可能以一部兵力由姜驿方向直攻会理。因此,他将该旅第二十八团摆在会理东路,第三十团摆在会理西路。只派了第二十九团刘北海营前往通安,协助当地的江防大队防守金沙江。他自己则带第二十九团(缺一营)和师直特务连、工兵连作为预备队驻扎会理城内。
5月4日这天早晨,干部团前卫五连一马当先,直奔通安。在离通安不远的山隘口处,与敌江防大队遭遇。
敌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后来回忆道:“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刘北海营和红军对抗,伤亡过半,退到通安后方据险抵抗。刘元瑭闻讯,即率会理所有部队向通安驰援。”
当五连乘胜穷打猛追,将敌刘北海营撵到通安镇北的一把伞附近时,刘元瑭带着第二十九团两个营和特务连、工兵连火速增援上来,又把五连挤出通安镇。
五连撤到镇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不久,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调整兵力,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丁秋生带一营虽然一度攻到镇中心的小街上,却又被敌人打退回来。打到将近黄昏,敌我双方仍僵持不下。
陈赓见敌阵前地域开阔,火力凶猛,不便正面进攻,决定改变打法。
这时,宋任穷带三营气喘吁吁地赶到,他焦急地向陈赓通报情况说:我们又搞到一条船,现在共有7条船了。大船一次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一昼夜能渡万把人。但是原定分别从龙街渡和洪门渡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在当地没找到民船,那一带水深江阔也无法架桥。因此,军委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全部赶到皎平渡过江。一小时前中央机关已经赶到,正在渡江。如果拿不下通安州,敌人反扑,中央危险。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干部团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
陈赓当即调整部署,命二营正面强攻,一营、三营向右翼迂回,由侧面包抄攻击。
刘元瑭所部虽只有1个团,但该团3个营加直属队,共2000余众。而原本1000多人的干部团,几仗打下来,只剩下不到800多人,明显处于劣势。
然而,这群个个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红军精锐,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对三,毫无畏惧。为给身后数万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干部团主力再次投入决定性一战。
随着冲锋号声响起,通安州这座沉静了数百年的川边小镇,被一波猛烈的枪炮声、喊杀声撼动。干部团多路突击,骁勇善战,远的枪打,近了刀捅,不远不近就掼手榴弹。
暮色渐浓的通安小镇上,到处弹飞血溅,尸首横陈。
夜幕降临时,通安之战终于见了分晓。
张伯言回忆说:“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溃败下来,残部逃回会理的大约只剩400人。其时刘元瑭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跟追前来,跑不了,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以后更不好办,不如收拾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出城逃走10余里的老婆追回来……”
但干部团并没有跟踪追击刘元瑭,而是就地宿营。
在通安州一营的驻地内,一整天都在渡江、行军、作战的丁秋生觉得乏极了,天一黑就想睡。可倒在地铺上,他又睡不着,肚子饿得咕噜噜叫。他这才想起除了早上吃了一茶缸米饭外,到现在还粒米没进呢。他刚爬起来想找口吃的,就看见三连司务长韩先端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跑来,说:“政委,尝尝我们连的炖菜。”
丁秋生一看,那碗里既有肉块,也有鸡腿,还有绿油油的青菜,香味四溢。他惊喜不迭地问:“哪里来的?”
韩先得意地说道:“咱们缴获的战利品。”
丁秋生更纳闷了:“战利品?我打了这么多仗,缴过机枪也缴过小炮,还从没缴获过猪肉、鸡肉呢。韩先,不是犯了群众纪律吧?”
韩先笑道:“哪能啊,政委。群众的针头线脑咱们都不动,还敢拿大油大肉吗?镇上的老乡说这大半拉猪、十几只鸡都是敌人准备好的,逃跑时来不及带都扔下了,是咱连欧阳平和谢继友教员发现的。我让炊事班把它们放在一起,炖成一大锅。”
丁秋生放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边吃边感慨:“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餐了。”
通安之战和皎平渡之战,相互辉映,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尾追,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革军委对此战非常满意,当晚即向全军通令嘉奖干部团。
第二天,干部团在通安镇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然后昼夜警戒,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
从5月4日开始,除红三军团彭雪枫第十三团从洪门渡、红一军团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中央红军主力3万多人,全靠干部团夺取的7条木船,连续6天6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一人一马。
从此,干部团在红军中声名越发显赫,被称之为“御林军”。川滇边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戴铁帽子”的红军厉害,说子弹蝗虫一样飞都打不倒他们。川军更是闻风丧胆,看到戴钢盔的干部团便落荒而逃。
毛泽东在一次给部队讲话时,说到干部团的钢盔,幽默地笑道:“以后若遇到四川军队,每个人都把煮饭的黑脸盆顶在头上,去吓他们!”
险过大渡河
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由通安进至会理,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走西昌,过泸沽,占冕宁,穿越大凉山彝族区,连续12天急行军,赶往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
离安顺场还有40多公里时,前面传来的消息让干部团官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军委工兵连无法在水深流急的大渡河上架桥,先遣红一团在安顺场击溃守敌,但只找到一条木船。
5月26日中午,干部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担负离安顺场不远的大渡河西岸几个战术要点的警戒任务。
大渡河的水流比乌江更湍急,山势比金沙江更险恶。两岸百里悬崖,万丈峭壁;河中礁石密布,雪浪飞溅;湍急的河水漩涡翻腾,咆哮奔流。
这时,一个更凶险的消息传来:红一团二连17勇士强渡大渡河后,虽又找到3条修理后勉强可用的破船,但一天只能渡一个团,要把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河去,至少得20天。而敌薛岳追兵已渡过金沙江进至德昌,一周之内即可赶到大渡河,情势万分紧急。
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河,然后由东岸沿河北上;林彪率领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由西岸沿河北上;两纵队夹河而进,合力夺取160公里外的泸定桥。
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拿不下泸定桥,两路纵队被大渡河隔断不能会合,就由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创造个局面。他断言:干部团有干部,在有群众的地方就能搞出块革命根据地来。
黄开湘、杨成武率左纵队前卫红四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数万红军命运,狂飙疾进,一天走了40公里,途中还歼敌一个营。第二天,红四团再次挑战人类生理极限,以一天12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泸定桥头,攀援13根铁索,冲破对岸敌人的弹雨和火网,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一条生路。
5月27日,当英勇的红四团西岸飞兵,用双脚创造人类奇迹的时候,干部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接替红一师在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警戒任务,掩护红一师部队渡河。
当天临近傍晚时,情报侦知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率其第七团和第二十八团两个营,沿大渡河向安顺场东岸的安靖坝扑来。陈赓命三营留下扼守安顺场渡口,李荣、丁秋生率一营先行渡河增援东岸。
李荣率一连先渡,丁秋生断后,乘全营最后一条船过河。
因大渡河水流速高达每秒4米,船工不得不先将船往上游拉到一座碾房跟前,再从那里顺流斜渡,才能开到对岸渡口。空船回渡亦如此,先往上游拉出近2000米,再放船斜向河西渡口。因而,河面虽宽不过300米,一个往返却需花上个把钟头时间。
丁秋生坐上船还没离岸,就明显感觉到大渡河的浪比金沙江的大。他不敢有丝毫大意,身子靠紧船帮,一离岸衣裳就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了。在河谷间隆隆的轰鸣声里,他随着木船在惊涛骇浪和礁石丛中穿行,颠簸着,摇晃着,忽而被抛上波峰,忽而被扔下浪谷。满船见惯生死血腥场面的红军官兵,在大自然如此的张狂和蛮力面前,无不惊得一身冷汗。浪溅汗浸,不一会儿丁秋生身上的衣裳就湿透了。
船到河心,浪头更猛,哗哗地打进船舱,两个浪过后就是半舱积水。丁秋生和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挥动葫芦瓢,不停地往外舀水。当两脚踏上东岸的土地时,丁秋生听见许多战士都唏嘘不已,说:再也不想过第二回了。
这时,忽然有人冲着河面惊叫:不好了!
丁秋生扭头一看,就见跟在他后面的那条运载物资和骡马的船已经快到岸边了,突然一匹大黑骡子受惊,四蹄乱跳。船身顿时失去平衡,撞到一块礁石上,一个倒扣砸得粉碎。船上的人、牲口和物资全部翻入浪里。
丁秋生和岸边的人,眼睁睁看着船上七八个人和两匹骡子很快消失在浪里,一筹莫展,不胜悲痛。
渡过大渡河的那天傍晚,干部团一营接替红一团警戒东岸及渡口。夜晚忽然风雨骤起,渡口边只有一个老百姓用树枝搭的茅草棚,能容纳四五个人,一营官兵只好轮流进棚避雨。
第二天中午,川军杨学端旅的先头营,已逼近安靖坝。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一营坚决阻击,至少坚持到天黑,掩护红一师主力北进。
李荣、丁秋生保证:就是把一营打光了,也要完成掩护任务。
一营在安靖坝构筑阵地,用密集火力打退了川军先头营的进攻,并乘机发起反击,将敌追出三四里地远。然而杨学端部主力增援上来,重又将一营逼回安靖坝中坝。
丁秋生回忆说:“当时幸亏我们占了地利。那一带大山连绵,山间狭窄,只有一条小道通往东岸渡口,敌人大部队展不开。我们依托隘口、河坝上构筑的工事,一连打退川军一个多团的三次进攻。……”
看到一营在东岸激战,警戒西岸的三营又是呐喊,又是吹号,为一营助威,并用仅有的一门六零迫击炮隔河轰击川军。
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川军终于撑不住了。这时,漆黑的河谷里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川军只得龟缩在悬崖下喘息。
陈赓抓住机会,命令一营悄悄撤出阵地,北上泸定城追赶主力部队。
一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上,摸黑走了10多公里地后才点起火把,又急行军15公里才宿营。
至此,国民党“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预言彻底破产。
此后,毛泽东再也舍不得用干部团作战了。
但这还不是干部团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
※ ※ ※
4天后,干部团从安顺场赶到泸定城与军委纵队会合后,又于5月31日踏上征途。他们沿二郎山南麓东行,经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小镇化林坪,翻越渺无人迹的泡通岗,再折而北向天全。
6月中旬的一天,在离天全县城20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召开会议,部署进军天全。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几个领导人便挤在一间茅屋里和衣而眠,准备天亮后再出发。唯一跟随军委行动的干部团,各营都在村里择地露营。
拂晓时分,突然一阵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一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有大约一个团的兵力,嗷嗷叫地从村外的山上冲了下来。眼看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依偎在一棵大树下的陈赓霍地跳起来,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李荣和丁秋生带着一营跑在前面,迎着泼面而来的子弹,不顾死活地顶着打。就连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一直都没舍得用的“上干队”,这次也全部投入了战斗。
丁秋生后来回忆说,那会儿真是急红眼了,因为那是直接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一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干部团全团打光也在所不惜。
杨森的部队从没遇到过这样骁勇的对手,就见晨光里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烁,七八百人迎着弹雨就扑了上来,那手榴弹扔得跟下饺子似的。交手不多会儿,杨森的川军就撑不住了,由攻转守,继而一路退却。
敌人已仓皇退回到村外山坡上了,陈赓还是觉得危险离军委总部不够远,率领干部团继续追着打,一直把他们赶到山那边去,才令吹号收兵,掩护军委总部迅速北上。
6月12日,干部团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
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懋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干部团各营轮流为会议担负警戒任务。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但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的丰功、它的战绩,永远是长征这一宏大叙事史诗中的辉煌篇章。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