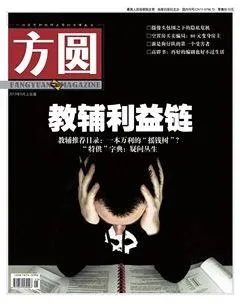高群书: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
拍摄《风声》的时候,这种严谨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高群书向剧组美术部门要求,一定要让角色各自房间里的家具都融入人物的经历,能显示出人物的个性
国内知名导演高群书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以两个特殊群体作为描写对象——警察和罪犯,他执导的最新电影《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也不例外,两个男主角分别就是警察和罪犯。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上映之前,高群书找来几位朋友看片,片子放完后,女性朋友们纷纷表示不喜欢女主人公吕月月,原因是她在警察薛宇和罪犯在熙之间游移不定的做法让人生厌。高群书听后有点急,反问她们:“凭什么一定要求她选择一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怎样的?不也整天这么选择着吗?自己都做不到意志明确,怎能去要求别人?”
高群书始终认为,理解剧中人物应站在现实的立场,电影是一种忠于现实的艺术形式,他在大学修新闻时就被灌输了这种思想,执导电影以后也一直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
高群书所拍的电影往往都有一个精彩的剧本,很多作品甚至很大程度上照搬了现实,但观众并不全部买账,反而会误以为“故事不完整”或“人物太离谱”。高群书坚持认为自己的叙事方式是前卫的,他向《方圆》记者解释道:“身处现实洪流之中,我想要表达的真实生活现状就是如此,舀上一瓢水,里面什么都有。”
“不能因为他们身上有个标签,他们就不是底座了”
高群书上大学的时候,适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是国内文学的黄金时期,有创作梦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读中文系,高群书也不例外。当时河北大学办了第一届中文系新闻专业,高群书想着毕了业还能做记者,比较吃香,就报名读了。
大学时的高群书留着长发,喜欢扮酷,还写诗。他不爱上课,喜欢泡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杂志。
高群书电影方面的启蒙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晚上没事的时候,他总爱纠集一帮朋友走遍保定找电影看,从位于保定东郊的学校出发,一路走到西郊,保定的每个电影院所有公映的电影,他们都要看一遍。高群书还记得第一次看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进去一看,就傻了,那电影中人的状态,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太喜欢了。”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高群书被分配到石家庄的《建设日报》实习。一次,报社领导派他去写一名雷锋式好人的故事。高群书去采访,回来后按照他对好人好事的理解和逻辑写了篇通讯稿交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报纸,他那篇将近四千字的通讯还在,署名是“实习记者高群书”,但文章里已几乎没有他的一句话,全是各种宣传用语。因为这个经历,高群书放弃了当记者的想法。
高群书回忆,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我为什么排斥新闻写作,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物不能因为他身上有‘模范’的标签,就不是现实生活里的‘人’了。”高群书说,他后来自己做导演拍电影,才有机会把这事给“掰了过来”,他拍《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人物原型都是现实社会中的模范人物,但在他的电影里,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而非被无限拔高的偶像。
“实际上,把中国社会看做一座金字塔,这些人全是底座。不能因为他们身上有个标签,他们就不是底座了。”这是高群书对他刻画的人物的认识。
“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
高群书从没把自己做导演拍电影当成一段励志故事,他说这是他与同龄的“第六代”导演们的不同。当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时,对高群书来说,首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在社会上生存。
“就算你还有点理想,它所验证或者参照的仍然是生活。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大学毕业后,本来是要被分配到河北电视台的高群书“阴差阳错”到了石家庄广播电视局,在那个有着三层破红楼的“公社大院”里,唯一让高群书满意的仅仅是每天投射进办公室里的充足的阳光。
为了打破“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他开始把大学时期的一些文学创作拿去投稿,并跟着单位的办公室主任鼓捣起电视剧,自己担任摄像,第一次接触了镜头。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要拍电影的想法,一直以来,他想自己独立做一个片子的念头很强烈,就跟单位申请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涯。
在北京,高群书长期“混迹”社会,当过摄影、拍过广告、开过公司、做过监制。其间,高群书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蓝骷髅》,是部惊悚电影,赔了本。但很快,他与河南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火了,他因电视剧而蹿红,这也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从《中国大案录》开始的过程中,高群书得到了与一些罪犯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与罪犯的交流过程中,高群书发现,许多罪犯只有在真正接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可怜之处。
1986年,西安发生了一起公然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魏振海是西安黑道老大。1991年,魏振海被捕,在采访魏振海以及向办案警方了解案情的过程中,高群书了解到,这名一度让西安市民闻之色变的罪犯,座右铭竟是孙中山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因为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文化,魏振海整天穿整齐的中山装,口袋挂两支钢笔。听搜寻他住处的警察们说,在魏振海的床头还搜到了线装的《左传》,里面还有不少批注和心得。”高群书回忆。
令高群书印象深刻的还有山西“九五打拐案”。其中有一名女人贩子是贵州人,唱歌唱得特别好,她先让别人拐卖了,后来竟加入这个团伙转而拐卖别人。这名女人贩子到案后,讲自己的经历讲到声泪俱下,她说自己挺着个大肚子被警察追,沿着铁路一边逃跑一边把孩子生下来,可是孩子生下来是个死婴,她再哭着亲手把自己的骨肉埋在了铁路边。
还有一名内蒙古人民银行的库管员,后来被判了死刑。他管理着银行金库的钥匙却监守自盗,问他原因,结果是受一个朋友怂恿,让他弄点钱出来做小生意,等赚了钱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哪知最后生意越做越赔,把自己也赔了进去。枪毙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改革的步伐迈得大了一点。”
高群书意识到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好的电影题材,而与此同时,电视剧《中国大案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据说热映的那几个月,西安几乎家家户户都待在电视机前观看,当地公安机关还做了个统计,当月的犯罪率下降了很多。
随后几年里,效仿这种形式的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而高群书却开始谋划如何跳出这种模式,用电影更加真实地叙述警与匪的故事。
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
在大量采访罪犯的过程中,高群书发现,很多案件的基本脉络都是这样:二人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口角,例如打麻将吵架、夫妻闹别扭、邻居间磕磕碰碰等等,可正是因为这些微小的负面情绪,不断地累积,最后才导致了严重犯罪的发生。
高群书试图将这种小人物的时刻潜伏着的、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危险情绪提炼出来,通过影像告诉人们“不要这么做”。《中国大案录》之后,高群书执导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作了一次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很多集都以罪犯的性格弱点来命名,如“软弱”、“愤怒”等等。
但对高群书来说,最符合他“展现小人物犯罪”想法的作品,要数他的电影《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
拍《千钧·一发》的时候,高群书正痴迷于小津安二郎电影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生活逻辑。刚接手《千钧·一发》这个题材,高群书就跑去见了电影主人公原型,齐齐哈尔的那位擅长排雷的模范老片警。采访的时候,高群书发现这个片警讲话太有意思了,让他讲讲平常生活中排雷的过程,讲讲如何同四处安装炸弹的犯罪分子作斗争。那个老片警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一张嘴就能让所有人沉浸其中,该惊心动魄的时候惊心动魄,该掉泪的时候掉泪,该笑的时候笑。于是,高群书一想,还编什么编?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
所以,高群书拍这部电影,就选择了最符合生活逻辑的拍法,而且还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要求他们本色出演。《千钧·一发》之后,高群书又拍了《神探亨特张》,他认为这可以成为一个系列,所讲的都是具有当代现实意义、来源于真实的法律事件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如果高群书这些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有一个贯穿的主题会比现在好看得多。但高群书告诉《方圆》记者,设定那些内容对拍电影出身的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但如果为了单纯让电影更好看,而把不属于它的内容强加于其上,我就失去做这系列电影的全部意义。我拍这些电影都是有目的的,我要为这个时代纪实,所以我不能改变。”
除了作品外在题材基本来源于真人真事,高群书对电影内在的真实性亦尤为重视,他的第一部国内公映的电影《东京审判》就有所显现。
最初看《东京审判》剧本的时候,高群书认为审判过程没有写清晰,这么重大的一个法律事件需要更有张力地表现出来,于是他给剧组定了一个原则:去各地图书馆寻找关于东京审判的文献资料,必须让所有片中的细节都有出处,并且严格符合法律。
拍摄《风声》的时候,这种严谨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高群书向剧组美术部门要求,一定要让角色各自房间里的家具都融入人物的经历,能显示出人物的个性。高群书说,他给《风声》每一名角色都写了小传:“比如张涵予演的吴志国,家乡是哪里、中学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在德国又上的哪所军校;李冰冰演的李宁玉,初中上的什么学校,后来到了美国又上了哪个学校,回到中国又做了什么工作。”
有些内容,观众甚至不能从电影中看到,但高群书还是坚持这样做。“这对导演来说是故事的基础,对演员来说是表演的根本。这些信息传达出来,角色才是立体的,他们所说的话、所思考的东西才会有所不同。”高群书说。
“犯罪片让我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真谛”
因为作品皆为犯罪题材,高群书又被同行称为“中国警匪剧的领军人物”。但实际上他对这个称呼并不“感冒”。
“国内电影的类型片趋势还处在初期阶段,连我自己的电影也在摸索着前行。”高群书解释道。他告诉《方圆》记者,之所以喜欢拍这种题材的电影,并愿意在这个空间里发展下去,原因是自己比别人多出的那些面对面采访罪犯的经验。
“你要拍犯罪题材的电影,去体验和采访真实的罪犯是一道门槛,这个门槛在没有迈过去的时候,你是很难把握这类型电影的拍摄的。不是谁都能理解警方和罪犯的潜在规则。”
高群书是一个有神论者,这些年来他接触的各种离奇的犯罪故事,让他越来越相信“逆道者亡,顺道者昌”的古话。“聆听犯罪故事的时候,你就接触到了这个世界的真谛。”“当年武汉的张明高,身穿雨衣见人就杀,没有任何人真正看清他的样貌特征,就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仍然仅凭目击者的一幅笔绘画像就将其抓获,而且过程十分偶然。这样的巧合,很难说不是天注定的。”高群书说。
这也许能解答在高群书电影中,总是会出现某些难以理解的离奇情节。高群书表示,自己平时上网也喜欢关注真实发生的却又离奇的事情。
高群书的下一部电影叫《井盖》,讲一个黑社会老大掉进了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井,爬上来以后决定维权,结果四处碰壁,遇到各种哭笑不得的事情。“最后没招了,井盖就愤怒了,自个儿飞上天去了。”高群书笑说,这是他打算设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