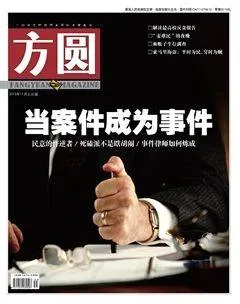克兰比尔的尊严
【√】 警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法官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成为罪犯的克兰比尔却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它让我们反省:法律的功用到底应当定位在哪里?
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散文很著名,他写小说也十分在行,短篇小说《克兰比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誉为“世界必读的100篇短篇小说”之一。教科书上称“克兰比尔的冤案是影射德雷福斯事件。法朗士写这篇小说的用意,在于抗议对德雷福斯的诬告和陷害。” 德雷福斯事件,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然而,现在用法律的眼光读这篇小说,也有深意在里边。
故事很简单。克兰比尔是蒙马特尔街上走街串巷的卖菜小贩。一天在等买主送菜钱时,一名警察责令他立即将车推走。克兰比尔辩称自己在等菜钱,警察连说三遍,随后便要办他个“违警罪”。克兰比尔叫道:“该死的母牛”、“上帝作证,我可不是那种藐视法律的人。”克兰比尔最终被定罪,“判处15天的监禁和50法郎的罚款”。
小说的震撼在于克兰比尔出狱之后。尽管他自己不以为荣,也不以为耻,甚至没有一个痛苦的回忆,但是他发现,人们开始对他冷淡。
他去找欠钱的贝尔亚太太讨要15个苏的菜钱时,她甚至没有瞧他一眼。就连过去最忠实的主顾洛尔太太,也瞧不起他了,人们都嫌弃他,说他是个犯人。人们骂他,逃避他,整个社会都这样对待他。他几乎跟所有的人都吵了架。由此他变成了一个说话粗鲁,蛮不讲理的人。他不断地酗酒,和人吵架,“他的精神瓦解了”。
从前他可以一天赚到100苏的银币,如今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极端的贫困向他袭来,他被房主赶出,借住在停车房里,“恶臭的脏水,做伴的蜘蛛和老鼠”,让他想到了“不会挨冻、不会受饥饿”的监狱。于是他走到街上,对一个警察大声说:“该死的母牛,我骂你,你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警察不予理睬:“把说浑话的酒鬼抓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小说的结尾是:“克兰比尔垂头丧气,冒雨向黑夜深处走去。”
小说的结尾富于喜剧性,类似《警察与赞美诗》,只是结局不同:前者的主人公想进监狱而不得,后者的主人公在不想进监狱的时候进了监狱。如果我们再做深一层的思考,后者想进监狱是为了躲避贫困,而在法朗士的笔下,克兰比尔的贫困却是成为犯人之后。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孔子教诲国人的一句话在克兰比尔身上完全应验,自从他成为“违警罪”的罪犯之后,他就被社会归为“异类”,社会不再接纳他,他开始贫困,开始堕落,开始向往监狱生活。而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让一个正常人变成了社会的累赘,如果更通俗一点,是什么让一个好人变坏的?
这是一次并不严重的“违警”。他的车子阻碍了交通,并非有意,而是为了等顾主的菜钱;警察督促三次,他申辩三次,在警察看来就是对警察的不敬了,何况他还有一句“该死的母牛”的脏话,尽管这句脏话到底是警察先说的,还是克兰比尔先说的,在法庭上仍是莫衷一是。
警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法官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成为罪犯的克兰比尔却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它让我们反省:法律的功用到底应当定位在哪里?不错,是维护秩序,是维护公正,但归根结底是维护人的尊严,是让人有尊严地生活着。倘若离开了这个根本,那么即使是公正的法律也可能把“人”变成“鬼”,克兰比尔的蜕变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试想一下,一个“鬼”多的社会,还会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吗?而制造这样的社会,还会是法律的初衷吗?
也许是小说,也许是法朗士有意制造一种氛围。生活中不会有如此倒霉的克兰比尔,那是小说。但是放眼当下,类似的克兰比尔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