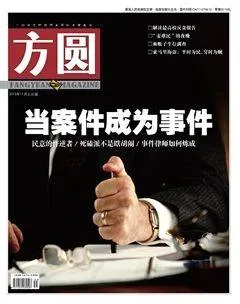新闻报道别被个人恩怨挟持

陈永洲案,现如今变为一桩受人指使,拿人钱财,发表不实报道的职业丑闻。这两天,微博上另一件仇子明案也被翻出,这两起在全民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弹的背景,都是记者深陷企业之间的恶争,事件的根源都在记者是否收取一方的钱财。的确,在采访过程中调查记者别说收钱,即使收人恩惠,就容易授人把柄。一旦报道文章出刊,记者和报社很容易被认为是私人恩怨,企业间利益纠葛的工具。
这让我想起一个亲身经历,那是我去采访“房媳”事件。我在网上检索了这起公共事件发酵以来所有的报道,并找到了第一爆料人和他的联系方式。我们见面时,他正同两名助手商议第二天去隔壁县市的行程。他把我介绍给助手,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感到一丝惊讶,这个人不简单。通常的举报人都是担惊受怕、半遮半掩的,而他显然不是。来此之8rG/KMfYVOOFBUfm1MPrSQ==前,我曾读过一个关于他的报道,在这篇人物报道里,该线人被记者描述成一个遭受重大迫害,如今沦为没有生活依靠的文人,而眼前的他显然不是这样。他有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和手下,更要命的是,通过名片上“新闻策划人”的头衔和简介,我知道山西省好几起轰动性新闻事件都有他策划的痕迹。
这个爆料人给我联系方式,让我去联系其他知情人。到了运城市当地,我在采访中逐渐发现向我爆料的人都或多或少跟房媳家族成员有矛盾。我也开始了解到,原来持续近半年的房媳事件幕后的确有人在利用媒体造势。
我的体会是调查性报道要讲究平衡,但很多时候记者容易陷入举报人预设的立场,很容易成为举报者的枪手。所以记者接受举报材料要看类型。比如,仇子明在微博上称只接受两类爆料:严重践踏公众利益;政府恶意违法。也就是说针对的是公权力,站在天然的弱者一方。
当时在山西采访时,有人通过中间人找到我住的宾馆,希望我去“捅”另外一起“不法”之事。找我的人是运城市一位审计局干部,他要举报运城市下辖某县的公安局长,他给我一份工资表,里面有证据表明公安局长安排自己女儿在公安局里吃空饷,目的是给女儿以后“提干”累计工作年龄。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说是去年的事,目前该局长听了风声,将女儿送往北京上大学。当我得知,这个审计局干部举报公安局长是因为两人先前有仇时,我婉拒了他的请求。当时我的考量是,虽说公安局长是违了规,但吃空饷的事都是过去式了,再去追击痛打,在新闻价值上没有多大意义,而我本人可能成为举报人打击报复的工具,况且还有可能毁掉一个在读大学生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