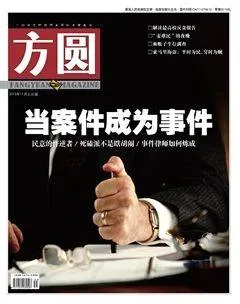杨学林:“死磕派”不是瞎胡闹

【√】“一个因非法律因素遭遇障碍的案件,如果引起舆论关注,从而引起高层领导关注,那这个案子往往就会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开展,这对当事人是有利的。所以搞大的目的不是搞大,而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人物名片
杨学林,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委员,业务领域为刑事辩护。从2005年开始密切关注日益激化的官民矛盾,逐渐将工作重点放在办理维护公民人权的案件上,特别注重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
2011年接受李庄家属的委托出庭为李庄辩护。通过“北海案”、“小河案”、“桂松案”等影响力案件,成为“死磕派”律师的提出者和中坚力量。
近年来,地道的东北方言“死磕”,竟成为法律圈内某一群体的标签,这或许谁也未曾料想到。
“死磕派”在中国律师界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从李庄案开始,以“公开”手段吸引舆论、抗议案件审理程序违法、与办案机关对抗的律师们往往被归入此类。
经过四年的沉淀与酝酿,“针锋相对、抗议激烈、搞大案子、吸引媒体”似乎成为“死磕派”律师的标准形象。曾被驱逐出庭、遭遇威胁与人身伤害的杨金柱、陈光武、迟夙生等个性鲜明的律师即“死磕派”的代表人物。
人们对“死磕派”的评价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赞誉者将其称为“以惨烈的方式推动中国法治,是悲情斗士”,诋毁者将其称为“为私利破坏法律与秩序的庭闹儿”。
首次将某一律师群体公开称为“死磕派”的律师杨学林,看上去与“死磕派”似乎毫不搭边。虽然他同“死磕派”一样,也一次次出现在李庄案、小河案、北海案等“死磕派”律师必然出现的案件中,却总是以一种理智和沉稳的形象出现在人前,在媒体、律师界乃至司法部门中口碑都很好。不过,这并不能阻挡他严正地声明:“我是‘死磕派’,我以‘死磕派’为荣。”
“死磕”的道路顺其自然
从商业律师,到维权律师,再到“死磕”律师,这是杨学林的“成长道路”。
“刚当律师的时候,只要能赚钱,什么案子都做,也不分专业,银行、合同、纠纷、离婚,只要有律师费就干。到了一定时候,解决了生存问题,就要考虑社会责任。”杨学林说。
在北京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里,希望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杨学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2005年,浙江东阳“4·10”群体事件爆发,当地居民因环保问题集结起来,最终导致警民冲突。“老百姓抓了很多,我们委员会里的8、9名律师一起去为他们辩护,效果很好。后来通过环境污染受害者维权、失地农民维权、毒奶粉宝宝维权等一系列案件,我们这批律师成为了社会上专门关注弱势群体的‘维权律师’。”
2009年李庄案发,关于证人出庭、审判管辖等问题的探讨逐一浮出水面。也是从这时起,杨学林逐步开始关注诉讼程序明显违法的案件。
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涉黑案”被看作当代刑辩律师的整装出场,全国88名律师受聘无偿为57名被告出庭辩护,因质疑小河法院违法管辖,曾有4位律师被逐出法庭,20多位律师多次受到审判长口头警告,19名外地律师被受官方背地操控的当事人“不用”。
杨学林回忆说:“当时情况很不好,基本几分钟法官和律师就发生一次冲突,非常激烈,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当然,法庭上的你死我活和现实中不一样,法官明显违法,没有任何预兆将律师驱逐出庭,律师不惜自己被拘留,和办案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抗争。当时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说了一句话,‘这案子,必须死磕’。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觉得很贴切,死磕代表一种抗争,当时和派系并无关系。”
有次聚会,律师周泽和杨学林开玩笑,称有些刑事辩护律师不坚持程序公正性,开庭走过场、走形式,干脆叫“形式辩护”更妥帖。参考之前自己曾提出有些刑事律师通过幕后勾兑解决案子,可称为“勾兑派”,杨学林也玩笑般地随手将“三分法”贴上微博:刑辩律师分为“形式派”、“勾兑派”、“死磕派”。杨金柱律师也立刻跟上,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死磕派’律师验证中心”。
杨学林对《方圆》记者说:“这种分法确实只是一种自我调侃,包括验证中心,都是玩笑成分居多,并没有学术上的意义,更不会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不过这条看似无意的微博,险些让形象一向良好的杨学林自毁长城。
争议重重“死磕派”
对于“死磕派”,第一波反对声音来自同行。“三分法”无疑给非“死磕派”律师扣上了道义上存在问题的帽I3lV7mQgIAagGS75UUrhqJX3Mi5CSGWPQWRRyeo8/L8=子。部分律师隐晦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做他们的‘死磕派’,我做我的普通律师”。律师王立峰则干脆发表文章,列出十条“死磕派”律师的“德行”,讽刺他们无非是利用轰动效应、仇官仇富心理和批判体制以博眼球,言语间颇有指责“死磕派”律师喜欢炒作、煽情和不顾当事人利益的意味。
第二波的反对声音来自公认的“死磕派”内部。被认为是“死磕派”律师的朱明勇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死磕派”律师,和他抱有同样看法的是斯伟江和陈有西。
第三波反对声音来自最高法原副院长张军,他在一次法官培训会上把这种律师的行为归纳成律师“闹庭”,并要求法官加强庭审的掌控能力。
本是一句玩笑,结果引来重重争议,这出乎杨学林的意料。或许犬儒主义当道,“你认真你就输了”依然管用,但“你不认真或许更糟”更是真理。
杨学林认为,个别司法部门反对“死磕派”可能是因为立场不同;同行反对“死磕派”大多是因为“三分法”将“死磕派”划为了异类,这些都与“死磕派”的标签化不无关系。
“我要说明的是,‘死磕派’并不是瞎胡闹。 ‘死磕派’律师接到案子,第一件事想到的是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而不是死磕,我们比谁都希望案件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办。但往往我们会遇到非法律因素的障碍,而原本中立的法庭恰恰成为了这些障碍的保护人。”
虽然张培鸿律师对“死磕派”律师不甚赞同,但他认为杨学林说的现象存在。“‘死磕派’是司法的大环境催逼的结果,是且仅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与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密切相关。在制度层面的改革裹足不前的情况下,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等问题未见改善,这一局面使法院无法对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惩戒,还在某种程度上不断为违法行为背书。作为刑事案件的诉讼参与人,法庭几乎是辩护律师唯一的舞台,在整个诉讼活动中最直接、最公开、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庭审,也就成了他们仅有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他们不愿再失去这最后的领地。律师之所以死磕,部分是因为法庭先失去了独立性。”
“好比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裁判吹黑哨本已违背了规则,但过分的偏袒就似裁判直接下场帮助另一方踢球,我们能做的只有抱住裁判的大腿,不让他踢。这么做表面上是犯规,是违反法庭纪律,但不这么做,就无法制止下场踢球的法庭。没有人愿意死磕,我们希望以平和的、安静的方式来进行庭审,我们也不费力,没风险。”杨学林说。
公开并非单纯“闹大”
从出发点上,杨学林解释了死磕的必要,从技术手段上,“死磕派”也并非单纯地“抱大腿”。
杨学林称律师当庭抗辩的点“全是从《刑事诉讼法》上抄的,一个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来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来”。
张培鸿律师则归纳:“他们激活了一些早已被明确规定但在现实中却始终沉睡的条款;另一方面,他们又将那些被正常使用的条款重新做合理的引申与解释,并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这些做法往往集中在诸如管辖权、回避制度、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的权利规定中。”
另一方面,“死磕派”律师对外的“搞大”,实际上就是公开。“可以公开的案件,如果不公开就一定有问题。”
“这也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一个因非法律因素遭遇障碍的案件,如果引起舆论关注,从而引起高层领导关注,那这个案子往往就会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开展,这对当事人是有利的。所以搞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大,而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杨学林说。
杨学林认为“黎庆洪打黑案”就是一件不得不搞大的案子,其公开手段是发微博。“必须搞大,非得搞大!当时律师已经失去了辩护的权利,主流媒体也根本不敢介入,个别勇敢的记者来了,也被叫了回去。这件案子全靠律师的双手,用140个字的微博一点点记录33天的庭审活动,从而引起最高检、最高法和司法部的关注,三个最高司法部门派出领导坐镇,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
“死磕派”的搞大也非全程,“前期大力死磕,网络揭露,后期庭审和谐,网络消声。”皆因违法程序已回归正常轨道,在本质上,“死磕派”律师也是务实的。“铲球是不是犯规,要看那脚是冲着人去的还是冲着球去的。”如果搞大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就坚决搞大。相反,对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子,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子,那就绝对不能搞大。这样的辩护原则,“死磕派”律师是把握得很精准的。这就是“死磕派”与炒作派的区别。
在“黎庆洪打黑案”后期,杨学林甚至当庭和书面都称赞过法官:“感谢合议庭的法官们,为我履行辩护职责提供了便利。”
每位辩护律师执业所在地的司法局都派出人员当庭听审。北京市司法局每天都有2个人在,晚上经常和杨学林这些北京律师吃个饭,他们评价:“这些律师辩护水平还是可以的,也没有出格的行为,并不像传说的那样乱来。”
“所谓的死磕,实际上没有策划,也没有方案。我认为,就算通过死磕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侥幸的。我代理过的很多案子,也和法庭产生了针锋相对的矛盾,并希望通过公开让一切回归正轨,不过收效甚微。可奇怪的是,死磕从未带来任何坏的效果,比如虽然案子程序有问题,但判决结果还是在正常量刑范围内的,不会因为我们死磕了就多判几年。为何会这样,我也无法解释。”杨学林说。
“我名声好,是因为他们冲在第一线”
“死磕派”引发的争议并没有完全抹杀杨学林固有的公众形象。分析其原因,杨学林认为与自己在历次的庭审中低调的作风有关。“大家会看到,杨学林没有闹,而是沉稳、理智地在辩护,所以杨学林是个好律师。”
不过,他亦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坐在那里安静地辩护,是因为其他‘死磕派’律师冲在了第一线,把他挡在身后,以损毁形象为代价为他换来了能正常辩护的机会。
2012年“黎庆洪打黑案”中,恰恰因为有了杨金柱、周泽这样的律师以激烈的方式和违法行为抗争,杨学林才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完整阐述,否则法官会在2分钟的时间就打断他,“提交一个书面的辩护词就算了”。
今年在广东的一个案件里,当地法院不顾最高法的明文规定,坚持律师必须安检以后才能进入,辩护席上也只有一排桌子,很多律师无处安放电脑和案卷。对此,法院称“我们就是这个条件。”杨金柱站出来“咆哮公堂”,“把你们院长找来”,“如果要安检、如果不给律师提供正常的辩护环境,我们坚决不开庭”。经过一个小时的僵持,法院最终妥协。
“在这种案件里,我单独辩护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我必须和‘死磕派’在一起,我也坚持自己就是个‘死磕派’。”杨学林说。
杨学林不是杨金柱等人唯一的受益人,一向温和的张培鸿在今年也依靠他们打开了法院的大门。和往常悲壮激烈的抗争相比,今年初的“送红薯”事件则显得颇有戏剧性。
福建省“福清纪委爆炸案”主犯吴昌龙已被羁押12年仍未判决,其姐姐及当地律师林洪楠等人多年努力无果。去年底,张培鸿接手此案,但福建省高院拒绝吴昌龙更换律师,张培鸿连高院的门都没能进去,于是找到杨金柱和伍雷出马。
两人接手后,多次联系经办法官无果,开始死磕——花8元钱买了5个红薯,在高院门口穿着律师袍“散步”,引起注意后,被“请进”法院沟通,并在微博上“直播”沟通内容,法官很快便同意二人为吴昌龙辩护。几个月后,吴昌龙及同案被告人共5人被宣告无罪释放。
杨金柱等人冲在第一线已成习惯,“死磕派”内部皆称并没有做过明确的分工。不愿称自己是“死磕派”的朱明勇律师实际上也是个“先锋”,“朱明勇的辩护从不留情面,甚至比我激烈,要不是有杨金柱、周泽他们在,被撵出庭的估计他会是第一个。”杨学林回忆。
“因为他们的激烈,往往使大部分‘死磕派’被渲染为没有水平的胡闹,但实际上,这些律师的法律功底也是很深厚的。杨金柱律师在没有辩护稿的情况下,当庭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每一点都讲得很透彻,一般律师根本做不到,我深为钦佩。”杨学林说。
后“死磕”与消灭“死磕”
在几件重大的“死磕”案件之后,杨学林觉得法院的办案氛围有所变化,刑诉案件的庭审违反诉讼程序的情况减少了。有些案子的审判长甚至满足律师提出的所有合法的程序上的要求,比如以往在职务犯罪中很少传唤证人到庭作证,现在有“死磕派”律师就遇到有法院同意传唤所有有关证人到庭作证,甚至包括反贪局局长。
今年3月份,杨学林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代理一起打黑案件,庭审进行了16天,主审法官“答应了律师提的所有要求”。杨学林说,庭审很和谐,一点死磕的余地都没有。
杨学林在为重庆“不雅视频”案雷政富辩护时,法官更是客气到了一定程度。法官主动提出,让律师观看全部录像,哪怕杨学林表示根据掌握的情况,录像无需全部观看,法官依然坚持。同时,全部案卷也向律师开放,并将案卷提前复印好,律师看过原件之后,可以把全部案卷的复印件免费拿走。
“这或许是‘死磕派’对中国法治的一个小小影响,使司法部门比较注重律师的意见,在办案环节变得格外谨慎。”杨学林说。
但杨学林坚持认为死磕只能磕程序,实体是不需要去磕的。“程序是当场剥夺律师的辩护权,不死磕马上就完蛋了。实体不同,一审不行还有二审,二审不行可以申诉,申诉不行向上一级再申诉,总有救济程序。”虽然双峰打黑案的判决结果让他不大满意,但他表示“也只能这样”了。
再者,虽有原因和理由,“死磕派”质疑法官、将控辩审三者的关系彻底拉平到同一个平面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一些争议,比如法庭尊严如何维护的问题。
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交给新一批的“死磕派”律师去解决,“死磕派”的旗帜作用被杨学林认为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之一。“当年做弱势群体维权的人少,结果都集中在我们这批人身上,而之后受我们的一些影响,愿意做这类案件的律师多了,这是中国律师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体现。我想‘死磕派’律师也是如此,我们还未解决的,总有人要接过我们的工作,用更适合的方式,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一小步。”
不过,杨学林认为,所有的“死磕派”律师的最大愿望不是找到自己的接班人,而是促成这个群体的消亡。“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死磕,‘死磕派’的目的就是消灭死磕,希望律师不再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进步,但在当下,就算我们毁誉参半,也是中国法治史上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