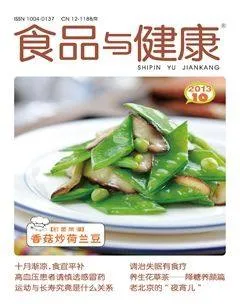花非花
笔者进餐馆坐下,一位年轻又很精神的小帅哥递上一本印得花花绿绿的菜谱。我看了他一眼,指着菜单上的“木须肉”说:“这个长胡子的是什么木头,红木?花梨?”小堂倌自作聪明:“这单子印错了,应该是苜蓿肉。”“那就更不对了。你说木须肉还沾点边,因为此菜的主料是肉片炒鸡蛋,俏头是黄瓜和木耳。木耳也算是木头上长的胡子。可是苜蓿是野菜,原是喂牛的呀。”
小堂倌无语了,开始审视这老头儿是不是来混吃碰瓷的。好在大堂经理认得我,笑嘻嘻地说:“这位是许老,经常在电视上讲食文化的。”我赶忙拉小伙子坐下给他讲,这道菜讲究的是鸡蛋的炒法。炒出的鸡蛋要色泽金黄,有嚼头,味道鲜香而不腻,出盘要颤颤地像朵朵金桂。桂花又名木樨,因此这道菜要叫“木樨肉”。
以鸡蛋做文章的菜还有“西红柿炒自己”。有道是,“刺身不能有刺,黄瓜必须有刺,西红柿的大忌是不能炒自己。”西红柿怎么能炒自己呢?原来,这种提法缘自一种误判。东北人本来把它念成“西红柿炒鸡子儿”,即西红柿炒鸡蛋的意思。不懂东北话的,自然按这话的谐音去理解。其实这也不是拿东北哥们儿开涮,这么多年来,本山大叔的小品老火老火的,忽悠得全国人民满嘴蹦“那必须的”、“这个可以有”等东北话,又有谁能说东北话不能登大雅之堂呢?
关于“西红柿炒自己”的另一种出处,则跟地域无关:说的是几位客人到餐馆吃饭,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但菜上来后发现里面的鸡蛋太少,肉眼几乎看不出来,西红柿炒鸡蛋遂变成西红柿炒自己了。这虽然只是一个笑谈,但西红柿的身价却曾经高贵过。上个世纪廿年代时,天津市场上的西红柿很少,只有在租界地才能买得到。当时的废帝溥仪住在张园,他的“御膳”才有“火柿子(即西红柿)炒鸡蛋”。那时的“火柿子”和现在的味道也不一样。余记得儿时见到的火柿子是粉红色的,吃到嘴里是发沙的那种淡淡的酸甜,市价是很贵的。当然,我们现在调侃的“西红柿炒自己”也是建立在时蔬价格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按现下波动的市场价,说不定有一天“蒜你狠”、“姜你军”之后,西红柿的价格超过鸡蛋了,那店家只好卖“自己炒自己”了,玩笑!
说起鸡蛋来,鸡蛋花不是冲的鸡蛋汤的蛋花,而是一种植物的花朵,和金银花、菊花、槐花、木棉花组成“五花茶”,是一种清湿解热的代茶方。乌鱼蛋不是黑鱼下的蛋,而是干燥的乌贼卵巢,用其为原料做的“乌鱼蛋汤”常见于高档宴席。
其实,中餐宴席上名不符实、以想象命名的烹饪原料或菜名有很多,玩的是个意境与情调。
西米不是米,是树制品。松花不是花,是鸭蛋制品。松花粉不是鸭蛋,是松树的花粉。淡菜不是蔬菜,是贻贝干。燕菜不是燕窝,是萝卜菜。炒粉虫不是虫,是种面食。乌龟子不是蛋,是南京小元宵。索饼不是饼,是面条。栮脯不是脯,是木耳。木鱼不是敲的,是粽笋。抄手没手,是蜀馄饨。蝤蛑不是牛虻,是温州的螃蟹。鸭信就是鸭舌,但鱼信不是鱼舌,而是鲨鱼、鲟、鳇脊髓的干制品,又称鱼筋。鱼肚不是鱼肚子,而是大黄鱼、鳇、鲟的胃,或者是鮸鱼、毛尝鱼、鳗鲡的鳔和胃的干制品。鹿头不是鹿的头而是鱼唇,即鲨、鲟、鳇犁头鳐等鱼唇部软肉的干制品。我国古代有升学宴,是文科中榜后,要举行“鹿鸣宴”。此宴因在会上演奏《诗经》中的《鹿鸣》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助兴而得名,而不是凑在一起啃鹿肉。千万不要“鱼唇不对鹿嘴”哟!
不过有一种菜大家都明白。到饭馆要了一碟“熘腰花”,那腰花绝对不是花。因为在全国诸菜系中,大部分都有腰花菜。
鲁菜有“炮(bao)三样”,系由猪腰、肝、瘦肉三种原料爆炒而成。特点是质地脆嫩,鲜咸爽口。
津菜有“熘腰花”,系将猪腰打花上浆、滑熟,其特点为脆嫩可口,蒜香味浓。亦有“老炮三”,源自鲁菜,腰子打花上浆,爆炒成菜。
冀菜有“熘腰花”,系以猪腰为主,菠菜为俏。方法是将猪腰去净腰臊,刀剞成花,滑熘而成。成菜形似麦穗,软嫩清香。
湘菜有“玉麟香腰”,以猪腰、猪肉、鳜鱼肉等为主料。传说为清湘军水师彭玉麟家宴菜,在衡阳民间为红白宴席的“头碗”。
在我国传统食文化中,动物的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被称作“不典之物”,大概是受了儒家经典的影响。儒家谓不守常道,不合准则为“不典”。其实典与不典,仅仅为一种观念,很多人照吃不误,因为许多人还相信进补之道:“吃啥补啥”。补什么呢?补腰补肾。因为认为肾是主管储排水和藏精之地,所以似乎一时所有的男人都肾亏了,都阳痿了,都需要进补了。而所有家长对子女的疼爱,以及男男女女之间的缠绵之情,通常表现在电话的一句话里:“回来喝汤吧。”于是滋补药广告商趁机兜售一句口号:“我们一定要拥有一个强大的肾!”这就是忽悠误导了。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五行”中所指的“肾”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肾脏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的饮食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食物只要有利于养生健身,无毒无害,自然和谐,味道佳美,就可以照吃不误。所以,炒腰花、炒腰片、宫保腰块、醉腰丝、炸麻花腰子几乎传遍各地。不过老朽还是奉劝各位,肝肾美食,适可而止,少吃为佳。
葱花也不是葱的花,而是一种佐料。现在很多人弄不清烹调过程的中作料与佐料之分。作料是烹调过程中使用的调味料,如醋、酱油、味精等。佐料是烹调过程中起调味作用的辅料食材,如葱、姜、蒜等,有些佐料为绿叶辅托主料红花,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葱烧海参中的葱、烧茄子中的蒜米等,在天津菜中称作“俏头”,粤菜中称为“料头”。在中国要吃饭就离不开葱、姜、蒜。西餐用香料很多,一束一束显摆地挂在餐厅里,唯独没有葱。
山东人对葱情有独钟。过去谁家生了小孩在“洗三”时,山东人就要用大葱轻轻地打几下屁股,这叫“打葱”,寓意越打越聪明。山东大汉在赶路时,用不着进饭馆,就在路边荫凉地抽出一根大葱用煎饼卷着吃。那葱要有一米长,葱白要有小擀面杖粗。大汉一口一口地吃得香,看的人却惊得吐舌头。此为吃界豪放派也。
中国美食中的用葱是有很多学问的。该用小葱的地方绝不用大葱,该用大葱的时候也绝对不能用小葱。
“十里荷花,雨巷吴娃”,在吴侬软语的苏杭将小葱叫香葱。此小葱不比北方春天下来的那种,不是一根根的,而是一撮撮的。到了上海吃阳春面离不开香葱。汤宽面少,全仗碧绿的葱末渲染画面。此外,生煎包和城隍庙的大荠菜馄饨也离不开香葱,好像不打这个标识就算不上得上海名吃似的,此为吃中婉约派也。
到北京吃烤鸭,最离不开葱。现在饭桌多上葱丝,雅则雅矣,但无豪爽,反而不如将小葱切为两寸段,蘸酱卷饼,吃着痛快。
吃大葱菜当然要去山东馆子吃葱烧海参。盘中之物除了海参便是大葱。这道菜的妙处是葱段要比海参还好吃。海参虽是贵物,但经常是盘里的海参还没吃完,那葱段却不见了踪影,吃到最后,盘里剩下的汤汁油亮诱人,最宜以此汁下饭。过去的大饭庄用整捆的葱来制葱油烹制此菜,费料费时,如今谁还下这“笨”功夫。
葱炮羊肉也要用葱,但不能用葱丝。否则肉已爆熟而葱丝则黑糊难看,不忍卒睹。再提醒各位,此菜要放盐而不能放酱油,否则便不是味了。
葱花常用来做馅活。史记后周有洛中团练史郭进得周世宗故宫女婢,善烹美食。郭遂大宴宾客显摆。席上,郭令女婢献美食。女婢答只会做饼。郭无奈只好令献饼。婢答只会做馅饼。郭令做馅饼。婢答只会剁馅中之葱……由此看来,专家是不可全信的。
我们再介绍一道雪花菜。雪花不是花。江西有名菜“雪花泥”,是用豆腐渣和肉为料做成。清代《随息居饮食谱》载:“生榨腐渣,炒食”。制作方法是取豆腐渣焙干了与煮烂后的猪肉酱一起入沙锅,加干辣粉、生姜末、小虾米、小炖肉汁及调料合成。很多人把豆腐渣当作弃物,实际上如果烹调得当,它也是一道美食。老朽在北京吃过麻豆腐,那要用羊肉炒,配二锅头。
唐代有名菜曰“雪婴儿”,出自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其制法仅有“治蛙、豆英贴”简单的5个字。详情见王子辉先生的《仿唐菜点》一书。
烹饪界造雪,常用蛋泡糊(即高丽糊、芙蓉糊、滚泡糊),也有直称“雪衣糊”者。蛋泡糊是将鸡蛋清搅打成泡沫后,加适量干淀粉或面粉调制用于松炸的菜肴。此糊制成后色白如雪,炸后白里泛黄。有的还直接用蛋泡挑或抹在菜肴的表面,让人感到菜面有雪状。如川菜“雪花桃泥”、陇菜“雪山骆驼”、楚菜“雪山鱼片”等。糕点则有“雪花酥”、“雪花糕”、“雪蒸糕”,冷食也有“雪花酪”等。
“叫花不是花”这种奇妙的称法不仅在中餐有,在西餐也有。现在的年轻情侣都喜欢在约会的时候来份意大利提拉米苏,用小勺子舀一点,入口即化,最适合含情脉脉时。其实提拉米苏的意大利文的原意是很性感的,是pick me up的意思,直说就是“带我走吧”之类的。
中国饮食是以味为核心以养生为目的的。它是上升到哲学艺术层面的一种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它是历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对饮食文化、餐饮文化的追求也产生了质的飞跃,逐渐游离了单纯追求物欲,升华为一种精神享受,憧憬在饮食活动中吃出品位、吃出情趣、吃出愉悦。当然,这种审美应该能够体现出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而不是相反。
花非花,雾非雾,大德之用就是为道。
(下期预告:国人爱喝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