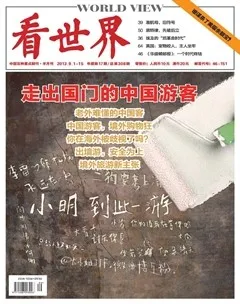冬菜扫荡积存的陈腐
母亲来自台中东势客家村庄,父亲出生在江西武夷山脚下的客家村,丈夫则是南京出生的河南人,周岁便迁移到新竹公馆的客家聚落,因此也说得一口客家话。独独我,莫名其妙地在中年过后才发现自己与客家人的渊源如此深,但一句完整的客家话都不会说,恰恰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地被客家文化包围,却对客家文化了解不深入。
若非接触过传统特质鲜明的客家饮食文化,我当真几乎忘了客家人的存在。许多经典客家腌制品当中,冬菜,是最常见的价廉物美之作。小时候经常在面馆与小吃摊上看见免费供应的冬菜,近年来,几乎找不到了。据说是制作繁复又不受欢迎,因此近乎绝迹。若真想找回这道古早味,只能去客家村庄里,看看那仍保留柴火锅灶的砖瓦厨房里,是否有老瓮藏起的冬菜。
冬菜,顾名思义就是冬季盛产大白菜之时,处理过量的白菜,制作成半干状态的未发酵咸菜,以备冬天过节时随时取用,熬过那蔬果停产的严寒季节。很显然地,除了大白菜的品种南北有别外,各家也有自己的独门口味,除了因添加蒜泥与否而决定了津京冬菜荤素有别外,川冬菜用芥菜、蒜薹、花椒和八角的制作,又增添了别传的异味。而我最喜欢的气味,则是山东日照特产的进京贡品素冬菜,细长而芬芳,闻着扑鼻香,特别清雅怡人。
台湾南方与澎湖小岛一带流行的高丽菜干,跟冬菜的制作方式类似,却风味有别,经常用来拌炒鱼头或剩余的各种杂牌海鲜,把原本残余的物资利用,晋升为风味绝佳的地方特产,一时演变为大宴小酌最受欢迎的佳肴,想尝鲜的人还必需预定。有位澎湖餐饮界大老板表示:“这道菜价廉却费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上菜单,只用来讨好老顾客。”难怪北台湾不太容易吃到,就连南台湾还得是熟客,才有机会解馋。一道最家常的古早味,竟成极品绝响,在我们这处处速食文化的年代,特别感谢自己生得早,记忆中仍有这些好滋味,堪慰此生。
母亲在西门町经营美发院时期,无暇照顾初逢丧父仍年幼的我,寒暑假经常在她的朋友或职工家里轮流寄养,很巧地,我寄养的家庭,几乎都是客家人。回首当年,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厨房。尤其是老婆婆的锅灶旁,堆满了各种瓦罐,随手掏出来都是奇异的美味,三两下便能摆上一桌,就着浓稠的新米熬粥,特别馥郁芬芳地齿颊留香。很自然地,假期结束,大包小包地辗转搭火车与汽车,回到台北市区,手里拎最多的,就是自制冬菜。无论是干吃或用来搭配其他食材,蒸煮炒炸甚至用作水饺与面盒子的馅料,都很相宜。
曾经试图自己动手做冬菜,工序很简单,真要做时,才发现若无天时地利的配合,也会无计可施。我在北台湾住了半世纪,盛产白菜的季节里,多半雨纷纷,阳光炙烈的夏日,却又很难看见价廉物美的白菜或高丽菜。想起来简单,执行时却是如此之难,直到家中用了数十年的瓦斯炉退休,改换拥有大烤箱的电炉,才想起,这绝对是取代阳光做烤菜的时机。用微火烤晒蔬菜,逼出自然香气,也就随时能享受古早味了。
为何特别想念冬菜?除了好吃的记忆外,太阳的气味与能量,加诸当季蔬果后,激发的独特香气,让经历过更年期的敏感五官,汲取大自然气息,使人更能享受天然流动的芬芳。仿佛透过扑鼻香气与齿颊间流动的阳光暖意,便能让浑浑噩噩的灵魂苏醒,一口一口地抚慰着倦怠,无形中产生绝佳的食疗作用。古人偏爱日晒食品的理由,终于在步入晚年的身体感官里,明确地感受到医书上强调日晒时的真意。看似人人惊闻回避的更年期,于我而言,是最好的老师。自此,也终于明白,为何中医老师要谆谆告诫:“全世界没有比自己更好的老师!”冬菜,就是自我发现的契机。
陈腐之气,未尝不是回春的转机。冬菜,是干瘪失去生命的蔬菜,更年期,是走向衰老的预告,这两者,在我身上,却发挥了绝妙回春作用,身心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