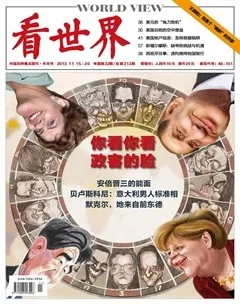庐隐: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
还记得是谁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吗?那就是“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
美国女汉学家艾米·杜丽(Amy D. Dooling)和杜生(Kristina M. Torgeson)合编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前些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硬皮版,收录了18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庐隐。
童年:写满遗弃与伤悲
庐隐出生时,便无辜地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她一生的悲剧色彩,就此注定。
她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哥。1898年5月4日,她降生那天外祖母去世。缘此,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庐隐在懵懂无知的婴儿时代,即遭到全家人的厌弃;2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3岁后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缺爱的孩子慢慢养成了爱哭闹、倔犟的脾气。偏巧这时她还得了很重的热病。奶妈将她带到乡村,在乡野中她恢复了健康。日后在中篇小说《海滨故人》里,她如此回忆:“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地过了大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这里的露沙无疑有着庐隐自己的影子。
庐隐6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庐隐四兄妹随母投奔北京外祖父家。庐隐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但她因不得母亲欢心,未能入学。严苛的姨母担任其启蒙老师,每天她被关在一间小房里背书。她常遭到姨母的责打,此后还有母亲的打骂。
但她有自己小小的娱乐。那就是一个人悄悄溜到花园里观花逗鸟,自言自语。乡间半年生活的印记,给了她面对生活的勇气。
庐隐在家没有地位,与婢女同住。由于性情倔犟、无人待见,9岁那年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免费教会学校去读小学。在那里,她的脚长了疮,差点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吐血不止。童年的悲惨经历让她发出“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的声音。
少年:像候鸟一样漂泊
内心好强的庐隐拼命用功,出乎所有人意料考上了高小。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13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家里人开始改变看待她的有色眼光,她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庐隐自传》)
世界从此为庐隐打开了一扇温馨明亮的天窗。
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后,校规很严,但因其年龄小、身材小,处处被同学优待。她和五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开始以少女的顽皮取乐,集体对着一个人大笑,让对方手足无措。到了三年级她16岁时,迷上了小说。
少女也开始怀春。她在亲戚家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他聪明俊秀但读书不多。两人靠借阅小说来往渐密,林某求婚,庐隐母亲不允。庐隐写了一封信给母亲:“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只得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成婚。
1916年,18岁的庐隐中学毕业了。北京女子中学聘她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内心未能安定的她不到一年就找借口辞职了。
1917—1918年间,她应一位女同学的邀请赴安庆任教。在安庆,庐隐认识了日后与她齐名的女作家苏雪林。教书出色的她很快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半年后又回到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她便又到了开封。那里保守的气氛与直率的她不相合,半年后她又回到北京。表姊妹们于是送给她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学期先生。
童年缺爱的人,其实是很难有长性的。
青年:跳跃式前行
1919年秋,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她的天赋才气逐渐得以显现。
苏雪林后来回忆道:“庐隐虽然不大用功,功课成绩却常列优等。她的坐位恰在我前面,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又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操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虽然有许多行动不检点处,始终能得朋友们原谅与爱护,也无非为了这一点。”
大学时的庐隐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祖籍福建的她还被选为女师大福建同乡会代表。此时的她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而未婚夫的平庸显然不能入她的法眼了,她主动提出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苏雪林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她还以“夜雨春蕾茁新笋,霜天秋隼搏长风”之句来形容庐隐当时的文章。“‘霜天’两句形容庐隐文章也觉溢美,不过她那一股纵横挥斥,一往无前的才气,如何使我倾心,也可以想见了。”
庐隐大学毕业时22岁,不久后到安徽一个中学任教。“学期先生”又只教了半年,还说那里复杂的环境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
婚姻:两度惊世骇俗
像候鸟一样跳跃的庐隐却与有妇之夫郭梦良一见倾心。善良的她无意让郭抛弃发妻,在信中她写道:“我们相知相谅,到这步田地,我今后的岁月,当为你而生;不过,我历来主张,人以精神生活为重,你我虽无形式的结合,只要两心相印,已可得到安慰了。”
1923年夏,25岁的她不顾家人朋友的强烈反对,与并未离异的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婚礼。唯有苏雪林为她辩护说,“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很快他们有了女儿。1925年7月,庐隐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她还没来得及高兴,爱人郭梦良因肠胃病突然病逝。身心疲惫、痛苦不堪的庐隐送爱人的灵柩回故乡福州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婆婆处处刁难,连晚上点煤油灯都遭痛骂,于是她不得不从福建再返上海。到上海后,她一身任多职,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在附中任教,继续写作生活。尽管如此,带着女儿的她依然入不敷出。
rcIr+reKsz6uHug/vMJS+uDh69NWFN/01Hv9rRQd66o=那个大学时代满身豪气、大声说话的女子,陷入了生活的泥淖。应朋友之邀,庐隐回到了北京,并担任了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满心文学家梦想的她显然不适合当校长,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第二年,她又辞职,去北京师大附中教书。
“学期先生”后来还曾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一年后又辞了职。在几个朋友的协商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并办了一个《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同时笔耕不辍。她此时创作的小说、散文,大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曼丽》。
此时的她,生活是灰色的: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哥哥相继死去。在病了一场后,庐隐结识了比她年轻的新男友瞿冰森,当时他还是就读于法政大学的学生。但这段短暂的恋情很快无疾而终。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诗人李唯建。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倔犟的庐隐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1930年秋她罔顾一切反对的声音,宣布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行前,她将两人的信件《云鸥情书集》(共68封情书)交由天津《益世报》连载。一年后,上海国光社出版了这本充满狂热情话的书信集。
两人回国后,李唯建受聘于中华书局任职外文编辑,庐隐则任教于法租界工部局女中。生活幸福,她的文学创作也激情洋溢,仅仅在1931年至1932年短短两年间,就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火焰》,还有《飘泊的女儿》等二十余篇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许多散文、随笔。
庐隐说,“我从小就喜欢萍踪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幸福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因此也不长久。1934年,历尽坎坷、只过了几年美满生活的她,就因省手术费在家待产、终因送医太迟离开了这个令她爱恨交加的人世,终年36岁。
一个著作丰富、内心真实的女作家,从此将灵魂留在了文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