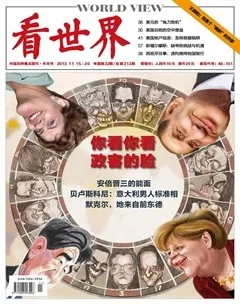纽约访鼎公
国庆期间,在纽约拜访了华文大家王鼎钧先生。老人家今年88岁,人称“鼎公”。抗战、内战、流亡,客居海外,王鼎钧说自己的人生很齐全。这大起大落,沧桑历尽的经历,给了他创作的无尽源泉。在台湾,“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文”;然而在大陆,鼎公的名字还少有人知,若不是三联推出他的简体版回忆录,只怕先生还如隐士一般,大隐于万丈红尘。而我,也是通过龙应台的讲座,听她不止一次非常推崇地提起鼎公,才找来《风雨阴晴》、《左心房漩涡》,进入鼎公的文字世界,也由此萌发采访的念头。
我们相约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家粤菜馆见面,当日飘着细雨,鼎公一身中式坎肩,外面一件格子风衣,站在法拉盛街头,高大魁梧的身姿并不因为年高而减损,依然鹤立鸡群。或者因为听力弱化,鼎公话并不多,但每出口,必字字珠玑,幽默中见真章。也许因为我的职业,鼎公特别对我这个后学晚辈谈起“大记者”和“名记者”的区别。他认为任何时代凡不守规矩、好走极端、爱出风头的,人品道德往往可疑,如民国的名记邵飘萍之类;而像《罗马假日》里派克扮演的那个小报记者,最终没有拿公主的私密照换取名利,他的作为和职业操守就可称作一个“大记者”。大记者和名记者往往如鱼和熊掌一般,不可得兼,大概要终其一生不断努力选择、尽力坚守吧。出生于山东兰陵的王鼎钧,一辈子乡音不改,听着熟悉的家乡话,在纽约这个多元混杂的都会,真有时空错乱之感。
王鼎钧虽然已年近九旬,仍然笔耕不辍。当天的《世界日报》上,刚好就读到了鼎公署名陶铭的文章。问这个笔名做何解?鼎公答,这个“铭”本来是在铜器上的,万世不朽,我这个“铭”是在陶器上,很容易就被打破了。都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说文章就是现在的事,得失众人知。当年《大公报》的张季鸾说过,我们写这些玩意,早晨还有人看看,下午就包花生米去了。所以新闻工作者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机会。有人说过,报纸只有24小时的优势,广播只有1小时的优势,这是大众传播造成的,很快就变成陈腔滥调。文章都是速朽的,都变成陶铭。
然而,鼎公的四部曲回忆录可不是陶铭,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没有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提起如我这一代隔世的沧桑,鼎公说:“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努力只能是文学上的。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
王鼎钧著作等身,在写作上更是“良工式古不违时”,无论小说、散文、评论、诗、剧本,都力求创新、雅俗共赏。由于写过很多怀乡的文章,一度被贴上“乡愁作家”的标签。“日光之下无新事,但普天游子皆怀旧,偏爱旧时天气旧时衣引发一丁点儿旧时的心情。名川大山见许多,天下胜景还是老家东门外的丘陵,岭上一棵石榴树。树失去了,山在;山失去了,地在;地物改,地形变,大地万古千秋。土在即苗在,苗在即树在。斯土斯地得你亲眼看,亲自用脚踏,亲身翻滚拥抱。”《左心房漩涡》里的这段文字,分明读到了他对家乡的刻骨相思。但他自己并不喜欢甚至并不认同“乡愁作家”的标签,他说文学里的故乡,只是一个符号,故乡是虚幻的,它一直在变,故乡也在遗忘你,除非你在外面得了诺贝尔奖,故乡也许会想起你。也许大痛无言,虽然我们在异域的天空谈故乡,但我牢记荒田老师的叮嘱,故乡,是鼎公心里永远的痛。因此,是否打算回乡走走这问题,一直没有问出口。
王鼎钧是基督徒,却倾心于佛法。鼎公了悟佛法,却在作品中不着一字,无沾无碍的境界可望可即,我与鼎公面对,如对得道老僧。许多年以后,我也会记得,在法拉盛的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