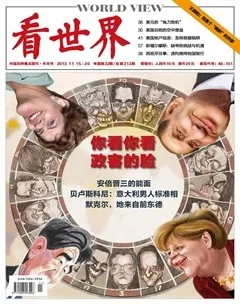方言

1977年前,农村青年要“进城”吃上商品粮,道路不外三条:推荐上大学,做工农兵学员;招工“进城”当工人;当兵当成四个兜,提干转业。这几条道,都不容易走,甚且可谓狭窄坎坷,近于羊肠。譬如吾乡,窝在大别山腹地,至今不脱老少边穷的帽子,跟发达无关,教育的分量当然不重。招工更难,整个新县,“大”企业,也就一家化肥厂,容纳不了几个人,就我所知,整个陈店乡,进化肥厂当工人的,一个都没有。结果,吾乡“跳农门”的道路,只剩下当兵这唯一一条窄缝。
我眼中那威风凛凛的公社司机,当兵转业的;村前岭上那条简易公路上,骑着绿色自行车招摇跑过的邮递员,当兵转业的;在供销社站柜台的,当兵转业的;公社能见到能吃派饭的男性,差不多都有到部队这个大熔炉冶炼的光辉经历。所以,每年招兵,吾乡那疙瘩,从没愁过兵源。不跟公社、大队负责推荐招兵的人武部门有点亲故,不能套点近乎,即使健壮如牛、灵敏如狐,一样报国无门。每年一度的披红挂彩、敲锣打鼓送新,在吾乡就是阵仗很大的节庆。我常常挤在夹道的人群后面,呆呆地望着漆成绿色的敞篷解放大卡,载着换了绿军装还没佩戴红领章的一众兴高采烈的新兵,绝尘而去。只是奇怪,何以新兵的家属,尤其奶奶妈妈们,要抹眼泪,心里难免不屑:婆妈。
话说有位仁兄,侥天之幸,当兵了。入伍一年之后,从“新兵蛋子”混成“老兵油子”(我没当过兵,不敢胡说,借用后来军旅小说中读到的两个有点赞赏色彩的谑称)后,这位仁兄探亲了。回来照例必得先在县城住一晚——这倒不能指责他贪图享受不念亲人。县城通乡下的班车,就一班嘛,还都在一大早,赶不上趟就只能破费住招待所了,好在探亲的旅费,部队早就想好了,周到。
早班车到家时,村子里还飘着炊烟。我们这位仁兄,放下行李,跟灶下生火做早饭的妈打了声招呼,问了声:“我爸干嘛去了?”老娘回答在某块地头薅草呢,你去叫他回来过早吧。仁兄出门,和村里碰到的任何一位婶娘招呼,给碰到的每一位爷们儿递上一根乡下稀罕的卷烟,三步两跳,一路哼着歌儿到了地头。“爸,这紫秆儿开白花的,是啥玩意儿啊?”躬身锄草的老头子一回头,倒握锄柄劈头打来。“哎呀不得了了,荞麦地里打死人了。”“你还晓得是荞麦啊?”仁兄落荒而逃。
这个故事在吾乡腾传一时,“紫秆儿开白花”成了取笑任何一位变腔调者的通用语了。我在县城读了高中,却发现,八里畈、陡山河、千斤、沙窝、卡房等不同公社的同学,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故事。新县虽然人口不多,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村落只能随山走,住得相当分散,不同乡镇之间的横向交流当然不便,也不可能多的。即便每个公社都有当兵的,即便每位兵哥哥都在荞麦开花的时节探亲,也未必碰上听不惯撇了音调的老爹,老爹也不非抡锄头不可,吾乡播种荞麦的时候也不多的。故事的源头应该只有一个,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让人吃惊,传达出来的共同信息就是,对不认乡音这近乎“背叛”的厌恶不屑。
山给交流制造障碍,久处一方,几乎每一镇甚至每一村,都有可资识别的语音变化和用词歧异,外人听来,毫无区别,我们那小地方的人听来,响若闻雷。一开口,浒湾、吴陈河的同学就笑话我们,“蛮子”。我们这些陈店蛮子,又都不会混同郭家河蛮子、箭厂河蛮子、田铺蛮子,更不会跟“蛮得不得了”的湖北红安蛮子们搅成一团了。
到武汉念大学之后,渐渐发现,新县蛮子、红安蛮子、麻城蛮子、大悟蛮子们的口音,差别实在有限,我还能跟九江蛮子用土话交流呢。看来,洪武年间从南昌筷子巷被逼迁徙的口口传说,并非无据。
离家越远,家乡方言的些微界限也就越模糊。社会越开放,方言融入通用语的速度就越快。譬如吾乡,“紫秆儿开白花”的时代,像那位仁兄那样改口叫“爸”的,跟白乌鸦一样稀罕,吃商品粮的孩子的专利嘛,如今还喊父亲为“大”的,基本上都是我这样人过四十天过午的“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