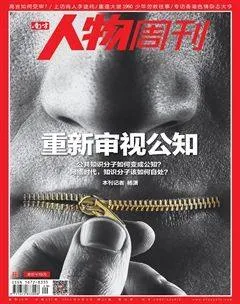更专业?更业余?
知识分子的“业余性”
人物周刊:早在200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一书里,你就提出了,“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看法,反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当时是什么样的研究情境和问题意识,让你有了这个判断?
徐贲:我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和业余性问题的。当时我正在写关于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以美国两位文学批评家为例,其中一位便是萨义德。萨义德对专业主义有许多批评,他所说的“业余”是一种与专业主义相对抗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其中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专业主义不等于学术的专业性或专业;第二,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专业还是业余,涉及到知识分子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如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葛兰西所说的专门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反抗性和批判性等等。我在书里专门用一章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业余是一种与学院体制里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批判姿态。 专业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在知识活动中划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我在中国语境中提出专业主义的问题,是为了不希望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专业主义”而变成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制度内知识分子变成的那个样子。
其实,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专业主义开始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后来才发生了异化,转变到反面去了。
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政治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知识与政治分家,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政治、金钱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让学术归学术”的意义。因此,参与到专业主义中去,开始是一种进步的政治行动,是一种抵制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干预学术的反抗策略。
但是,随着中央集权式统治被体制化控制手段代替,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专业主义的对抗策略也就开始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专业主义也从对政治、金钱的反抗策略转变为一种为“有专业者”自身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一旦他们的自我利益受到所谓专业化体制的保护,当然不想改变现有体制,相反,他们会积极维护这个体制,这也使教育改革变得更加困难。
任何一个在大学体制内端饭碗的人,要批评专业主义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义德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图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要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伊斯兰》(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中他才正式把批评者定义为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他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异议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政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业余者这个说法本来有点以谦虚来自夸的味道,一般的教授、专家根本没有这个本钱。
人物周刊: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受到,甚至微博上也开始相关讨论,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开来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
徐贲:我觉得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精,所以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样。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中国人把“业余”理解为“降低标准”是因为不大有机会见识高水准的业余。捷克人在家里跟朋友一起演奏室内乐,就像我们国人在家里打麻将一样,虽然是业余,水平是一点不低的。
人物周刊:萨义德提出用“业余性”(amateurism)对抗“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压力,他认为专业主义在今天对知识分子造成特别的威胁,让知识分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在你看来,他描述的这种威胁多大程度上也在当今中国存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徐贲:是存在的,那些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把它说成是了不起的独家擅长,不过是想奇货可居而已。
不话说回来,一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专业主义一无是处。专业主义的好处是起到“拉平”(equalizer)的作用,不是拉平起跑线,而是拉平终点线。以前,学问的高低与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极大关系,受“幸运”因素的影响特别大,谁如果幸运地能从小在家里学好两三门外语,广泛涉猎中外古今的书籍(并不需要读得太精),就能比没有这个条件的同龄人占先许多,因为少年时代没学到的东西以后一辈子花大功夫也未必能学好。你去看看西南联大的那些名教授,差不多都有这种起跑线优势。在古代那就更是如此了。西塞罗少年时代,罗马已经有了拉丁文的修辞学校,但他还是一定得到更高级的希腊文修辞学校去学习。昆体良跟名演说家阿弗尔(Domitius Afer)学习修辞。他们的资质当然都很高,但能在同代人中鹤立鸡群,又何尝不是因为赢在起跑线上?

有了专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没什么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小学、中学、大学一路上来,把课堂里的那一点功课学好了,考上研究生,把硕士、博士学位拿到手,得到个大学里的职位,升到教授、博导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叫按部就班、水到渠成。在这个终点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每个人都是专家,他们安守一隅,兢兢业业,在专门知识的范围内授业解惑,是大学里最适宜的劳动力。办了那么多大学,招收了那么多学生,要想每个教室里站一个像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根本就不可能,再说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学生的知识量和知识面就这么一点,他们上学也不过是为将来在劳动市场上找一碗饭吃,并不是要当什么学问家。这种时代的变化,不是知识分子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1930年代,著名作家艾略特(T. S. Eliot)嫌大学生素质太差,建议把大学生人数砍掉2/3,也不过是说说气话、发发牢骚而已。今天的大学生比那时候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没有专业主义下培养出来的大学教授,一大半的大学都得关门,这么多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上大学?专业主义至少还有这点好处的。

“专业”与“业余”之争
人物周刊:在学科与知识越来越细分的今天,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他们不够专业。总体上,您对当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市场”有何判断?是否同意一些人所谓“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的说法?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看待“专业”与“业余”的关系?
徐贲: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够专业是个事实,但不一定是一个缺陷,当然能够专业一些会更好。其实,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是像西方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的人物,如爱因斯坦、加缪、萨特、乔姆斯基、桑塔格,科学家卡尔·萨根,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萨义德。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职业特征和公共活动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国家里,“公共”的含义并不相同,这与公众关心怎样的公共问题有关。不同的公共问题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一般中国民众对公共问题的理解比美国人狭窄和专一,主要是像民主、公民权利和自由、宪政法治这样的问题。许多社会权利的问题,如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子女的教育机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环境保护的要求等等,也都是“公共问题”。
讨论和批评这些问题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波斯纳或其他研究者所说那种特别有专业造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正直、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公民”。这样说决不是要贬低他们的社会贡献,而是要强调他们在中国的特殊贡献。美国革命前,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个鞋匠,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称他“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公民,他先于美国共和而出现,是一个呼唤和帮助共和诞生的思想者,一个美国革命的助产婆,一个在精神、人格和心灵上自由的人。潘恩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须用知识分子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人物周刊:“提高公共言说市场的质量”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目标?与之不无关系的问题是,怎么看待公共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社会事务发言者的“大嘴巴”乃至“信口开河”?
徐贲:一个知识分子从专业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可能是很缓慢的,但一定要知道,随着自己角色的变化,责任的程度也在增加,而最大的责任则是当他越出自己专业范围表达意见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看法会不周全,观点会有偏颇,也要知道,无论说什么、写什么,都必须为之承担良心责任的后果。负责任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基本要求,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事务发言者都不应该“大嘴巴”和“信口开河”,都应该在公共参与中谨言慎行,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最难得的美德:审慎(prudence)。负责任不只是指尽可能的周密思考、理性表达,而且指对自己说出的话有所担当,不能只顾一时说话痛快,今天这么说,明天换个腔调,变来变去,改变立场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定要向公众交代改变的理由。
“公知污名化”的背后
人物周刊:在“公知污名化”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根源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的缺陷”,比如欠缺社会科学分析框架、逻辑缺失、煽情泛滥等等。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徐贲: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你告诉我一两个具体的人,也许会好谈一点。这些“根源分析”显然不适用于我所知道的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泛泛而论、以偏概全本来就是一种抹黑的手段,而不是理性讨论的方式,所以,除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不必对它太介意。
不过,专门知识有助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质量,这也是真的。问题是,那些可能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学专门学识的,他们不出来说话,那怎么办呢?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不然岂不是连一点异议的声音都没有了?所以有人以前说,中国的教授们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韩寒,这不是韩寒的光荣,而是教授们的耻辱。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是公共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言论质量如何,都至少有两个“门槛”,分别是学术和良心勇气。在中国,发表某些公共言论经常是一件与言论者自己的利益过不去的事情,因此需要准备付出个人代价的良心勇气。许多“学术成就很高”的人正是因为顾及自己的利益,才对不良现象保持沉默、顾左右而言他,或者首鼠两端、曲意辩护。他们的水平是很高,但又怎么样,他们不愿意当公共知识分子啊。与其抱怨说话的人水平不高,还不如直接呼吁,让那些水平高的人站出来说真话吧。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发聋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现在中国“顶级”作家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奉行莫言原则,装聋作哑、置身事外,不愿意出来当“牛虻”,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人物周刊:还有人认为“公知污名化”应主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国内环境,比如说,被泼脏水,又比如说,中国现在的文化氛围是民粹和反智的,等等——有趣的是,美国也是一个可以说有“反智”传统的国家,可否对比一下中美公共知识分子的境遇?
徐贲: 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作用是对民众启蒙,启蒙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民主公民启蒙,另一个是人文启蒙。至于哪一个比较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去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环境决定的。知识分子做什么事,离不开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怎样的启蒙?这不只是主观的选择,而是决定于具体的境遇。
中美境遇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特别关心民主、法治的启蒙相比,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很少直接涉及这些问题。他们关注得较多的“公共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过是一般的“文化问题”或者根本就是“人文学术问题”,如文化歧视、女权、动物和环境保护、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例如,著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写文章,向民众介绍科学的意义,讨论科学与文化和与宗教的关系;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向民众介绍人类基因的“双螺旋线”(Double Helix);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讨论人类智能进化的《伊甸之龙》;理论物理和数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向有志于科学的青年读者介绍自己科学研究经历的《打扰宇宙》,这类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在美国还有很多,更不要说像乔姆斯基、萨义德、桑塔格那样的人文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了。放在中国,这些都是学术,根本不会当作是公共知识分子事业。
相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抨击腐败、要求社会公正,或有关干部裙带提拔、官员戴什么名表,甚至批评地沟油、牛奶品质、拖欠农民工工钱、随意拆迁、大吃大喝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这根本就是普通报纸记者和民众来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必知识分子用专门学问来说明的深刻道理。
只有在民主启蒙有了成效后,才会需要和有暇进行程度更高的人文启蒙。这是一种特别需要有专门学识的知识分子来帮助实现的启蒙。在一个在政治、社会制度形成高度民主法治共识的社会,人的精神、人性、心灵、文化、修养等等都会变成公共问题,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问题”。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有相当的学识、见解、文化素养,是知识分子所擅长的问题。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许多知识分子自己都搞不清这些问题,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对一般民众谈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