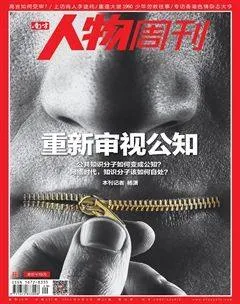时代精神
到住处时已过午夜,谨记中介之前的反复叮嘱(“扰邻是要赔钱的”),蹑手蹑脚提着箱子开门、进电梯、再开门,生怕发出一点声响。公寓比想象的要好,连浴巾和手帕都整整齐齐备了好多条,客厅里的假树萎靡得很真,我差点就给它浇水了。
这里比北京慢12个小时,头两个晚上都是凌晨两点以后入睡,4点多就醒了,像是睡了一个绵长的夏日午觉,窗外风凉,枫树和梧桐在黑暗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打开电视全是购物节目,我鼓起勇气从九百多个频道里寻找BBC world service,想通过看新闻找到自己在陌生世界的坐标,却只发现BBC America,它在播放烹饪节目。后来我又看过它几次,好像每次都在教人做菜。
熬到6点,出门吃早餐,经过了一个五星级酒店、两座教堂和一块墓地后,居然摸到了哈佛广场。人最多的Au Bon Pain门口,风度翩翩的老人家微微鞠躬,微笑着说了声ni hao,我一进门就明白了他为何那么确定我是中国人:餐厅里有一半人是操着各地方言的同胞,哈佛还有两周才开学,也不知是亲友团还是旅行团。
通过搭帮朋友的介绍,周末混进几个北美留学生社团举行的论坛,连听三场演讲。B先生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10年,从李思怡到太石村,从最牛钉子户到邓玉娇,听得我唏嘘不已——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但又感觉如此遥远。2003年有时被称为“民权元年”,记得那时候社会有共识,大家心气颇高,觉得众人推墙墙必倒,而今墙仍是墙,人也未必不是墙,就像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里写的:“……不仅是某些官僚程序,而是整个文化语境;不仅是国家的干预,而是所有合谋摧毁自主的真正艺术行为基础的情形;不仅是政治勒令,而是一元化社会里的个人的世界观;不仅是‘合法’与‘非法’的限制,还有维系着国家权力能够渗透到文化的哪怕最后一个细胞的秘密心理源泉。”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它可能是眼界也可能是局限。在哈佛教课的R老师说,你们这一代受汶川地震影响很深,所以对郭美美事件反应很大——有趣的角度,倘若一个外国观察者空降中国,他能够打开我们话匣的问题之一肯定是:2008年5月12日那天你在做什么?而塑造R老师那一代人的却是更早之前的悲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关切,不妨想象我们的下一代问我们:汶川地震真有那么惨吗?
R在课堂上运用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来辨析教育、传媒、同龄人、家庭等媒介(agents)在不同社会起的作用,从而对年轻一代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产生的不同影响。这并不是高深的理论,但能带来很清晰的分析——你或许听过一种熟悉的说法,“在哪里都是被洗脑”,或者,“他们那个也是一种宣传”,那就来看看这些媒介在不同社会的状态吧,它们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是被一个权力中心控制还是被若干个控制?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对任何事情做出判断前,你是否会意识到政治社会化对自己的塑造?
参加论坛的人价值观比较接近,不过他们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大概也是少数派。一个社团发起人在自己学校做的小调查说,大多数参加社团活动的留学生同意对政府的批评,但也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有损国家形象”,只有极少人对异议者表示同情。最后他总结,希望培养更好的讨论气氛,希望吸引到更多本科生,以及,“更多女生!”然后一屋子男生都大笑起来。
活动结束,大家一起看了部介绍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纪录片。吉恩就住在波士顿,以倡导非暴力抗争理念闻名于世。片名叫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我之前没听过,用手机Google,敲到how to start a时,下拉框提示出现了how to start a business(怎样创业)和how to start a conversation(怎样聊天)的句子,我继续敲打,到how to start a re时,以为差不多了,结果出来的是how to start a restaurant(怎样开一家餐馆),这才是时代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