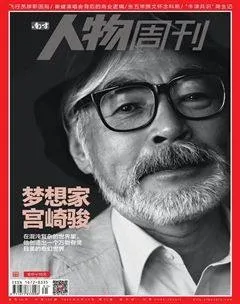卡明斯基 失去听力后,我开始看见声音

诗歌的“音乐疗法”
面对乌克兰裔美国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你不相信他有36岁。一张娃娃脸,天真的大眼睛,孩子般的笑容一下将你融化。“我宁愿做童年的公民。”
黑棕色卷发下架着圆框眼镜,加上他1米98的身高,巨人版“哈利·波特”就这样出现在眼前。不管坐下站起,卡明斯基的脖子都习惯性前倾——因为他听不见,交流都靠助听器。
我的秘密:4岁时我耳聋了。失去听力后,我开始看见声音。……(摘自《舞在敖德萨》)
《舞在敖德萨》是卡明斯基的第一本诗集,甫一出版便斩获美国6项文学大奖。“这位年轻诗人为英语带来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以及茨维塔耶娃的遗产,但同时他的诗歌语言同明天的广告语一样新鲜,同民间音乐一样令人感到熟悉。卡明斯基的想象力是如此具有蜕变性,令我们的共振带有同等的悲伤与欣喜。”(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麦卡夫奖授奖辞)
4岁失聪,16岁流亡美国,27岁,他就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
在一座被鸽子和乌鸦联合统治的城市,鸽子盖满了主要地区,乌鸦占据了市场。……
1977年,卡明斯基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那是一座海港城市,有鸽子和乌鸦,有剧院和音乐厅,每个人都喜爱跳舞,还有西红柿和烤鱼。
卡明斯基的父亲维克特有段坎坷童年:父亲被斯大林镇压枪毙,母亲被判刑20年,遣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古拉格)挤牛奶,维克特被送到孤儿院,他的奶奶从一列一列火车顶上跳过,穿过大半个俄国,把一岁的维克特从孤儿院里“偷”了出来。
祖父母的苦难后来被卡明斯基写进诗作《赞美笑声》:
我祖父写的讲义,有关云彩在我们国家的/需求与供给:政府宣判他为人民公敌。他兜着西红柿追赶火车,在我们家房前的桌上裸身跳舞——他被枪毙,我祖母被强奸,公共审判员用钢笔插进她阴道,那支钢笔给人民判了二十年。但在秘密的愤怒史中——一个人的沉默/活在他人的身体里——我们跳舞而不至于倒下……
卡明斯基4岁时因医生误诊而失聪。在他的诗中,“医生”同“审判者”一起出现,但没有怨恨的字眼,他甚至可以爱上医生的孙女。他的童年比常人孤独,“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4位数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声音,那个神奇的东西,鸣响4年之后戛然而止。
卡明斯基的父亲维克特后来成了富有的商人,乌克兰经济萧条后却破产了,又遇到“排犹”浪潮,于是把全家弄到美国。16岁的卡明斯基,很早就体验到流亡的滋味,但他完全同意布罗茨基等人对“流亡作家”的嘲笑,他说他最看不起“自我怜悯”。
“我并没有生长在一个宗教家庭里,直到有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说‘肮脏的犹太佬’,我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我这样说并不抱怨什么,这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在华盛顿的犹太博物馆,他第一次看见关于他母亲在集中营的照片和记录,有些震惊,但并没有沉溺于仇恨。正如他以诗歌所宣告的,“我必须赞美/最黑暗的日子。”他赞美失去听力,赞美失去祖国,赞美睡眠,赞美活着,“谁知道自己明天能否醒来?”
去美国之前,卡明斯基从未戴过助听器。儿时他读童话,读巴别尔的小说,读布罗茨基的诗,12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诗与散文合集《被保佑的城市》,人称神童“小布罗茨基”。
刚到美国时,他一句英文都不会,接触到第一首英语诗是史蒂文斯的《十三种看黑鸟的方式》,他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我一下感受到英语明晰、精准的魅力:它很节制,却充满各种可能性。”
他继续用俄语写诗。第二年父亲去世了,他开始用英语写诗,“用他教我的俄语来写关于他死亡的诗,为之写出‘美丽’韵律,我做不到,我知道这样会伤害我的家人,用某个人的温暖气息来写出一种气息,而这个人几天前还在我旁边,这样做我感到是一种背叛。”
他决心“以新的语言来悼念父亲”,自那以后走上英语诗歌创作道路,谁料一写就停不下来,2002年小诗册《音乐疗法》一问世即获好评。2004年出版诗集《舞在敖德萨》,美国媒体评价:“同他之前的布罗茨基一样,卡明斯基好得可怕,又一位来自前苏联的诗人,拾起英语,使我们母语者感到羞愧。”
卡明斯基把诗歌称作“音乐疗法”,他在诗中插入散文、杂文,甚至——“两汤勺黄油、一杯纯酸奶、一枚洋葱(切碎)、一个大蒜……盐和胡椒”这样的菜谱!“我父亲生前擅长烹饪,我在诗中加入最爱的‘冷薄荷-黄瓜汤’菜谱,就像是在诗中和大家打个招呼,因为里面有我的个人经历。”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上,卡明斯基和诗人萧开愚、翻译家明迪等进行了一场对话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他的朗诵仿佛是一种嘶喊,词句从他胸腔里迸出,令人震惊——那个无法正常听到声音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
卡明斯基给他下一部诗集取名《聋子共和国》,那是一部童话诗,“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聋子。 ”

写诗就和回到童年一样
人物周刊:您养的那只猫叫什么名字?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和生活?
卡明斯基:好问题!事实上,我以前养了3只,现在剩下两只,去世的那只叫Pandora(潘多拉),是只母猫,很遗憾,她因感染跳蚤而死。活着的另外两只,一只公猫叫Rooster(公鸡;狂妄自负的人),因为他大清早就把我们弄醒。在美国,每个人大概会说100万个Rooster!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白猫,我们叫她Lady Bird,英语民歌里唱过,越战期间任职的约翰逊总统的夫人也叫这名字。(大笑)
我从猫咪那里学到很多,它们教会我许多重要的事:睡眠比工作重要,晒太阳、闲庭信步很重要,政治没那么重要,而且它们很优雅,有个说法,狗恋上你,猫恋上你的大房子,同在一个屋檐下,猫教会我:我并不是这个屋子里最重要的生物,呵呵。
人物周刊:您的童年是怎样的?
卡明斯基:我的童年是怎样的?我已经到了悼念童年的岁数了?不,我还住在童年呢!
童年永远是新鲜的,充满各种气味和音乐,拒绝看见死亡,一旦你看见死亡,你就是成人了,我拒绝成人世界。对我而言,童年是一生中结合叙事与抒情的时光,我们都喜欢听童话故事,而童年本身就是抒情的,所以写诗就和回到童年一样,抒情和叙事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孩童的状态,但需要存留孩童的视角。
人物周刊:4岁失去听力前,您最强烈的听觉记忆是什么?
卡明斯基:我得想想,这大约和我偷吃苹果的经历有关。记得我小时候奶奶喝茶,遵照俄罗斯人传统会把苹果片放在热茶中,而我经常去偷她茶杯里的苹果片,我至今记得那片苹果掉落水杯“噗”的一声,然后就被发现了。我这坏男孩,是吧?
人物周刊:你后来写下“失去听力后,我开始看见声音”。
卡明斯基:我想说的是,当你听不见别人说什么时,你便开始关注人们说话时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我给你举个例子,当你把只会说自己母语的中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放在一个房间4小时后会发生什么?Nothing!因为他们不理解彼此。但你若把3个聋人放在同一个房间4小时,你会发现他们彼此可以深度交流,因为我们的肢体会说话。
杜甫的《春望》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人物周刊:听说您很欣赏中国的唐诗?
卡明斯基:1992年,苏联解体前夕,我在旧书店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首杜甫的《春望》,这位远方诗人用这么短的一首诗向我这14岁的异乡孩子讲述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同时我也理解了我所处的时代。
这首诗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尽管当时俄语译本并不完美,却让我这个在黑海边长大的孩子感受到这位伟大诗人在同我进行一场极其个人的隐秘交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他写随自然变化你我都会有的那种个人感触,但同时他又写出了那个悲壮的大历史时代,某种角度而言,甚至连俄国诗人都没能描述出这种感受。
杜甫的诗启发了我,因为苏联经过许多历史灾难直至解体,如何写出这种大时代下的黑暗,但又不是使用那种过分政治的口吻?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对一个诗人而言,只有当诗歌语言美妙到足以同众人进行一对一隐秘交谈时,诗作才变得具有公众性。一首诗相当于一次握手,唐诗教导我住进隐秘的个体经验中。
我很喜欢唐朝诗人,他们如此不同,构成那个时代辉煌的文学,李白是欢欣的,而杜甫是沉郁的,有趣的是他们还互相认识,杜甫写了很多诗给李白,李白我想就写了一首给他吧?但我觉得这种交流非常有意思。还有王维,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在真实生活中如此跨界,艺术与诗彼此影响,对我而言,这非常神奇!
我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很有限,但我不只对李杜、王维他们感兴趣,而是对中国整体的诗歌文化感兴趣,例如孔子,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的编撰者,所以从那时起,你们的核心文化就和诗歌并肩而行,而且行进了几个世纪。在我印象中,你们的官员都需要通过科举考试,都会写诗,这在俄罗斯简直不可想象,美国也是这些年诗人才可成为大学教授,但在我记忆中,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已经有这一传统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
卡明斯基:我看到的是一个全新世界,一个多样化的中国诗坛。今天你问美国学者对中国诗歌的看法,他们多数还是会和你说朦胧派,朦胧派的确重要,我也很喜欢,但还有很多其他作品。
美国文化很关注名人,他们喜欢北岛,因为他是大名人,但当我们只聚焦于一个人的创作时,就忽略了全景和多样性。历史上新诗始于民国,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当代,写了近一百年的诗,他们不是只写一个年代,而是不同年代。
我觉得北岛的诗歌总体上是因为政治历史背景而产生影响,就像布罗茨基之于俄罗斯。布罗茨基说,我不写政治诗,我对政治不关心,我要过远离政治的生活,但这本身就很政治。同样,朦胧派说他们不追求意义,事实上却带出了许多意义。但是中国目前还在前进,我们要看到这个纵向的历史,横向除了朦胧派还有很多不同的诗歌团体,我希望英语世界不只关注朦胧派诗人,也关注其他各种声音和感知方式。
人物周刊:听说您父亲认识布罗茨基,您对这位诗人前辈如何评价?
卡明斯基:布罗茨基就像一个文化符号,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在美国很知名,但其实他作品的英译本并不好,所以人们欣赏他的散文胜过他的诗歌。事实上,他用俄语写作的诗歌非常棒,他以各种方式改造着俄语。有个笑话:当他在瑞典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排着长队问他索要签名,一个老头上前问他:“布罗茨基,你为什么那么自傲?和其他俄国作家相比你有何特别?你不在俄罗斯那么长时期,你为俄国文学又带来些什么?”你知道,那时有上百人在现场,人们等待布罗茨基的回答,一分钟后,他只答了一个词:粗野。
这虽是个笑话,但却有深意,布罗茨基追随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高雅,然后将这些语言带到平民话语系统中,他所做的是将平民化的语言与诗歌创作技巧相融合。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死亡?
卡明斯基:就像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一个事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觉得作为诗人,创作每一首诗时,你都要当作你生命的最后一首诗来写,这样它才具有某种意义。我认为是生活创造着我们,而死亡就像一面镜子,帮我们看得更清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