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典与志业
从小到大,我都爱看日本漫画。小时候喜欢科幻侠义,长大后口味变了,新宠是讲述主角从少年开始投身某行业,从低做起、奋发向上的故事。这些漫画都做了很扎实的研究,对相关行业的运作、细节和诀窍了如指掌,并作出深入浅出的描述。
以《将太的寿司》为例,它从如何做好一盘简单的寿司饭开始,再到慢慢认识不同鱼类、海产和食材的特性,最后到不同寿司的拿捏和烹煮手法,娓娓道来,讲述主角如何从基本功开始,一步一步打稳基础,最终成为行业大师。
类似故事也成了电影素材,例如前几年的《礼仪师之奏鸣曲》。男主角本来从事大提琴这个优雅行业,因失业被迫做了殡葬礼仪师。起初他十分抗拒这份“死人工”,受尽亲友白眼。但慢慢地,男主角从殡葬细节中,体会到对先人的尊重,领悟到礼仪当中独特的东方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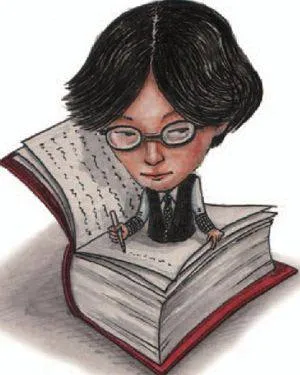
这些故事最让读者感动的,是看到日本人对专业的执着和坚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一志、精益求精,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过程中散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与不少人的得过且过,形成强烈对比。
说到敬业乐业,从单调、沉闷、枯燥的工作中,领略出专业的学问,甚至美学,让我想起近日看过的另一部动人电影——《编舟记》,关于词典编撰的日本电影。
上期谈到在古代,一些传教士,学识渊博又心无旁骛,在严格修行中,锻炼出坚强意志、坚忍耐力,对于单调、枯燥、艰巨的字典和辞典编撰工作,无疑是理想人选。
或许大家会问,如今还会有哪类怪人,奉献青春,传承文化历史,去制作一部辞典?片中答案,是个书呆子。
男主角是语言学硕士,文字修养深厚,却也是宅男一名,只懂得与书和文字交往,与人交往时,舌头打结,手足无措。同事午饭时与女孩子嘻嘻哈哈,惟独他拿着书本专注阅读。最初在出版社当推销员,对于口齿不灵的他来说,完全是件苦差,到书店推销新书时总遭奚落。后来因缘际遇,调到辞典编辑部,同事嘲讽他说,一眼望过去,便看到他一副字典相。起初,男主角仍诚惶诚恐,甚至做梦也梦见自己在大海中,对着一页又一页水上漂着的词条,载浮载沉。
但是他的宅男个性,其实与辞典编撰工作十分匹配。编撰小组原本有位型男,但坐不住,不断埋怨工作苦闷。男主角不善交际的性格,却让他能够做好十分刻板、枯燥乏味的文字编撰、校对工作。结果,这个与前述贺神父一样,缺乏生活技能、要靠房东婆婆看护的宅男,却成了一位很好的辞典编辑。
上期提到《利氏汉法辞典》用了半个世纪,片中辞典《大渡海》用了15年,其中酸甜苦辣,一样不足为外人道也。电影把制作过程刻画得很细致,例如逐张制作浩如烟海的词汇卡,为每个字词撰写定义。
电影刻画了老派日本人对专业的执着与坚持,例如新来的时髦女编辑,为了迁就配图而把文字删减,被老主编发现,立即指出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求她改正。此外,词典的噩梦,便是经反复校阅后,仍有纰漏。因为已进入制作的最后阶段,只是小小一个纰漏,换了我们,多半会睁只眼闭只眼蒙混过关,但男主角却决定从头再校对一次。因为此事,卧于病榻之上的老主编没等到辞典呱呱落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男主角并不后悔。
片末,辞典出版酒会,其他人对辞典大功告成如释重负、喜气洋洋,惟独男主角与辞典编辑部的一位前辈,仍患得患失,未敢松懈,不约而同拿出口袋里的词汇卡,相视而笑,说明天便开始为辞典编修订版。“辞典编辑没有结束的一天”,这就是对一份志业的态度,无休无止,生生不息。
我记得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笔下曾经有如此一幕:“尊敬你的老板,热爱你的工作,接受你的人工,那么你死后,便一定会升天堂——因为你活着的时候,根本就是在地狱。”
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工作观,很少人把工作看成一种志业,只当成赚钱糊口的手段,而不是一种修行、一种追求极致、一种自我实现。
这也是这部电影讲述的这个热爱文字、文化,对工作执着坚持、追求极致的故事让人感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