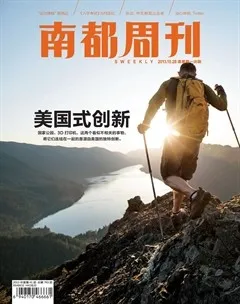士大夫遇沮则退
明朝弘治十一年三月,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内阁首辅刘健被人告了。告状的是一位大学生,即国子监的学生汪某,他告李东阳和刘健,“杜绝言路,掩蔽聪明,排抑胜己。”要求皇帝将这两个人“急宜斥退”。
大学生小汪的告状奏章,作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东阳和内阁首辅的刘健,即便是有机会先看,也不敢扣压阻止。按照制度,这份告他们的奏章顺利地到达皇帝手中。刘健和李东阳也不能对大学生打击报复,而是要到皇帝面前陈情申辩。他们说:最近不少官员和知识分子告臣等的状,私下议论臣等,说我们只顾自己当官,巴结权宦,勾兑利益等等,这些告状的说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类多可采”,因为我们在朝廷这个重要位子上,官场所有弊病的责任理所当然应当由我们承担。我们自己检讨,错误主要在于“因循将就,苟避嫌疑,不能力赞乾纲,俯从舆论”,让朝野如此议论纷纷,这是我们失职,请求朝廷罢免我们并追究我们的责任。
其实,李东阳和刘健不是没有作为,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扛持,国事才没有更糟糕。当时,明朝有三个很能干的大臣,除李东阳和刘健外,还有一个谢迁。刘健稳练端正,谢迁刚直豪爽,李东阳温和多智谋,弘治帝对他们非常信任,见他们都尊称先生,不敢怠慢。
现在出来一个大学生告状,朝廷总得有个交代,不了了之反而更引起朝野议论。皇帝为了安抚大臣,让锦衣卫将小汪抓起来问罪——明朝皇帝脾气都不好,动不动就抓人。
刘健和李东阳赶忙紧急上奏章,两个人全力营救小汪。说我们大明朝不能没有小汪这种大学生,他告状所言,未必全是实情,但是,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敢对朝臣提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正是国家之元气所在也。千万不可给他治罪,否则会杀伤天下士子之心啊!臣等在朝中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了。弘治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将小汪释放了。
后来的明武宗任用宦官刘瑾,自己放纵游乐,李东阳等拼死力谏,极陈“嬉戏废政”之弊,武宗不听,刘健、谢迁跟皇帝争执,将桌子都掀翻了。明武宗还是不听,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请求退休回家。他们说:“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我们不干了,干不了了。
刘健、李东阳被一个大学生告状,尽管告状的内容并不属实,但这两个人就要求退休了,而不是通过手段和关系摆平此事。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士大夫为人处事的特点是“行己有耻”,遇沮而退,而不是没脸没皮,忍耻求进,潜身缩首,苟图衣食。
从前的读书人,寒窗苦读,走科举求取功名,能成功考中的人是很少的,能考中后入职做官的更少。尽管这样不容易,但是很多读书人好不容易考上了,也当官了,没几天,自己又要求退休回家,不干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朝陕西高陵人吕柟,状元出身,一辈子为官治学,为人处事,皆以希贤希圣为宗旨,当官数次辞职;皇帝数次起复请他再当官,他又提意见,又辞职,如此反复多次,最后终老关中老家。
就是说,你让我干,我就按道理干;你不讲道理,我就不干,哪怕我饿死也不干。吕柟的道德文章,行为事业,为天下楷模,名声远播,当时自称“小中华”的朝鲜国给明朝皇帝上书,请求赐给一套吕柟先生的文章,为其全国教材。
当官很不容易,可为什么遇沮则退,不珍惜自己的前程?如果用那种神逻辑“别人是禽兽,我没禽兽不如就不错了”,博得皇帝和上司的理解同情,保禄固位不好吗?不行!当时权宦刘瑾就是吕柟的关中同乡,他却备受刘阉打压排挤和迫害,按照世故的价值观,吕柟太执拗了,太不会来事儿了,其实你拜访一下刘瑾,吃顿饭、唱个歌、弄个书画笔会联谊联谊,就好了嘛。这在吕柟和他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真正的士大夫根本就不具备丝毫蒙混世事的“贱商”。
因为他们有廉耻之心。今天的人思维贪惰,以为一建立某个制度就会万事大吉,总希望浩繁纷乱的政事人心,有一个阀门,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冀毕其功于一役,忽视人廉耻之心的培养。其实,制度再严密,人没有廉耻之心,都会钻制度的空子,慢慢将空子扯成豁口,最终致使制度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