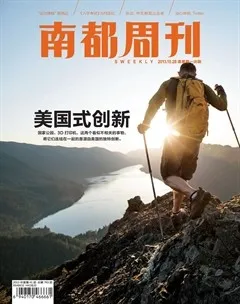葛亮:从南京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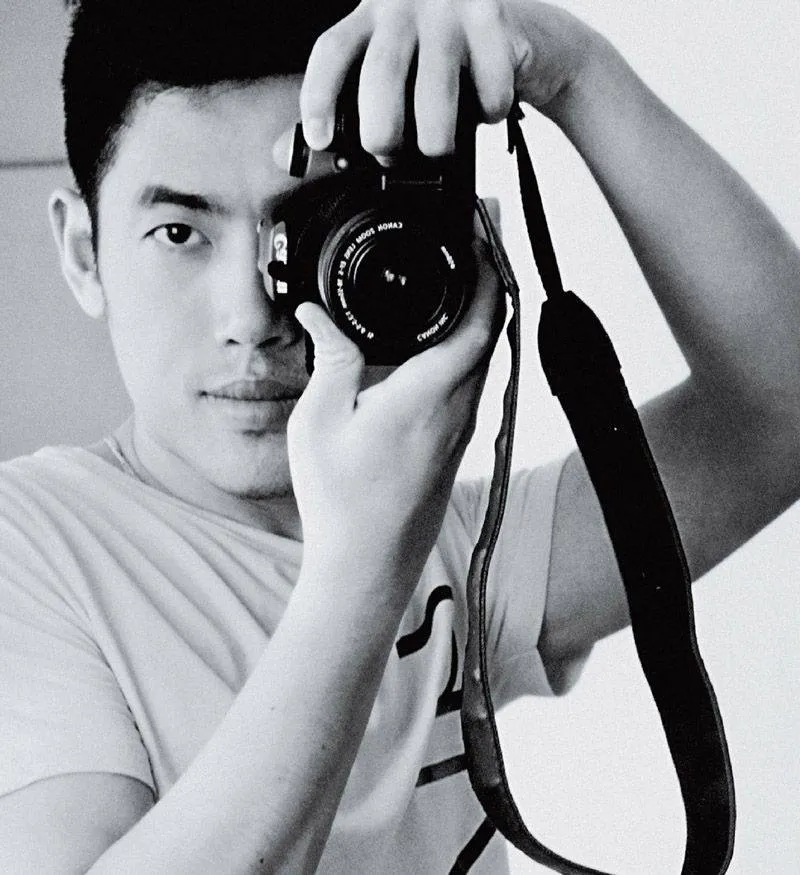
来自家族的文人气息
上世纪40年代初,时局动荡,葛康俞和陈独秀一同避难四川江津。陈独秀是葛康俞之妻的舅舅,一直以来关系密切,葛康俞经常去看望花甲之年的陈独秀,两人高谈阔论。聊到兴处,陈独秀曾录了一首诗送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葛康俞痛切地为其墓碑亲自手书“独秀陈先生之墓”七个大字。之后,在抗战的炮火中,最初在陈独秀影响下开始研习书画的葛康俞,在江津潜心完成了艺术史论著《据几曾看》。1952年,年仅41岁的葛康俞也跟随陈独秀而去。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香港,葛亮经常会想起葛康俞的这段经历,葛康俞和陈独秀正是他的祖父和太舅公。除了陈独秀,葛康俞还有一个著名的表兄弟,也就是葛亮的表叔公—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如今,葛亮作为青年小说家已声名鹊起,很多人谈到他时都津津乐道于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家世。在葛亮的简介中通常写着“原籍南京,现居香港”,实际上他的祖籍是安徽安庆,葛、陈、邓正是安庆的三大家族。这种祖辈的渊源让年轻的葛亮散发出一种难得的古典文人气息。
由于祖父英年早逝,葛亮对他的印象更多是从父亲那里得来。同样有着士子之风的父亲对他的切身影响更大,带他听昆曲、逛画廊、淘古书,指导他阅读古代笔记、俄国小说,给他讲祖父的故事。而他后来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带着敬仰和向往,穿越时代,像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流抵达祖父。
某种意义上,葛亮的确把祖父作为源泉,视为他为人为文的一个尺度。祖父作为离他最近的历史身影,使民国也变得有温度。他曾说,祖父给他最大的影响,是祖父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他很喜欢的,不是所谓的民国风月,而是那个时代的人。
“虽然有些事情是我祖父身后的事情,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和友人之间的交往,是十分深厚的,不是一时一地,真的是一辈子的朋友。”葛亮说,十年前祖父遗著《据几曾看》的出版,就是祖父的好朋友王世襄一手促成的。多年来,《据几曾看》在国内出版遇到难度,因为葛康俞当时品评过的很多书画真迹,1949年都被运往台湾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了。出版这本书,涉及到图片使用版权的问题。后来王世襄亲自跟台北故宫交涉,花了大量精力才使这套书顺利出版,“可以说是王爷爷玉成了此事”。
葛亮也经常会翻阅祖父的手稿,包括他和朋友、同仁之间的一些信札。葛康俞的手稿是那种清晰的颜体小楷,祖父那种独立于时代之外的认真,或者说对自己文字的珍视,让葛亮觉得特别不容易。
“我的写作实际上比他容易得多,为什么不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做呢?”
迷恋历史掌故
今年8月18日上午,在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的佛山主会场上,葛亮刚刚举办完新作《浣熊》的发布会,并与阎连科进行了一番对谈。初次见面,葛亮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快言细语、温文尔雅的人,显得非常有礼貌、有教养。
谈话是从《世说新语》开始的,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我很喜欢那种节制的叙事方式、经典的叙事态度,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人性和事物最本质、最内核的部分,对我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葛亮说,他喜欢读的还有《东京梦华录》、《阅微草堂笔记》等。对笔记文学的深入,给了他两大影响:一是对人物的勾勒,二是在写作涉及到历史背景的小说时,非常重视掌故感。
葛亮有一种对旧事物的迷恋,这种掌故感,就和历史、文人传统息息相关。相对于现实,他更喜欢书写历史,特别是民国。因为民国虽然也进入到了一个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但仍保留很多完整的传统的东西,保留了一种中国风骨。这种风骨在今天已经慢慢剥落。而如果纯写古典的东西,似乎和现在的读者又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在写作题材上,葛亮觉得民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在聊 《浣熊》之前,他谈到正在写作的一个长篇小说,讲的是民国时期一个士绅家族和一个民族资本家家族联姻的故事。在这条主线中,涉及诸多社会风貌、历史人物。比如写到当时的北伐,涉及一系列军阀之间的争斗,包括奉系、直鲁联军和北伐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会提到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最近他的小说写到一个部分,关于当时主要盘踞在天津的一个军阀褚玉璞,写到关于他的很多故事。
“我就想怎么从一个当下年轻人的角度去再现一个历史人物?这种掌故感能够帮助我比较快地进入到历史的情境中间去,去把握他作为一个人物的精髓。”葛亮说,有时候一个人物被书写或述说得太多,多多少少会对后人的诠释产生影响,而他自己对掌故感的迷恋,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他写作或诠释上的独立性。
而这种写作的难处在于,不得不考虑人物的真实性和虚构之间的非常微妙的制衡,同时还得做许多案头工作和与素材相关的访谈,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但作为一个小说家,葛亮看重的仍是对历史诠释的态度,是写作的“真切”,而非“真实”。“我总觉得推动历史是非常神秘的事情,希望通过我这种方式去找寻到这种神秘感的蛛丝马迹。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这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
就像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中,虽然会出现天津、上海、北京、大连等真实城市的名字,但他虚构了小说中的主要地点,一个位于中国南北交界处的城市—“襄城”, 因为他不想让小说的细节被束缚住。
一座走钢丝的城市
过去,葛亮几乎没有虚构过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在他已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中,故事背景主要就是南京和香港。前者是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乡,后者是他成年后求学和生活至今的容身地。他把这两座城市分别称为“家城”和“我城”。
葛亮曾多番书写南京的六朝烟雨,尤其是长篇小说《朱雀》获得诸多好评。莫言评价说:“葛亮是具有超人禀赋和良好训练的青年才俊,《朱雀》是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拷问的新型小说。他像写自家的家园一样写出了一个他的南京,他像写自己的亲朋一样写出了众多的人物。”
葛亮是在香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南京的,而近在咫尺的香港在他笔下却刚刚开始。作为他第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作品,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浣熊》成为葛亮在创作上新的开拓。那些不时插入的粤语方言、香港地名和风俗,在富有质感的文字中带着特有的鲜活感陡然跳跃着。
正如苏童所说,“这一次,葛亮转过身来,目光正对香港。繁华世界里,人心的秘密与万家灯火捉迷藏,葛亮告诉我们,所有的秘密,其实都通往孤独之门。”
南京和香港,这两座不同的城市,让葛亮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气味。葛亮特别强调一个城市的气味,因为它会决定作者叙述的状态和书写的方式。
对葛亮来说,南京古典、缓慢,写这座六朝古都无法跳出对历史元素的再现,所以《朱雀》的时间跨度达70年,从民国30年到千禧年,其文字也更古典,被批评家认为是“新古典主义”。而香港现代、迅捷、多元而又光怪陆离,所以《浣熊》的行文更加简洁、跳脱,更多的是一种空间的碰撞。
对葛亮来说,南京是故乡,会让他的写作获得一种天然的自信,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麻木感,因此在《朱雀》里,他让一个从苏格兰到南京留学的华裔青年作为线索人物,以一种外来的陌生力量去撞击司空见惯。而在香港写南京,也会有一种抽离感,让他有一个躬身反照的机会去观看南京。
香港却涉及到另外一个“身份”问题: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既非生长于斯,也不是过客。因此他写香港的态度更加审慎,必须选取一个最合适的角度。不同于张爱玲以一个过客心态和文化俯视眼光写作《传奇》—“给上海人写的香港的故事”,葛亮希望自己站在一个抛却先验和文化成见的立场来表达这座城市。
“香港是充满相遇的城市。它在上世纪30年代扮演的就是东方卡萨布兰卡的角色。很多人到了香港,是把它作为人生过往的驿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造成了不同人群的汇集,呈现出一种混杂性的特征,焕发出一种自发向上的生命力。”葛亮说。
因此,“相遇”是这本小说的关健词,主要篇目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比如脱胎于新闻事件的《猴子》,写一只从动植物园里逃出来的红颊黑猿和不同的人相遇的故事,它突然的侵入,让一些人生命中麻木的状态被打破,本相哗然而出。“这个过程是苦痛的。”而他以动物作为书名和篇名,就是为了表达对“动物都市”这一主题的关注。
“浣熊”是2008年过境香港的一场台风,这篇小说描写了一对普通人在非常状态下的非常匆促的相遇。“每个人都行走在钢丝上,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状态。”葛亮说,他们就像《浣熊》里的主人公,有各自的布局、心事和无奈,又不得不以另外一种方式示人,去扮演他们的角色,所以“浣熊”成为一个契机,让他们相遇,最后改变了他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