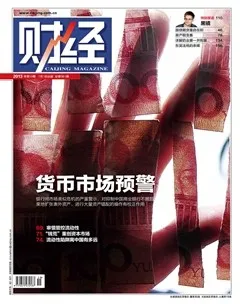中日关系的“结构论”与“本质论”
2012年6月20日,正是中日关系从名古屋市长的“南京大屠杀乌有论”向东京都知事酝酿“钓鱼岛事变”过渡而持续“高烧不退”的时候,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日报》社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发布了颇有刺激性的数据:日本人的中国反感率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84.3%,好感率只有15.6%;而中国人的日本反感率为64.5%,好感率为31.8%。
“空前最坏的结果!”“相互反目的两国国民!”日本媒体反应强烈,与东京都发起“购岛募捐”挑动的“钓鱼岛危机”形成共振。
然而,中国主流媒体却一再发表把危机描绘成“右翼分子破坏中日友好”的“闹剧论”文章,呼吁“正气”压住“日本右翼的邪气”,警告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回避事实的批判、诅咒难免搅乱外交战略思考:既然绝大多数国民感情如此,“友好”立论逻辑何在?“正邪”所指究竟是谁?
事实上,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日本人的中国反感率早在2004年就开始超过半数达58.2%;而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第二次中日舆论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日本反感率为53.6%。进一步来看,中方2002年“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的数据是43.3%,日方“外交舆论调查”的同年指标为49.1%;即在2002年就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反感对方”的状态。
现代政治和公共外交需要“信息化民意”作为政策根据。战后中国对日外交一直高举“友好”旗帜,为什么“大局”适得其反?日本是国民投票选举政府的政治共同体,哪里有“扶正压邪”的头绪?直面事实,反思经验教训,才能整理化解危机的思想路线图。
正视“真问题”
以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解,相互高度嫌恶的国民感情正是谴责对方的借口和机会;并且从调查数据来看,日本人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社会主义、一党制、利己主义因此不可信赖”,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认识是“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好战,因此不可信赖”。如此认定对方具有某种讨厌的“本质”,倘若让容易感情短路的“本质主义”者判断,似乎只有长期“死磕”乃至“终有一战”的前途了。
然而,知识探讨应看到“结构性”事实:有80.3%的日本人和78.4%的中国人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并且双方多数都不满于政府外交和首脑会谈的成果,都肯定存在“领土问题”,都认识到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是“领土问题”,都最希望首脑会谈能解决“领土问题”。很显然,“领土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对抗性“结构”,通过谈判和平、合理地解决“钓鱼岛问题”乃化解中日关系危机的出路。
中日外交的实际状况怎样呢?就在“钓鱼岛事变”发生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于2011年底访问了中国,双方把即将到来的邦交正常化40周年确定为“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希望深化“战略互惠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2012年1月31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审议中,一位在野党议员质询野田首相:去年举行了日中首脑会谈,但总是用“战略互惠关系”之类“悦耳动听”的语言游戏搁置“真问题的解决”。为什么不谈“尖阁列岛”和油气田共同开发问题?是不是应该反省?野田答道:“战略互惠关系见面就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咒文那样,见面就相互唱念一番,但个别悬案还会闹起来。”
“战略互惠”是日本提出的中日关系新概念,堂而皇之地载入两国的“政治文件”,但竟然被戏称为“咒文”,引得议员们当场失笑。野田也似乎意识到不妥,一边致歉,一边修正说:“应该说是理念,或者说是基本原则,相互确认,反复念几遍,也有深化意识的作用。”
但那位议员不以为然,强调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政治家的工作”,指责两国首脑遇到麻烦就靠唱经念咒逃避问题。
对于“战略互惠关系咒文论”,日本媒体称首相“无意中流露出本心”。事实证明日本政府的外交谋略超出那位议员的想象:首相访华照例念一通“战略互惠关系”咒文,但几个月之后就发生“购岛事变”,爆发钓鱼岛“悬案”。
如果在邦交正常化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合理解决了钓鱼岛问题,或者即使当时搁置但后来择机谈判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条约化,何至于如今撕破脸皮。
中国的信息战略“盲区”
历史认识、钓鱼岛之类“问题”间歇发作造成周期性恶化的外交僵局,这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规律。“历史认识问题”时有“休眠”,外交缓和周期尚能勉强复位。但“钓鱼岛问题”出现了日本否认“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死结”,所以挽救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两国共同澄清历史真相。
外务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课长浅井基文指出:搁置主权争议问题,“不仅是外务省,而且是日本政府共同的认识”。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的外务省条约课长栗山尚一也确认:存在中日首脑之间关于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共识”。于是,玄叶光一郎外相在2012年10月10日会见记者时说:“据当时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不能认为达成了合意。”
所谓“第三次首脑会谈”,是指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于27日的会谈。日本否认存在“搁置争议共识”,是基于这样的会谈记录:
田中:“关于尖阁诸岛,你怎么看?我这边有说这说那的人。”
周:“关于尖阁诸岛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它不好。因为出来石油,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石油,台湾、美国都不会做文章。”
这份1988年9月打印的“记录”一看就有异样感,据当时参加谈判的中国外交官指证:周恩来怎么可能按照日本的说法称“尖阁诸岛”?但这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文件,随着日本的《情报公开法》于2001年施行而被请求公开,学者还汇编出版,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权威资料。据此,日本主流学者得出中国政府承认“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结论。
然而,根据中方资料,两首脑是这样谈的:
田中:“想问问尖阁列岛问题。”
周:“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
田中:“既然到了北京,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提一下,回去后会遇到一些困难。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
周:“对,就因为在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把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做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
田中:“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
周:“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大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
由此来看,两国首脑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且是日方主动提起并倡议“以后再说”,与亲历者的回忆能够统一起来。岂料,日本政府从1996年就尝试在外交场合否认共识的存在,中国却从“友好”立场发表见解、提出批评,而未在档案公开、学术研究、信息收集、议程设置、国际传播诸方面展开有效行动。
2013年6月3日,日本前官房长官野中广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作证亲耳听到田中角荣首相承认“搁置争议共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国内回应说:“仅以我国的外交记录来看,没有那样的事实。”话到这种程度,可能是中国公开档案并进行相关交涉的最后机会了。
信息战略“盲区”的存在导致外交无行动或盲目行动。从日本外交的国际传播特征而论,中国抓住机会的前提是外交转型改革——从意识形态主导的秘密外交转变为信息战略主导的公共外交,即放弃“或人民或右翼”的本质主义日本观,依据国民国家的现代政治原理,通过主动的信息、知识传播和有能力的专家型交涉,推动国际共识的形成。
日本的东亚“无意识”
当然,并非只是中国被本质主义日本观控制着,日本也存在着强势的“中国威胁论”本质主义中国观。
2012年9月30日出版的《外交》期刊(日本外务省发行)策划了反思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的特辑,其中一篇从战前历史对比两国相互认知的文章受到关注。《朝日新闻》特别报道说:舆论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反感中国,认为中国是“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自我中心国家”。这种中国观其实是向80年前回归,和1931年“满洲事变”时期日本媒体批判中国的逻辑一样。而另一方面又“反转”过来,80年前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日本,现在日本人则认为中国是威胁和平的“霸权国家”。根据这种比较历史学分析框架,中国被推到了知识思想审判意义的被告席。
日本人中国观的“80年前回归论”和“中国疑似战前日本论”所隐喻的中日关系“倒退”到了上世纪30年代,这有利于调动日本的“领土民族主义”,有利于日本借助日美同盟压迫中国。
不过,日本即使取得了对华冷战的政治优势,能泯灭中国的钓鱼岛主权主张和双方有证的“搁置争议共识”吗?对比2005年的“反参拜游行”,2012年的“反购岛游行”规模扩大且暴力活动蔓延,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汽车曾经在路上被拦截、拔去国旗。亲历了这种失控临界状态惊险的丹羽大使卸任后回到日本,担忧日本政府见解主宰舆论的状况,一再呼吁,承认存在争端的事实并通过谈判解决。他2013年2月19日在东京演讲说:回国后感到吃惊的是大家没有勇气讲真话,中国有雾霾,日本的“空气”质量更坏,都很不幸。
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世界的地区政治进程特征分明:从和解到统合的欧洲共同体政治;战后遗留问题导致周期性外交僵局的东亚冷战政治;领土主权纠纷之无和解,诱发国家间战争和无政府暴力之无和平的中东战争状态。东亚是走向和解的“欧洲化”,还是堕落于仇恨与暴力循环的“中东化”?日本是东亚的唯一发达国家,应该反思传统国家利益外交,承担相称的地区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