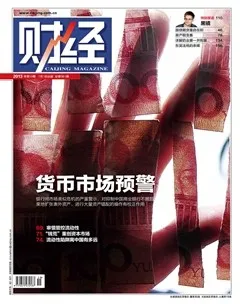龟与兔
让人不解的是,抛开协约国在“一战”期间所享有的巨大优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总是偏向于对德国战时经济的体制缺陷耿耿于怀。尽管经济实力的差距可能已经足够成为同盟国输掉战争的理由,但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对德国政府的失误加以指摘。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德国人在经济动员上比其对手显得更为慌乱无序。但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比起德国的敌人英国,德国商人和政客在思想上更倾向于接受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之后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德国的战时经济描述成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共同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并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落后可以归咎于这些理念。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德国并不高明的官僚主义以及缺乏现实主义的军事首领着实将其战时经济实力逐渐耗损,典型代表为兴登堡计划中粗鄙而失败的经济干预政策。
英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对与上述概念互补的观点进行宣传。与其说这种态度源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不如说是因为所有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仅为传统的海战而已。物价并没有得到控制,出口和航运亦如此。但是1915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惊醒了梦中的英国人。在英雄人物劳合·乔治的带领下,按照他创造的军需部的组织原则行事,英国极佳地适应了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它唯一的过失是战争刚结束时便忘记了自己从这场战争中学到的东西。因此出现了一个让人愉快而又矛盾的事实:外行者英国在经过一番探求、摸索和犯错之后,却战胜了德国行家。
杰伊·温特认为,英国和法国都“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进行一场独特的、并没有提前进行规划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相对来说是成功的”。与此相反的是,德国采取了一种“社团主义”的体制。这种体制将经济的管理移交给混乱的官僚系统,大公司和军队从此被控制在这些人手中。这直接引发了混乱局面。
温特指出,“如果德国工人在1917年到1918年争取到与英国相当的实际收入水平,并且如果他们的家庭能够保持和英国家庭相一致的营养摄入量,那么战争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他认为(基于他在柏林的一项调查),德国人缺少“公民权利”,而协约国的体系能够体现出“公平与高效”。
这与龟兔赛跑的情形极其相似,这终究是个“故事”。如果协约国的效率真比同盟国更高,或是在资源分配上更为合理,那么1914年-1918年的这场战争在时间上将会被改写:或许1916年到1917年冬天——德国国内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时,它就已经结束。关于战时经济的文学作品完美揭示了在没有比较研究基础上撰写国家历史的危险。一旦进行对比我们便可得知,关于“有缺陷的组织”的假设无异于极右势力和德国军事领导层在输掉战争后极力宣传的“背后中伤理论”的更为体面的说辞。正相反,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人比其西方对手在动员战时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对德国经济动员的消极观点部分源于当时的悲观情绪。战前曾有人设想,德国军事当局就是国家效率的象征。1914年8月,阿尔贝特·巴林还能“从总参谋部的严格控制中分一杯羹”。但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几乎立刻让他的美梦化为泡影。随着战事的推进,当巴林试图弥补协约国对其公司商船造成的巨大损失时,他更为悲观失望。再加上政府阻止他销售停泊在中立国家港湾的船只,他就更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绝望。1918年2月,巴林谴责“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拖到练兵场的危险行为”。
巴林只是众多愤懑者中的代表,德国商人——特别是柏林之外的商人——对政府处理战时经济事务的方式表示愤慨。汉堡商会主席曾痛斥“军火公司几乎控制了所有交易……将军队合同独家承包给柏林工业……联邦议会还颁布了名目繁多的限制商业活动的法令”。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就连重工业发达地区的人们都怨声载道。德国农民也一直在政府分配食物这样的事情上异常愤怒。
然而,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刻板地看待这些抱怨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其他国家的战时经济状态就会发现,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德国资源短缺的客观状况,那么我们便不必纠结于它的低效了。实际上,协约国才是在动员经济方面真正低效的一方,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挥霍的程度。
诚然,德国存在官僚作风,但问题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官僚作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德国最终输掉战争的事实掩盖了这些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