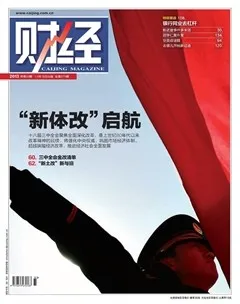空鼻症谜题
10月25日上午,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在诊室内遇刺身亡。嫌犯连恩青曾在该院做过鼻部手术。就在舆论谴责暴力行为、反思医患矛盾根源时,11月2日,腾讯网评论频道推出专题《空鼻症,杀医血案的“幕后真凶”?》,指杀医案总是与疾病“治而不好”、患者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有关,而了解“空鼻症”后,迁怒于医生的怪象就不怪了。由此,空鼻症患者这个外界知之甚少的群体浮出水面。
次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周激波在微博上回应称,不应该将空鼻症与杀人行凶动机随意联系,医疗话题可公布资料作为学术讨论,而不应以此作为杀医的原因,“退一万步,即便凶手存在治疗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同情他的杀人动机”。
空鼻症,学名空鼻综合征(empty nose syndrome),指鼻腔组织过度缺失相关的临床症候群,及相应的鼻腔鼻窦影像学表现,多为鼻科手术后引发,至今研究有限,还属于医学界的新命题,其群体数量、发病机理与规律等皆不明。尽管有国内外医生采用临床手术治疗,不过,仍缺乏通行的主流药物或手术治疗指南。
而事实上,空鼻症与刺医血案的行凶动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解决此问题亦应各行其道。
呼吸的痛
“每一次呼吸都痛苦无比!”疑似空鼻症患者王立(化名)告诉《财经》记者。他一个月前在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医院做了鼻中隔偏曲和鼻甲切除手术。术后,吸气过于畅通但呼气不畅,空气直接入肺,干冷而十分不适,每天需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晨起则感觉缺氧,鼓膜胀痛。
时间越久,难受症状与日俱增,王立经常莫名地情绪烦躁,爱发脾气,术后已和领导吵过三次架,有辞职打算。
“一周前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而实际上我生活在煎熬中。这种痛苦不是骨折、流血等肉眼可见的,不被别人理解。”王立说。
人体鼻腔有上中下三个鼻甲,均是鼻内软骨组织,其表面覆盖一层黏膜,上面覆有黏液。鼻甲如长期受到炎症的刺激,会引起鼻甲黏膜水肿,特别是下鼻甲的肥大,更容易造成鼻腔阻塞、头昏及头痛。在药物等保守治疗方法效果不彰时,鼻甲切除手术就成为一些患者的选择。
国内医学界形成的初步共识是,医源性空鼻症的病发与下鼻甲切除有关,其中完全切除、部分切除、黏膜下切除等手术后均有此类患者出现。
空鼻症群体的经历大致相仿:做过鼻科手术,而术后出现鼻部甚至咽喉的干燥、肺部呼吸难受、鼻子堵塞、精神不济等不适症。
两年来,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特需专家、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原主治医师王先忠接诊过国内数百名空鼻症患者。他发现,每位患者在术后的症状不尽相同:有的以鼻腔干燥为主,有的以过度通气为主,也有人以刺痛难忍为主,还有人几种症状并发。
自相矛盾的鼻塞是空鼻症患者最不堪忍受的状况之一。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斯蒂夫·豪斯(Steven M. Houser)告诉《财经》记者,鼻甲切除手术后,患者宽大通畅的鼻腔令人印象深刻,患者却感觉鼻塞。原因是,人类呼吸时,呼吸道会对经过的气流产生阻力,其中,鼻腔所做的贡献大约占一半。而鼻甲切除手术会减少鼻腔对气流的阻力,有可能打乱肺部正常工作所需的阻力平衡,使患者呼吸效果变差,效率降低,并导致呼吸急促。
空鼻症患者往往沉陷于呼吸困难的恒定状态,有些患者将之描述为“令人窒息”的感觉。这种糟糕的感受让部分患者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和鼻腔,无法集中注意力,出现沮丧、烦躁、愤怒、焦虑,乃至抑郁症。
在美国医学界,空鼻症存在很大争议,很多医生并不相信它的存在:患者接受鼻部手术后,疼痛可能伴随而来。当出现这种疼痛症状时,患者会怀疑自己得了空鼻症,但这种慢性疼痛并非空鼻症。事实上,除了鼻甲组织或者鼻甲外层的黏膜遭到过度切除以外,空鼻症的发病率是很低的。
诊断之难
近日空鼻症引发关注之后,很多有上述经历者,纷纷加入网络上的空鼻症患者群,或者组成“自救联合会”,几日之间,有的群迅速爆满。但1994年才被首次提出的空鼻症,由于医学界认识不足,研究有限,发病率仍是医学界的争议焦点之一。
根据豪斯的临床统计,约22.2%的下鼻甲切除术可能出现疑似空鼻症的症状;接受部分鼻甲切除术的患者中,有8%的人出现了鼻腔过度干燥。
但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周兵表示,由于深入研究甚少,实际发病率并非如论文报道多达20%,“否则这么高的发病率,鼻科手术都不敢再做了”。也有研究报告的数据支持他的说法,大量鼻甲手术案例中几乎没有并发空鼻症的报告。
此外,空鼻症的发生因人而异。有的患者鼻甲全部切除,却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与情绪异常,有的患者只做了轻微的鼻甲切除手术,甚至在CT检查中看不出明显改变,自身不适应症却很严重。而且,“敏感”的患者,不仅局限于鼻甲手术,甚至扩散至鼻中隔、鼻窦等手术。
“这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空鼻症的病发难度,它到底会在哪类人群中容易发生,发病规律如何,目前根本无法预测和判断。”王先忠说。
在空鼻症患者网络群内,探讨最多的话题是:“我这样的症状是否是空鼻症?”然而,鲜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由于缺乏可靠的客观测试方法,医生一般依赖于患者的主观症状描述,来诊断空鼻症。
而诊断错误就可能导致治疗不对症。最常见的诊断错误是,患有抑郁或其他精神心理异常的鼻炎、鼻窦炎患者,主要症状并非来自鼻部疾患,对这些患者盲目进行鼻部手术会导致病情加重;其次是非鼻源性头痛,被错误地诊断为鼻源性头痛。
豪斯认为,患者是否做过鼻科手术只是一个重要依据。对于过度切除鼻甲引发的空鼻症,可通过CT扫描获得清晰的缺损报告。但一些患者鼻甲缺损不大,进一步的诊断依据则需要通过棉片试验获得:将大小适中的棉片用生理盐水润湿,放置在鼻甲受损的部位,让患者自由呼吸,半小时后,如果患者的主观症状有明显改善,就支持空鼻症诊断。这一诊断方式也被国内少数几家医院采用,没有大范围推广。
鼻部神经遭到破坏是另一个可能的致病因素,国外多数学者推测空鼻症发生的两个条件:手术操作使得分布于鼻黏膜表面的感觉神经受损;创伤部位会面临神经再生障碍,导致患者出现鼻塞等症状。
在国内医学界看来,空鼻症的发病机理很难用单一原因来解释,而应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先忠认为,教科书中对鼻甲生理功能尚未完全明了,导致其重要性未能引起医生足够重视,在试图改善患者的鼻腔通气状况进行鼻甲切除时,尺度把握不当,容易造成空鼻症。
规避手术风险
面临空鼻症等诸多不确定性,鼻部手术的风险应该如何规避?医学界内部正在激烈讨论这一问题。
与其他众多的大型手术相比,鼻部手术往往被视为技术含量不高,不会像大型手术有术后预案准备。常见的下鼻甲手术,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对部分重症鼻炎或鼻窦炎患者有改善疗效。以前,这类手术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切除肥大的鼻甲、开放鼻窦,获得更大的鼻腔容量。现在,切除多少的量化指标有了争议。少数医生的观点认为,下鼻甲全部切除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解除鼻塞的方法,而大多数鼻科医生反对这种做法。
“以前对手术追求‘大而空’,比如把鼻息肉都切得一干二净,但现在是可逆性原则,杜绝任何无限度地扩大鼻腔容积的手术方式。”武汉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乐建新告诉《财经》记者,通常鼻科疾患应尽量保守型治疗,其次才是对发生病变的部位施以微创手术,前提是必须最大化保证正常的鼻腔组织。
现实是缺乏规范之时,每家医院、每位医生对此理念掌握的分寸不同,有不同判断和手术习惯,手术技巧也参差不齐。
荆州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姜义道曾经撰文指出,公立医院的空鼻症患者明显少于私立医院。按常理公立医院鼻部手术的患者数应明显多于私立医院,但空鼻症患者少说明公立医院在鼻甲手术方式选择和技巧上更为优化。
对于空鼻症患者来说,可以首先选择保守治疗,不过目前看总体效果欠佳。美国医学界一般建议,保守治疗效果不彰、鼻甲没有被完全切除的患者可以采取鼻内修复手术,即通过手术缩小患者鼻腔容量,增加鼻阻力等,以期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症状a25867642cca6ed1ffe01946f9e96e74。这一手术可以将空鼻症患者的鼻内结构恢复到发病前的状态。
鼻内修复手术需要精细操作,花费不菲。自2003年以来,豪斯为57名患者实施了81次植入修复手术,有的患者接受了多达5次手术,才获得较好效果。根据植入材料和手术方案的不同,单次修复手术的费用从0.2万美元到1.2万美元不等。
周兵认为,手术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带有某种程度的心理暗示作用,很多病人在手术后一段时间内会有反复。
国内医学界对空鼻症治疗的研究寥寥。王先忠是国内为数不多进行过“全鼻道缩窄术”治疗尝试的医师,两年来共做过20多病例,目前只有2例痊愈,病人可达到正常人呼吸水平。还有一部分患者虽有所改善,但与患者预期值仍有距离,而其他病例的疗效有待随访观察。
这种手术属于方向性比较明确的尝试,但治疗效果有很多不确定性。王先忠说,未来几年内,他将不会再进行这项手术,主要原因是患者过高的期望值导致手术风险难以掌控。
国内也有医生在进行包括自身组织移植、口腔黏膜转移、干细胞的组织功能学等临床研究,但都属于尝试阶段,而更多的医生回避新的探索,尤其是医患矛盾关系下,不愿意做更多的尝试。
纾解矛盾的必要
一位河南新乡市的疑似空鼻症患者告诉《财经》记者,在最严重时他几度想过自杀。他有抑郁的倾向,“不能去人多的地方,闻不得一点异味,身边不离加湿器和空气净化器”。为此,他失去了工作,之后去国内多家医院就诊,均被告知“没病”。
周兵接诊过的21名空鼻症患者,在手术前接受心理评估时,几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他认为,空鼻症的特性就是伴有精神、心理问题。
一部分患者被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并长期被建议服用抗抑郁药物,病症并没有得到缓解。精神心理障碍也是疑似空鼻症群体十分排斥的字眼,“根源在于医疗科研不透彻,却非要给我们强加上精神病或癔症,最终我们抑郁倾向更严重”,患者王立对此颇有微词。
对这些倾向,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慎用心理或精神障碍来解释。医学网站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认为,空鼻症与鼻甲手术、精神障碍的关联度还存在医学科研上的研讨空间,至少有两个问题有待深思:选择此类手术的优化性与必要性,须临床对照实验;手术对病人会在心理上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需要心理学量化表来评定。
在网上的病友群里,很多疑似空鼻症患者以自杀甚至杀人的过激言语来发泄情绪,他们认为目前的诸多不适症与手术有关,从而迁怒医院。
对此,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解决之道是,一方面,为防范医院内的暴力犯罪,医院安保措施升级,增加医疗工作者自我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国家和医疗科研加大投入对空鼻症的病理研究,对于这一症候群体应及早开展统计与评估,并启动必要的诊治与救济渠道。而患者自身也须理性采取合理方式维权。
“用空鼻症去掩盖弑医,不但容易混淆视听,且容易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加剧医患环境的恶化,受伤害的仍是医生和病人。”周兵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医生选择了自我保护,不得不放弃对疑难问题的探索。”
纾解医患矛盾,应有合理的申诉途径。一些空鼻症患者称,他们通常先与就诊医院投诉、协商,必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解决,但两条渠道都不畅。医院有时对术后症状进行推诿;采取司法途径时,手术与不适症状的因果关系又难以确立,通常成为不被法院支持的理由。
第三方调解机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可成为空鼻症患者争取权益的优化渠道。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5月,至2013年9月30日,共受理案件4044件,结案3442件,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补充途径。
该委员会副主任刘海英分析,对空鼻症患者,调解委的最大好处是不设置接案门槛,不收取患者费用,会牵头帮助患者与医院协商调解或进行鉴定,甚至引导患者合理司法诉讼。
目前,天津、山西等多地都成立了这一机构,可供各地患者选择。不过,真正扩宽和优化这一路径,必须首先破除在患者内心积蓄已久的医患不信任障碍,而这是由医患关系的大气候决定的,非一朝一夕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