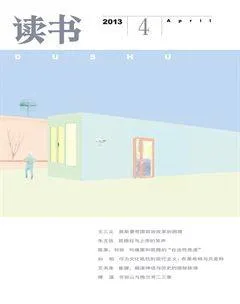世界心灵的高度
我曾将传教士卫礼贤与史怀泽,誉为“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无论是“非洲圣人”史怀泽(Schweizer, Albert,1875-1965),还是“中国心灵”卫礼贤(Wilhelm, Richard, 1873-1930),他们都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艰苦的人生实践,完成了他们作为“一代师表”的崇高形象塑造。“哲人虽已远,典范在夙昔。”
如果说卫礼贤的工作更多还停留在文化史意义的锱铢积累,那么史怀泽的意义,无疑更多可以反映在社会史层面的躬身实践。相比较卫礼贤日后更多地从传教士身份逐步淡出,那么史怀泽无疑更坚定地选择了基督精神的坚忍执著。如果卫礼贤能够享有史怀泽那样的高龄,他的成就或许也同样不弱于史氏,不仅是事功方面的持之久远,而且也是述思方面的体系建构。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史氏《文明的哲学》这样的体系性大著,卫氏是没有的。可无论是回守书斋,还是选择丛林,卫礼贤与史怀泽都有其不可磨灭、不可否认的重要之精神史价值;其出于个体生性的选择都同样值得尊重。
那么,如果将视域拓宽,以世界为范围,我们要举出另一位人物作为参照和比较,他就是中国人晏阳初(一八九零——一九九零)。虽然年龄有别,代际差异,但他们同享高龄,他们同具高尚的灵魂。中国曾经拥有晏阳初,也就意味着现代中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攀登上了怎样的精神高度。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奏影响之下的现代中国,并未因此就真的远离了世界精神的核心要义。回顾过去两百年的历史,我们会为国人之悲壮行程而动容,既可洒一掬同情之泪,同时又难免发一声浩然长叹。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代人所拥有的世界理想,让人感动,但毕竟李石曾还是个过于寻求“文化浪漫主义”的潇洒自如、随性而安的人物。他在社会事业上的事功不成,终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夸耀的事情,但他的精神和理念已经走出了或救亡、或启蒙的初级反应思维,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甚至是世界理念的层面,故此特别值得表彰和肯定。
从李石曾到晏阳初,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李石曾这样的人物,其意义已经非常了不起,他虽然事功鲜有“善始善终”者,但毕竟是一代“开辟风气”人。可必须承认的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领袖,因为他不曾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事业,并使之具有普适性的范式意义。可晏阳初出现了,他不但在打破原有传统观念的轨迹上继续前进,即敢于抛弃原有的“学而优则仕”的选择,而且承继了前辈锐身于社会实践的新风,将平民教育作为终身志业而发扬光大。作为留美学人,晏阳初从一九二零年留美学业完成归国,到一九四九年不得不黯然离去,晏阳初以其在历史苍茫中的平淡身影,为现代中国的建设事业留下了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有时很难想象,在非洲加蓬的岚巴瑞(Lambarene)的一所医院里,当德国传教士史怀泽以一种老僧苦行入定的执著坚守住其传教行医的事业之际,他居然同时写作了一部《印度及中国思想史》(Geschichte des indischen und chinesischen Denkens),当然最初是定名为《中国思想》(Das chinesische Denken),或许是与其早期的另一部专著《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Die Weltanschauung der indischen Denker)相衔接。或许,他已经发现,更应当将印度—中国视作一个整体,但他还是没有将其综合为一个名字。这样一种“行”与“思”的结合,使得史怀泽的思想建构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史怀泽以一介常人,发宏愿,转而借助教会力量而展开力行实践,在偏僻的非洲之邦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真是让人在平凡中感受到他的不平凡。晏阳初也是以一介常人回到母国,他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坚苦卓绝,展开了一项平淡如水而意义深远的大事业,这就是平民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某种惊人的力量,它不但能够扩张其势力范围,而且确实能培育养成一些伟大的人物,并且在持续的长时段内给予其有效的支持,既能在物质与精神上帮助个体发展,同时也可以促成与造就其在社会场域中的“网链点续”的传播功用。在史、晏二氏成长的经历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伟大的教化力量。史怀泽的家庭就是一个牧师之家(父亲、外祖父都是牧师),所以他宁可放弃大学讲师的位置而选择去做传道者;晏阳初是四川人,他先后在四川保宁府西学堂(中国内地会创办,China Inland Mission)、成都美华高等学校(美以美会创办)学习,深受传教士影响,并进入基督教系统的长程规训轨道之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基督教竟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培养和造就着如此不平凡的人物!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伟人形成背后还不仅是基督教的推波助澜,更有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性动力。正如谈史怀泽和卫礼贤时,我们不能回避他们身上“德国精神的现代之光”一样。晏阳初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他的一生事功表明,“中国精神”同样具有“现代之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甚至当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起意让他接手秘书长这样的要职,这足以说明他当初膺选“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的头衔不虚。当然,相比较史怀泽的走向远方,晏阳初的工作范围早期主要仍局限于本民族—国家之内,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晏阳初从中国走向亚洲,又由亚洲走向世界。一九五一年,国际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晏阳初担任主席,将其事业做世界性推广,其意义非同凡响。而恰在同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其出任秘书长的聘约,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不会为了外在的“荣名利禄”而放弃自我。他的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致电祝寿:“漫漫数十年,为那些积弱贫困地区以及最偏远地的人们,您创立了自我拯救的思想。为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孤落山村和广大乡村的农业、公共卫生、教育事业,您开创新道……您的工作一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道路。”美国前总统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讲得更加到位与深刻:“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绝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如果说里根还仅是就晏阳初的事功给予表彰的话,那么布什这段话的价值,更深一层地指出晏阳初对平民观念改变的重大作用。
李石曾也许颇难仿效,但晏阳初却绝对为常人树立了榜样。榜样的力量理应是无穷的,当晏阳初的名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期待,随着现时代中国的发展,我们也会不断涌现出如同晏阳初这样发大宏愿,行大愿力,将中国文化的慈柔之光普照世界的可能。正是这样,晏阳初接近了一种人类文明史的高层次境界——“世界心灵”(die Weltseele)。揭明此点,并非可有可无。要知道,佛道广大,无所不包。当此中国崛起于世界之间,我们不仅需要有属于政治层面的文化外交行动的展开(诸如孔子学院之类),更要有特立杰出(乃至伟大)个体的出现,只有出现了这样的大人物,他们能够像晏阳初一样发此大宏愿、做此大事业,这种事功不但不弱于将经济势力拓展于非洲、拉美等地,更能将中国人的印记以文明的方式深深地驻入世人的心灵。所以,我们需要属于现时代的晏阳初,我们更需要属于未来时的史怀泽。因为,只有他们,才更能标示出中国心灵的“世界高度”。
在现代中国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晏阳初竟然能够披荆斩棘走出如此曲径通幽的佳图,而且居然也能完成如此宏大的事功。在这点上他甚至远胜过史怀泽。我们不得不承认,晏氏具有天才的领导能力和坚毅信念。可需要指出的是,他在思想理论层面的探究则有所不足。相比较史怀泽探索整个人类文明的宏大构架和理论抱负,晏阳初若同样能在求知层面不断探索,不但去创造历史,而且是以一种求知的深刻方式去创造历史,那么,他所达到的境界,或许非常态所能限制。史怀泽、晏阳初都是基督徒,可他们接续的不仅有基督的精神,还有德、中两国的不同传统。晏阳初对自家报国之志的阐述,坦承“反映了那时代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我的报国之志,不是做大官,而是成就大事业。什么是大事业呢?不是开公司、赚大钱。我心中的大事业,是体现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做殖民地上的属民,不愿做被人歧视的廉价劳工,也不愿别人如此。恻隐之心,是消极的仁;舍己救人,是积极的爱。爱是人间最伟大的力量,能克服一切;恨是人间最可怕的力量,能毁灭一切。这世上恨太多,爱不够。我愿爱,不愿恨。仁者,恕也。仁者无敌。基督说:爱你的敌人。我没有敌人。若说是真有敌人的话,那是无知短识所造成的贫苦和歧见。我愿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这里没有更多地为世界、为人类的高远理想,而是更多地立足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并发挥传统儒家的仁义之价值观念。应该说,晏阳初的这一思考对于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祛魅是有其价值的,因为中国传统上始终是“学而优则仕”,即便是科举制废除之后,观念仍未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与现代性发展的基本范式相矛盾的。因为在古代中国,“知识人”与“官僚”是合一的,官员作为一种职业,不仅是政府统治的载体,更是读书人安身立命、获得生存的公共场域;而在现代以后的社会里,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社会分工来确立职业分野的,知识人有其自身的职业归属。但我们的制度虽然不得不变,而观念并没有根本转变,仍是在沿用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路。这是有根本问题的,因为此时的官场早已不再具备传统中国的“知识场域”功能,其本质是相冲突的。而这种结构性的错位,必将长时期地制约双重路径的发展,即知识人不能成其为纯正的知识人,而官员也不可能向纯粹技术化官僚的方向发展。民国如此,至今依然。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为什么就要混一个官做呢?这不仅是制度性的悖论,更是文化上的重大观念误区。因为说到底,观念是种子,社会是土壤,没有种子的误植,土壤再肥沃也很难结出硕果。精英分子如果不能在理念上占据主导优势,那么就不可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灯塔作用;而在社会语境中一味地放纵低迷风气,没有人敢于走出这个怪圈,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有长久的未来和期望。但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无论如何,它是在短期内能够立竿见影的。故此,为官仍是一条路,但那应该是一条众多路径中的平行一支,而非华山一条道。但走向第三部门的过程,恐怕更是一种艰难的观念超越之路。他们是一种调节器,是社会平衡、国家平衡、人类平衡、宇宙平衡的调节器。正如在贫富关系中,富人获得的财富不可能也不应该绝对化,穷人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得到调适一样,晏阳初的出现,其实为现代中国的个体发展提供了一种范式,至少可以称其为“晏阳初模式”,即不走为官之路,也可以青史留名,贡献巨大。
而在史怀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精神路径的蜿蜒伸展。德国人是有着永不断歇的求知精神的,诚如浮士德所言:“在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之间不断交替/君子惟有自强以不息!”在史怀泽这里,则转化为一种深层的人类整体使命感:“由于感受到对文化信念所负的责任,我们的目光就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而达到了全人类。谁献身于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事业,个人和人类的未来就成了他忧虑和希望的对象。……仅仅基于对精神力量的依赖,我们为未来的文化人类开辟着道路,这实在是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所能有的慰藉。”其实,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境界之高下,精神力度之撼动人心。当现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走向非洲,我们不但不应忘怀如同晏阳初这样的本土先贤,我们也要学习非洲圣人史怀泽这样的他乡贤达,作为人类精神的标尺,他们为后来者树立起一种向上的尺度!中国心灵的萃升,应当成为世界心灵的回声!
(《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德〕阿尔贝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晏阳初传略》,晏鸿国著,成都天地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晏阳初《九十自述》,载晏阳初、〔美〕赛珍珠:《告语人民》,宋恩荣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