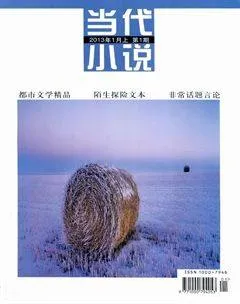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小题大作”与“大题小作”
“小题大作”与“大题小作”
马 兵
任何创作都要面对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作”的选择题,选择前者意味切入生活的开口小,好比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但力图在方寸中显大千,以一滴水折射整条江河的气象;选择后者往往更能体现创作者的抱负,冀望对宏阔的时代做出即时的反映,不过限于篇幅,不免要剪裁取舍,取得精准,舍得魄力。这样看来,文字上的“小题大作”与“大题小作”其结果往往殊途同归。本期四季评选择的作品既有大题,如房价民生,也有小题,如短信风波;作家既有“小作”,借微显著,言近旨远;也有“大作”,借力打力,滚雪球般让故事辐射的面越来越大。无论“大题小题”、“大作小作”都表现出可贵的直面现实与人心的态度。
何顿:《青山绿水》,《花城》2012年第4期
写“三陪女从良”的小说不在少数,但丝毫不影响何顿的这个中篇给人的深刻印象。这些年,何顿一向以对原生态的生活欲望和鄙陋的市民情态的书写见长,他的叙事直白简捷,用语家常俚俗,针脚密实,自有一股烟火气的蓬勃之力,然而他笔下那些商海弄潮儿的放诞和物欲横流也每每引人侧目,以为他对商业逻辑之恶的呈现缺乏节制和分辨。对此,《青山绿水》是个很好的回答。这个小说里依然有大量何顿式的人物,如暴发户“叔叔”、城镇电视台的明星“婶婶”、不得志又不甘心的派出所杨副所长等人,但小说的情侣主人公却让读者探摸到何顿小说中并不多见的正能量。苦孩子出身的片儿警黄志一工作就面临支撑家庭,尤其是抚养痴呆弟弟的重任,他也想把弟弟送入福利院,但父亲的遗嘱始终是良心的背负;他也想借发达的叔叔的能力升迁提拔,但面对犯罪的叔叔,还是拔枪捍卫了警察的尊严;他深爱杨小玉,但面对小玉做过小姐的事实又心思难平,选择和她离婚。再看杨小玉,当黄志愤怒中去找她发泄时,小玉的凛然不可侵犯让黄志醒悟到自己那自以为是的道德感既是强加于人的枷锁,也是禁闭自我的桎梏:“我以前那么看不起她们、讨厌她们,觉得她们把道德和秩序破坏了,但谁管过她们背后那些凄凉、酸楚和复杂的故事?”小说表现两人由爱而憎,由憎而悔的情节看不出什么新鲜,也没玩任何花样,但直白的叙述里却伏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时刻在撩动读者的心弦。小玉在家庭中的柔情缱绻和对外的庄重自持,让人想起沈从文的名篇《凤子》里那个“爱你时有娼妇的淫荡,不爱你时有命妇的庄严”女神般的形象。对于“青山绿水”的题名,作者承认有寓意,但又建议让不同的读者寻找不同的答案。小说中曾交代杨小玉的家在“青山绿水”间,似在暗喻她质本洁来。人们又常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小说结尾,两位彼此深爱的人再度见面,虽然小玉一再申说着“但是”,叙说对未来生活的隐忧,但大部分读者都愿意相信他们的爱会有好的结果。
卢金地:《亲爱如牙》,《当代小说》2012年第11期
这是篇切口细小而辐射面甚大的小说:切口是母亲的意外摔倒住院,而辐射出的则是少妇华美“人到中年”、危机四伏的生活。作者的叙事策略是引而不发,他在小说里埋设了多个线头,每一个抽开拉长都会是一个好故事:诸如华美和丽达孪生姐妹因情而生的心结、华美因修电脑而认识的吴雨浇对她展开的爱情攻势、误会了妻子华美的丈夫“石油”的蓄意报复等等,都是点到为止,不多渲染。这些线头且都拢于华美一身,以此来刻写其在生活进退失据的状态中的疼痛与缺失感。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整个的世界像一个蛀空了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些酸痛”。本小说题中所谓的“亲爱如牙”,大抵也是冷暖自知的意思,接二连三的变故,与姐妹情、婚外情、母女情的纠缠,让华美四十四岁的人生如同自己那缺少了两颗牙的牙床,咝咝地冒着寒气。作者曾有“打酱油”的小说创作心得,即小说不一定直指事件或情感的核心,漫漶地溢出主要逻辑主要流程之外的东西或许会让小说更有可堪回味的声色和质感。这个小说显然即是作者这种创作观的又一次实践,几乎在情节演进的每一个环节里,作者都要把笔墨荡开一下,照应或交代与主线索无关的支线,不厌其烦,不厌其精。另外,小说的比喻运用和细节运用也非常考究,显现了作者细腻的文思。
范小青:《短信飞吧》,《作家》2012年第4期
范小青是“小题大作”的高手,她的短篇擅长从生活小事取材,信手拈来,却总痛痒相关,引人思索。《短信飞吧》便从最寻常的短信入手,在一系列的误发导致的误会里连带出对当代人短信社交乃至职场生态的冷眼旁观。在传播学的理解中,短信传播为公众提供了人际互动的新的资本,有助于消除自我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另外,短信传播还充当着一个全面转型的不安稳时代的泄压阀,为现代人消极的心理能量提供一个释放的渠道。然而,短信的传播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范,最显在的问题之一便是作为一种代码的交换和共享,短信在电话之后进一步消解了人们之间晤谈的那种在场交流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加大了人们离心化、公式化、淡漠化的社交体验。小说中的黎一平与同事老魏固然可以借短信试探彼此态度以免面谈伤了和气,但也发现,心底的实话无人可说,以至于让黎一平有给世界上一个不存在的号码短信交流的想法。而老魏在官场和情场上的两条关键短信,一真一假,更让他对世事有啼笑皆非的荒诞感,而他由此背负的包袱则更见小小的短信非同一般的内暴力。
嘉男:《伸手向上》,《广州文艺》2012年第9期
这是篇“大题小作”的小说,作者把高房价下升斗小民买房用房的艰辛化作“伸手向上”这么一个“生活方式”,规避寻常的路数,而用富于生命情韵的细节呈现来表征这个时代庞大的物质压力和没有被这压力摧垮的家庭的温情。为了节省购房成本,古金家买了层高很高的一室一厅小房子,并在有横梁的地方都打上吊柜以节省地面的空间,自此他们一家人便开始了“伸手向上”的生活——取放物品都要“伸手向上”才可勉强够得到,女儿伊伊甚至因此生长出一副不协调的长臂让她老大难嫁。当父亲去世,伊伊重回她曾无比憎恨的逼仄的小家,打开吊柜发现父亲记录她成长的那些见证时,她蓦地发现“伸手向上”的生活也是充盈关爱与梦想的生活,是她念兹在兹的“天堂”生活。所以,“伸手向上”又喻指对现实人生困境的超离。小说在很短的篇幅里容纳进近三十年的时空,当属于短篇体式中的“纵断”写法。一般而言,横断面是短篇小说的特长,而纵断由横断构成,林斤澜先生曾谈到过,“短篇一路走下来若‘站’三五‘站’,那些‘站’最好都只是个‘点’,都是一个‘特写镜头’,少来或是不来‘中景’、‘全景’”,这样结构的短篇才不会成为“长篇的提纲”或“中篇的缩写”。《伸手向上》的几“站”分别是买房时、伊伊小学和大学时、古金去世时,可见出作者构思的用心,不过在个别交代的地方还是因求全而稍有“中篇缩写”之嫌。
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收获》2012年第5期
作为一个对“底层写作”抱有警惕性理解的作者,徐则臣在处理他最拿手的“京漂”题材时总是会规避外在的苦难与困窘,这不是说他对“京漂”族饥寒交迫的物质匮乏视而不见,而是他致力于写出这一特定的群体栖身京城的选择背后的精神隐秘,相对于罗织苦难的惯常笔墨,他更在意去洞察人物幽微难言的内心,而这赋予他的京漂故事一种别样的诗意。也因此,他笔下那些个卖盗版碟、卖发票、卖假证的道德上有瑕疵的小人物总会因为他们内心的某种坚持与善念而得到我们的谅解和宽恕。《如果大雪封门》是小说里从南方来的京漂小伙林慧聪的高考作文题目,虽然高考一落千丈,但不妨碍他千万里北上寻梦,为了一个与从未见过的雪花的密约,他在北京清冷的冬日仔细地侍弄着一群信鸽。因为鸽子而与打小广告的叙述者“我”建立了友情,虽然“我”的两个伙什总在觊觎他的鸽子并伺机偷猎。小说起名“如果……”但结尾时让“如果”的假设出人意料地落到了实处,似乎这次作者本人善心发动,要帮他可怜的主人公圆梦了。“大雪封门”的北京虽然不像林慧聪期待的那样如童话世界一般“清洁、安宁、饱满、祥和”但自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让小林无比满足。只是,作者在收束时又看似轻描淡写地提到另一个期待看雪的京漂小伙宝来,而开头时作者告诉我们,他已经因为脑子被打坏而被送回了故乡。这个没有展开的故事分明为我们呈示了林慧聪的另一镜像,还让故事貌似温暖的结尾有一个清寒的回声——不用死劲实写的苦难原来更有内暴力!
补评:在乡村的挽歌声中上演
城市的舞蹈
王 琦
鲁敏《字纸》,《北京文学》2012年第10期
近几年,鲁敏一直在尝试从小镇“东坝”走向城市,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文学元素,发掘都市人的暗疾。这篇小说虽然延续了她之前的路,却在境界和视野上有了更大的扩展,从揭露人性的暗疾上升到揭示社会发展的暗疾和疼痛。主人公老申是一个爱字纸成痴的老人,这种爱发源于文化短缺的童年记忆。小说开头从擦屁股纸这一独特的生活意象入手,回顾了大跃进时代物质短缺文化更是稀缺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申将带有分数的试卷和带有钱数的帐页都快乐地使用掉,却不舍得用掉一张报纸,在他朴素的内心中,名和利终将归于尘土,只有文化应该得到尊重和继承。小说接着从历史的记忆回到现实当下,晚年的老申依然保有对字纸的热爱和敬畏,他从不浪费一张字纸,在精心的阅读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然而一次儿子带他到书店的经历摧毁了老申的精神高塔,现代文明的海量信息和新型传媒让老申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井底之蛙,他明白自己过去尊崇的字纸在当今社会早已成了垃圾,痛苦和失落之后他选择拒绝与这个信息社会交流,守着一堆废纸祭奠过去。小说表面描写一位极端人物的痴,实际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切身体会。老申对字纸的虔诚和精读的习惯来源于文化不发达的传统乡土文明,现代城市文明的信息爆炸和传播技术对人的传统精神造成致命冲击,面对这样的心理失衡老申的策略是逃避和退守,以祭奠逝去的传统文明。现代文明的进步虽然伴随着老申一类人的阵痛却是大势不可回,传统文明只能如小说结尾的字纸化为散片消散在历史当中。作者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剖析一针见血、微言大义,高超的细节捕捉能力和独到的社会体察能力使小说言简而意远。
张惠雯《流逝》,《莽原》2012年第5期
张惠雯过去的小说大多灵性十足,形式新颖,然而这部作品写法传统,格调沉重。小说讲述了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两个孙子因为挖沙船过度采挖留下的沙窝溺水身亡,他们的祖父母觉得无法向远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交代也随即赴水而死。这出悲剧的造成是人们追逐利益的结果,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更是传统乡村被破坏的必然结局。小说没有像启蒙作品一样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控诉,也没有像社会分析小说一样对社会问题的本质进行理性的批判,而是从祖父叶老汉的视角出发,用朴素懵懂的眼光打量乡村的变化,用几乎中性的语调叙述这个悲剧。只在小说的结尾用串联小说始终的河流意象,象征性地点出作者的思考:“而河流,它就这么一如既往地向着远方流淌,带走那些老人和孩子,带走那些村庄的往昔和未来,留下破败、废弃和荒凉”,历史长河的流逝是生命的流逝,也是诗意乡村的流逝,正像叶老汉的回忆一样,传统乡村文明经历过朝气蓬勃的青壮年已经在城镇化的发展大潮下变得像老人一样衰败、残破,也必将像他们夫妇那样最终走向死亡。小说用朴素的情节、简单的顺序叙事、平白细腻的文字,呈现出悲凉深邃的小说意境。
盛琼《星期天公园》,《作品》2012年第10期
星期天公园是作者的一段童年美好记忆。儿时几乎每个星期天,主人公我和家人都会精心准备妥当然后到星期天公园游玩,我们游戏、野餐、唱歌、跳舞、拉琴、听广播,陌生的路人也会加入到我们的歌舞当中,一起分享快乐。那时是八十年代初期,人们从狂暴的政治运动梦魇中醒来,满怀拥抱新生活的理想和热情,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富足,但是精神生活很充实,人们精神焕发、热情友善、热爱自然,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和谐发展,星期天公园正是当时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的一个缩影。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和金钱洪水般地侵占着人们的生活,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人心却被利益束缚和扭曲,人们争名逐利、互相防备,人际关系隔阂,生活的压力夺去了人们的笑声,我们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星期天公园玩了。小说语言细腻柔婉、活泼生动、充满童趣,采用儿童视角和散文式叙述为星期天公园唱一曲挽歌,记录逝去的美好生活,控诉拜金主义对快乐的侵占。
刘庆邦《路——保姆在北京之六》,《花城》2012年第5期;《榨油》,《江南》2012年第5期
刘庆邦过去的作品,一半写的是矿区,另一半是乡土,关注的是社会底层小人物。如今他第一次将目光从记忆中的煤矿和乡村转向现代生活的北京城市,关注城市的内涵,并且从城市中的一类特殊人群保姆来观察这种内涵。保姆从乡村来到城市,带着乡土文明的眼光打量城市文明,两种文明的碰撞常常产生一些戏剧冲突,而这就是刘庆邦保姆系列小说的切入点。《路》讲述的是青海小保姆吴启雪初中毕业就辍学来到北京的赵教授家当保姆,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赵教授车祸后残疾的儿子练习走路。吴启雪在和陶老师的作文交流中体会到城市人和农村人一样有着内心的痛苦,农村人的苦来自贫穷,而城市人虽然物质生活富足,但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使人生的命运像天气预报一样没有准信。所以人生的路要继续走下去就需要相互扶持,城市和农村应该打破二元对立,互相借鉴帮助,才能获得双赢的发展。小说结局给了城市生活一抹温情,吴启雪在赵教授一家的帮助下圆了上学梦,而赵教授儿子的身体也在吴启雪的照料下有了起色,城市文明在接纳乡村文明上体现出包容。《榨油》写的也是北京保姆,不过和吴启雪不一样,周玉影在城市的金钱欲望中迷失了自己,她处心积虑地勾引老板的父亲韩老爷子,从服务员做到保姆,再到情人,最后成为韩老爷子的妻子。她贪得无厌地榨取着韩老爷子的金钱,并在遗产的诱使下榨干了他的身体,把他送上了死亡之路。韩老爷子作为城市人也有着过分的欲望,他贪恋美色而且精打细算,用一张遗嘱彻底将周玉影的幻想破灭。这篇小说揭露的是城市文明的黑暗一面,城市中泛滥的欲望洪流不仅席卷着城市人,也改变着涌入城市的农村人,金钱和身体的欲望在城市的温床上不断膨胀,膨胀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不论是周玉影还是韩老爷子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这两篇小说题材相同,基调却不同,分别揭示着城市温情和丑陋的两面,结局都意味深长,颇具寓言色彩。小说语言纯熟朴实,透着浓浓的市井气息,像老北京的评书,也像北京人的唠家常,从语言到人物都紧贴着地气,毫无都市的浮夸之风,体现着一个成熟作家的稳重。
薛舒《诗人或女人》,《作品》2012年第9期
艺术创造怎样在世俗生活的挤压中生存?这是小说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主人公苏秀秀是一个执着得有点极端的女诗人,她拒绝婚姻和生育,排斥物质生活,追求自由和诗。在她的身上作者思考着文学和商品、精神满足和生理欲望、艺术创造和世俗生活的关系问题,也许小说题目“诗人或女人”而不是“诗人和女人”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二者是对立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小说通过一个女诗人的生活缩影,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世俗化趋向和文学式微的处境,揭示了世俗物质生活对精神文化创造的冲击。在二者之间,女诗人选择了后者,然而精神生活难以完全脱离物质生活,她对邻居老莫的依赖和最后前夫回归的情节都说明了这一点,小说结尾包裹着婴儿的彩蛋意象进驻诗人的头脑和心脏也象征性地写出了二者具有部分依存关系。虽然女诗人不得不向物质生活部分妥协,但是绝不投降,她将钥匙还回并与前夫保持距离就是为了和世俗生活分立,保持精神的独立性。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独白叙事,语言戏谑调侃,有时妙趣横生令人发笑,但是笑过之后又不免思考: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女诗人遗世独立的意义何在?人类的生物生命通过繁衍后代而复活,那么人类的精神文化靠什么延续呢?或许靠的就是女诗人这类不与现实妥协的文化工作者的执着坚守。
周新天《拔河记》,《雨花》2012年第10期
近年来,反映官场腐败、政治黑暗的官场小说一度成为文坛热点,这既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与政治难解难分的因缘延续,也是当下社会政治腐败、体制僵化的一个缩影。周新天写官场虽然也揭露腐败,但他没有疾言厉色地批判或声嘶力竭地控诉,而是选取了一个小人物的小事件,用幽默调侃的笔让读者在笑声中自己发现问题。主人公左冷禅是在步行街做管事的警察,他膀大腰圆、威风凛凛,公安局这样体格的警察还有很多,所以他们在市级机关运动会的拔河比赛上出尽风头,但在长跑活动中颜面丢尽。公务员庞大体格的背后是请客吃饭成风的官场恶习,作者没有简单粗暴地批评他一个人或一类人,实际上左冷禅除了食欲泛滥之外也算是一个好警察、好人,问题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官僚体制和社会传统陋习。小说像一出笑料频出的喜剧小品,语言凝练、情节精彩、人物生动,幽默的故事反讽沉重的社会问题,获得令人深省的效果。
王秀梅《鱼咒》,《青年文学》2012年第9期
王秀梅是位虚构的高手,她擅长塑造寓言化的意象,编织奇诡的梦幻,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情感倾向和理性思考,使小说具有象征意味。《鱼咒》是一篇聊斋式的魔幻小说,作者通过自己的敏锐观察和奇诡想象,从鱼摊杀鱼这一日常场景出发换位思考,用鱼的情感审视人,与人的视角互映,虚构了一个鱼诅咒人,最终人变成鱼的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呼吁环保,更重要是通过鱼和人的世界沟通比较,表达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一种思考。人生在世必然受到金钱、名誉、道德等种种社会规范的束缚,常常感到压抑和苦闷,就像肖老大因相貌和职业而爱情受阻,李成就经历事业和感情的起伏对生活产生厌烦,他们对变成鱼并不恐惧,反而淡定甚至期待,他们向往鱼一样自由自在没有束缚的生活。然而人毕竟是社会动物,离开社会也难以生存,两人变成鱼后虽然自由却倍感无聊,所以肖老大最后选择回到岸上接受命运的安排。小说以肖老大的独白叙事,通过人变鱼这一超现实的情节,打破现实和梦幻之间的界限,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人,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
邵丽《树上的家》,《山花》2012年第10期
题目“树上的家”具有一语双关的作用,既是指孩子的玩具,也是天真的孩子对幸福的家的期盼。玩具的拼装离不开一家三口的共同合作,一个真正温暖的家的维持也离不开三个人的携手努力。然而小说主人公和妻子准备离婚了,玩具家可以拼好,现实的家却行将破碎。主人公夫妻为何离婚小说没有交代,但是从小说描写的家庭日常生活状态来看,他们没有争吵,只有冷漠和僵持,各自忙着各自的事业,置家庭于不顾。他们都是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不肯承担家庭的责任,把家庭破裂的伤痛无情地抛给年幼的孩子和年老体弱、为子女操碎心的母亲,读来令人唏嘘和心酸。小说截取离婚前一夜的家庭生活场景,用细腻流畅的笔记录人物的日常活动,在细节的描写中把握人物的主要特色,出场人物虽多,但作者极为节省笔墨,所有情节均点到为止,只用寥寥数笔就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借助琐碎的生活细节准确地表达出来。
朵拉(马来西亚)《朝花夕拾》,《北京文学》2012年第10期
这是一篇由海外华文作家编织的爱情小说,三对男女的爱恨纠缠讲述着一个爱情与背叛的陈旧话题。小说通过线索主人公夏曼瑜的视角将三个故事巧妙地穿插在一起,有详有略、有点有染、互相映衬。夏曼瑜的父亲年轻时候抛妻弃女,母亲独自将两姐妹养大,后半生空对着父亲留下的夹竹桃伤怀;姐姐遭遇相同命运,因为姐夫外遇而离婚,自暴自弃下做了别人的第三者;夏曼瑜采访的画家夫妇貌似恩爱的爱情童话背后竟是赤裸裸的阴谋和伤害。人性是自私、丑陋、变幻莫测的,人与人之间的背叛导致了人心的寂寞和多疑,连爱情神话都已破灭,专一、永恒的真爱还存在吗?夏曼瑜表示质疑。小说采用象征写法,一树夹竹桃花贯穿始终,花朵美艳却有毒、朝开夕落、开时随意,象征着爱情美好背后的丑陋、短暂和多变。小说写作手法简单,主要通过人物对话叙事,只是穿插上了夏曼瑜的心理感悟,夹叙夹议,给苍白的文章添加上一点理想的色彩。虽然她的爱情感言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她对爱情和人性悲观消极的态度使文章悲情绝望的氛围萦绕不去。小说虽显老套,但爱情是永恒的文学母题,爱情中的背叛是吟唱不完的一曲悲歌。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