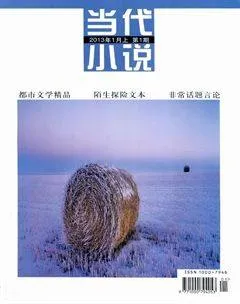小说二题
草手镯
1988年4月的一天,年轻的柳小惠坐上了张成林的自行车,自行车像个喝醉酒的汉子一样,歪歪扭扭地驶在了十八盘崎岖的山路上。这一天,是23岁的柳小惠和28岁的张成林新婚之日,然而除了满岭上花白如雪的刺槐花外,却再也看不见一点新婚的喜气。
时至今日,我对姐姐柳小惠当初和张成林的那段婚姻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张成林并不是个优秀的青年,无论是从外貌上还是家庭上,都难和柳小惠相般配。柳小惠没结婚的时候是我们这东山沟里十村八庄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在她刚满20岁的时候,提亲的人便络绎不绝纷至沓来我们家,其中不乏城里的正式工人和学校里的公办教师,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农业户口的分量有多重,而柳小惠只是个连高中都没上过的农家女。我爸是村里的技术员,但我们家真正说了算的人是我妈。我妈一拨接一拨地接待了来提亲的人们,并严格地按照她的条件筛选出了她比较满意的人选不下二十个交给柳小惠。张成林当时也是求亲大军中的一员,他的婶子曾两次来到我们家为她的侄子求亲,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在第一关就被我妈挡在了门外。我妈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张成林是个长相并不出众的大龄青年,他的家景也远不能同我们家相比,他又没有非农业户口的支撑,综合他的条件,在求亲的队伍里最多也只能排在中下等,他之所以也敢来我家求亲,在我妈看来那纯粹是自不量力的异想天开。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妈的意料之外,柳小惠对我妈交给她的那些人选看也不看就提出了要嫁给张成林,而张成林的资料我妈并没有交给柳小惠,这就使我妈感觉到了一丝奇怪。我妈便展现出她少有的温柔面,慈母般苦口婆心地对柳小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而柳小惠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却出乎意料的坚定,任凭我妈磨烂了牙齿她也不为所动,大有非张成林不嫁的态势。这使我妈很恼火,立马又恢复了她铁娘子的作风,她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地把柳小惠反锁进房间里,准备以强硬的手段逼其就范。这样关了两天,谁也没有退缩的迹象,局面就有些僵持起来。直到两天后的中午我妈又打开房门去给柳小惠送饭,一进门觉得有些异常,房间里寂静无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腥臭,我妈急忙走进柳小惠睡觉的房间,一眼就看见了柳小惠嘴吐白沫倒在炕上,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一只盛装“敌敌畏”的瓶子滚落在一边。我妈尖锐的嚎叫声引去了我爸他们,几个人急三火四地把柳小惠送到医院。幸好发现得早,加上敌敌畏的杀伤力不够,柳小惠被医生将胃翻了个后才活了过来。但经过这次事情,柳小惠的名声就不是那么好听了,各种流言蜚语甚嚣尘上,她的名声也一落千丈,往日里那些提亲的人一下子从我们家门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面对迅速冷落的门庭,我妈初时还抱有一丝幻想,但几天后她就认清了形势,于是主动出门去寻找当初那些上门提亲的人,但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大都避而远之,而那些当初不入我妈法眼的小子们却也在犹豫不决的取舍之中。一向要强好胜的我妈终于在数次打击下头破血流气羞交加,大病一场。病中的她指着柳小惠说,滚,你滚!柳小惠就乘势嫁给了张成林。柳小惠的出嫁也是当年我们十庄八村热议的话题之一。因为我妈是用一种驱赶的方式把柳小惠嫁出去的,所以柳小惠出嫁那天我们家并没有一个宾客。不光如此,由于羞于见人,我一向强硬的妈和当技术员的爸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蜷缩在屋里任由骑着自行年来迎亲的张成林把柳小惠扶上车带走了。我妈没有给柳小惠准备什么嫁妆,柳小惠是背着一个花布包袱坐在张成林的自行车上离开家的。那时正是四月初,十八盘岭上开满了花白如雪的刺槐花,浓郁的刺槐花香弥漫了整个山谷。而当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消失在十八盘后的那片山脚时,一对渴望爱情而又愿为此而抗争的青年人终于真正地走到一起了。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柳小惠和张成林这一对自由恋爱的典范,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痛苦之后,他们今后的婚姻生活肯定会和谐甜美,相敬如宾。
然而,婚后的柳小惠过得并不幸福,因此她拼死捍卫自己婚姻的举动就更加让人匪夷所思。柳小惠结婚一年多了也没有再回到我们家一次,虽然她的新家距我们家只有不足十里路。不是她不想回来,是我妈不让她回来。我妈已经扬言不认这个女儿了,所以当那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张成林依俗带着烧鸡和月饼来孝敬丈母娘的时候,被我爸手持一柄铁锨门神似的挡在门外,我妈没说多话,只说,快滚!再不走就揍你!张成林仓惶地放下东西扭头骑上车子飞一般地去了,我妈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踢飞了那只烧鸡,引来了村中两只恶狗的一场厮杀。这种敌对态势一直维持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在柳小惠结婚后的第二年夏天里出现了转机。有一天我们村有一个我叫二奶的人回娘家,她的娘家就在张家庄,回来后看见我妈,二奶说,我看见你家惠了。妈说,管她什么样,死货,死了才好。二奶说,怪可怜的,还真是死了才好。我妈的脸色就不对了,问二奶,你看见什么了?二奶说,人啦,人瘦了啦。二奶说着伸出两只手比量了一个不大的圆,腰就这么细,脸也不成样,脸上还有一块青……二奶看我妈有听她说的意思,又说,听说是张成林打的。这时我妈“哟”的一声嚎啕起来,她一边嚎一边往家里跑,嘴上叫着我爸的名,快,带上把家什,叫上老三,上张家庄……
张成林所在的张家庄离我们村并不远,转过十八盘岭就到了。我爸叫上我三叔还有大明哥等本家十多个人,坐上柳树林的拖拉机,浩浩荡荡地向张家庄奔去。我妈站在车头上,一手扶着车栏杆,一手向前有力地挥舞着,她威风凛凛气势汹汹,就像电影里的女大王。车人浩浩荡荡冲进了张家庄,在张家庄村人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找到了张成林的家。柳小惠正坐在院子里扒苞米,她瘦瘦的胳膊上筋骨齐露,就像她手里没有粒子的苞米棒,她的脸上果然有青紫的伤痕,她的眼睛因为脸太小了而显得格外得大。柳小惠看见冲进来的一帮人,她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当她看清冲在最前面的是我妈和我爸时,她竟没有一丝反应。
我爸看了看柳小惠,一句话没说就手持铁锨进了屋,他在屋子里找了两圈没有找到张成林,挥起手中的铁锨将墙上的大镜子敲了个粉碎,玻璃破碎的声音刺激着我爸和我妈,他们指挥着随后跟进来的人说,砸,使劲砸,砸死这个XX的王八蛋!随后在一阵刺耳的破碎的声中,张成林和柳小惠的家被捣了个粉碎。
而这时柳小惠就孤单地站在院子中心的一大吊苞米棒前瑟瑟发抖,她的院子外围拢来许多看热闹的村里人。她的院子边上没有围墙,看热闹的人围成一圈相互拉扯着欣赏着房间里的战斗。并没有人出来阻止,在张成林和柳小惠的家被捣了个差不多的时候,人群中才推推拉拉走出来几个年长的老者。他们是张成林的父母和村中的老人,显然他们已经弄清了来袭者的身份,所以他们并没有叫嚣着理论而是以一种近似文明的方式来协商解决问题。这种以柔克刚的招式给了正怒火中烧的我妈和我爸软绵绵的一拳,让他们把准备好的许多恶毒的语言都憋在了心里,差点把自己憋死。他们只好大骂张成林,说张成林你这个XX的王八蛋滚出来。但显然张成林已得到了信息,自始至终没有露面。在经过一轮言语交锋后,我妈把柳小惠拖上了柳树林的拖拉机,在张家庄的众目睽睽之下把她带回了我们家。在拖拉机开动的时候,我妈恶狠狠地给张家庄的老少丢下了一句恶毒的话:早晚弄死XX的张成林。
柳小惠终于回到了阔别快两年的家,到这时候人间的亲情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回到家后的柳小惠足不出户,我妈一边骂她一边杀鸡炖肉做好吃的给她补养身体,不出几天,柳小惠的脸上就有了红润的光泽。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班长的功劳。在柳小惠回家的第二天早上,部队上的一班长来借我们家的锸镢,说是要刨菜园种大白菜。一班长所在的连队就在我们村东边的山里,连队里有菜园还有猪场,他们人多工具少,所以劳动时他们常到驻地村民家借用农具,当然他们也会帮助农户做一些农活,比方说帮助孤寡老人挑水,农忙时节帮忙村民割麦子剥玉米等等,军民情深,鱼水之情。一班长姓姜,是个南方人,但我们只叫他一班长。一班长在部队上干得不错,听说要提排长了,平常日他经常来我家借东西,和我们家人都很熟。一班长进来的时候,柳小惠正坐在院子里发呆,一班长说柳小惠你回来了?柳小惠抬头发现一班长站在她面前,脸立刻就红了,呆呆地不说一句话,一班长抬抬手想做个什么动作却又放下了,说小惠你瘦了。柳小惠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哭着跑进了房间,把一班长晾在院中,神色极为尴尬。我爸说看这个没教养的孩子。就把锸镢递了过去,一班长笑笑扛上锸镢走了。傍晚来还锸镢的时候,一班长带来了两盘东西,初时我以为是向日葵盘子,仔细一看,吓了我一跳,竟然是山上经常见到的马蜂窝,这两盘蜂窝上面星罗棋布的巢房内还长满了白白嫩嫩的胖蜂蛹。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这东西,我不相信居然还有人敢去摘马蜂窝。我看看一班长脸上,果然发现他的额头上还有脸腮上有几处鼓鼓的包。我妈看着这些蜂窝说,我的天,你从哪弄来这些东西,没被马蜂蜇着吧?你也真敢下手。一班长说,没事,我在家时养过蜜蜂。又说我妈,把这些蜂蛹蒸了给柳小惠吃,好补身体。以后几天,一班长又送来了两次马蜂窝,这样过了十多天的样子,柳小惠的脸上果然恢复了不少的光泽,她的腰身也丰满起来。
这天柳小惠说在家憋得慌,想出去打猪草,就提着条篓和镰刀上山了。傍晚回来时她拐着满满一篓子青草累得脸红气喘,我妈说你身体刚见强就不能少打点?柳小惠微笑着说,以后打猪草的事就交给我吧。这是她回家后脸上第一次有了笑的模样。我妈说那行,以后打猪草的事就归你吧,也好让你弟多写写字。柳小惠的弟就是我,那年我十二岁,我是计划生育新政下的幸运儿。我听了挺高兴,终于可以不打猪草了。
但我还没高兴几天,一天傍晚,柳小惠回来时把篓子一放就进房间躺下了,她说不舒服,我妈问她哪不舒服,她说哪都不舒服。第二天打猪草的事又归了我,我挎篓上山的时候看见了一班长,我说一班长又在弄蜂窝啊?一班长说,我给连里打猪草呢,你这是干啥?我说我也打猪草呢。一班长笑了说,我看你不用打了,把我打的装些回去就行了。我一看,一班长已经打了高高—堆的青草了,估计我装他一篓子也没问题。我高兴地说那行。我就坐在树阴下乘凉,一班长还在埋头割青草,我说一班长,都打这么多了,快风凉风凉吧。一班长听了就走过来坐下。我问他,一班长听说你要当排长了,是真的吗?一班长说,当个屁,本来还指望着,可突然就不从基层提了,都是从军校下来的,白忙活了这些年。我今年就复员了。我说,什么时候?一班长说就这几天。我说那你还干个屁。一班长说,站好最后一班岗吧。我说,你不用回去算了,就在这里找个媳妇结婚。一班长说,你小孩伢伢懂啥啊?又说,早知道当不上排长我还真不如在这找个媳妇呢。我说找媳妇和当排长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不懂,部队上有规定,士兵不能同驻地上的人谈恋爱,要是被发现了,就要受处分,更别说提干了。我说,你是不是看好了哪家姑娘,为了提干就不要人家啦?一班长没回答我,低着头在青草中捡出了一大把长相别致的毛毛狗草握在手中。我觉得我说的有点不好,就改了话题,那你回家了干什么啊?一班长说,我们家是放蜜蜂的,我回家就放蜜蜂。我说蜜蜂吃什么?一班长说,吃花,最好的就是刺槐花。我说那咱这里满山是刺槐花,就到咱这里来放吧。一班长说我也这么想,槐花好啊,酿出的蜜甜还有营养。我说那好,明年我就等你来放蜂,我正好尝尝蜂蜜什么味。一班长笑起来,到时我弄点蜂王浆给你,保准甜死你。我瞅着他说,你说话可得算数。一班长摸了摸我的头说,一言为定。说着他把一只用毛毛狗草编的手镯套在我手上,我看看那只草手镯,毛茸茸的真可爱,用它抚在脸上,痒痒的真舒服。回家时,一班长把我的篓子里塞满了青草,我好不容易才扛回去。我妈看了表扬我,我们这小子,真知道干活了。柳小惠站在门旁不阴不阳地看看我打的草,走过来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丢给了猪圈里的猪。
张成林是在柳小惠回家一个月后来到我们家的。这是他这个当女婿的第一次进我们家门。我爸说,张成林,你坐炕上。张成林说,不用了,我就站地上吧。我爸板着脸说,叫你上炕你就上炕,还吃了你是怎么的?张成林只得上了炕,但他不敢坐实,只用半个腚坐在炕的一角。我爸说,张成林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打柳小惠?张成林看看柳小惠,说我没打。我爸说放你妈个屁,你没打她还是她自己打的?张成林只得招供,嗫嚅地说,我们吵架,吵上火了……还没说完,我爸一巴掌打在张成林的头上,这一巴掌的劲力很大,把张成林一下子从炕上打到了地上。张成林有些急了,爬起来梗着脖子说,柳小惠她……柳小惠叫了他一声,张成林。张成林把脖子低下了看着地,嘴里嘟囔着,柳小惠她……不肯怀孕。听了张成林这句话,刚才还斗志昂扬的我爸和我妈很意外,气焰也立刻灭了下去,在我们这里,女子结婚不怀孕和离婚是两件被人耻笑的事情,不怀孕还不如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而离婚一般就是浪荡女的表现。我妈说,你们没去看看?当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气氛就缓和了。
那天,张成林终究还是重新上了炕,在结婚两年后第一次在我家享受上了当女婿的待遇,他竟然还意外地享受了一点小酒。在吃饭时,我爸和我妈文武兼备地对张成林进行了教育,教育他夫妻间要恩爱,要体谅,要照顾。我妈说,张成林我问你,你娶了柳小惠知不知足?柳小惠嫁给你屈不屈?你还抬手就打,你对得起她吗?张成林一边使劲点头一边痛哭流涕下保证,保证以后再不打柳小惠。我妈又批评柳小惠,既然你已经嫁给了张成林就要一心一意地过日子,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怨不了谁,抓紧的怀个孩子,有了孩子就好了。柳小惠低着头说,我想离婚。还没等张成林着急,我爸先急了,他从炕上跳起来指着柳小惠说,你休想,你想让我们死啊?你这就跟张成林回去。柳小惠说现在不想回去。我爸说你是结婚了的人不回去还能一辈子住在家里?柳小惠一甩脸跑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妈也跟了过去。
我爸重新坐到炕上喝生气酒,张成林在一边看。张成林酒量小,刚才喝了一点脸就红得不行了。这时,一班长进来了,不过他今天有点变样了,他的绿军装上已经没有了领章。我爸招呼他,一班长,这是怎么了?一班长说,我复员了,今天是来告个别。我爸说,怎么复员了,不是要提排长吗?一班长说,没戏了,我要复员了。我爸又给一班长介绍张成林,一甩头却发现张成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下炕了,我爸一叫他,他才猥猥琐琐地凑过来。我爸不满地看看他,对一班长介绍说,这是……还没说出什么,一班长就接了过去说,我知道他,叫张成林。说着转过头冷冷地对张成林说,是吧?张成林看见一班长和他说话,竟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这种卑微的态度让我爸很有意见,但我爸觉得一班长的态度也有问题,毕竟张成林是被他承认了的女婿。一班长也看出了我爸的表情,就对张成林说,正好这儿有酒,我就借酒敬你一杯吧。张成林赶忙说,我不会喝酒。但一班长却像没听见他的话,拿起两个大碗,.倒了满满两碗酒,自己端起一碗,说张成林,我现在不是个军人了,我也当不成排长了,我现在和你一样了。我们喝一碗吧。说着他也不让张成林,一饮而尽。张成林两手抖动着捧起酒碗,神色尴尬地站在那儿,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我爸说,张成林不能喝酒,你看他脸红的,别让他喝了。一班长看看张成林没说话,张成林竟也一仰脖喝了进去。一班长又倒了两碗,说来张成林,好事成双,再喝一碗。说着就把酒又一口干了,张成林却不能喝了,跑到院子里吐起来。柳小惠忽然从里屋走出来,她捧起那碗酒说,姜大成,我陪你喝。我才知道原来一班长叫姜大成。柳小惠说着一口气把那碗酒喝下去了,42度的老白干一下肚,就把柳小惠呛了个泪流满面。我爸说一班长,你看你……我爸没说完,就闭了嘴,他吃惊地看着一班长,一班长的脸上竟然也淌起了泪。后来我爸跟我妈说,一班长真是个情义人啊,走的时候都哭了。一班长哭了,他没有再喝酒,他流着泪离开了我们家。在院子里,他看见了还在呕吐的张成林,一班长伸手在他的肩上用力地拍了一下,就离开我们家走了。
中午的阳光很明媚,太阳穿过十八盘岭上的树树木木直透过来,把柳小惠和张成林的影子都拉短了。他们在前走着,我爸和我妈在后面送。村口那儿正敲锣打鼓欢送复员老兵,老兵们都被摘了帽徽和领章,正往一辆敞篷军车上爬,我看见一班长正站在车斗上向这边张望着。张成林一抬头也看见了一班长,他脚下一歪踩空了差点跪下,被我爸拉了一下才站住。我爸说小心点,看着道。张成林忙架好自行车,骗腿上去慢慢地向前溜,等着柳小惠坐上去。柳小惠并没有马上上去,她跟在车后慢慢走了一段路,没有回头,忽然伸出一只手来举在空中挥了几下向我们告别,我发现柳小惠的手腕上竟也套着一个毛毛狗草编的手镯。我刚想说柳小惠,你是不是拿了我的草手镯?柳小惠已紧走几步上了张成林的自行车,张成林弓着腰,双脚猛蹬几下,自行车逃似的远去了。而这时,送老兵的军车也启动了,我看见一班长也把一只大手伸在空中向我们挥别,他的手腕上居然也套着一只草手镯,他和许多老兵一样,脸上也挂满了泪珠。车子向前走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我追着车子跑了几步喊,一班长,明年刺槐花开的时候你会来吗?一班长大声喊,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的——
他的声音很宏亮,穿过几条山谷都听得到……
在拐弯处
在我20岁的那个夏日里,我和水皮还有大涛三人坐在“美美”烧烤店前喝啤酒。烧烤店的女老板叫高美美,比我大两岁,人长得风骚,性格又豪爽,所以她的店前总是人最多。那几天,天气出奇的酷热,我和水皮还有大涛三人已经喝了整两箱了,空瓶子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水皮还在大叫:“高妹儿,再来一箱!”
我们总是叫高美美叫高妹儿,每次叫高美美“高妹儿”时,我们都会听见有人笑,这时我们心里就觉得特别爽。高美美答应着往后走去搬酒。这时我肚子胀得难受,起身歪歪扭扭到后面去上厕所,拐过弯,看见高美美正撅着个屁股在搬酒。高美美穿着个黄色的小短裙,一弯腰露出了两条雪白的大腿和半个屁股。本来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不该对她有什么想法。但那天我的酒真是喝多了,就走上前去从后面抱住了她。高美美“嗷”的尖叫了一声,挣扎着要反抗,回头看见是我,她不反抗了,只是轻轻地扭着身子做样子,嘴上却嗲嗲地说:“放开我,放开我……”本来她要是真的不从我可能也就算了,但她这样说话却更是给了我莫大的刺激,我就半拖半抱地拉她往另一间屋里走,高美美扭动身子挣扎着配合我,她的大奶子在她的扭动下像两只欢快的兔子不停地跳着,她的脸红红地贴在我的脖子上,嘴巴里、鼻孔里喷出一丝一丝暖暖的热气直往我的脖领子里灌,让我更是激情冲天。我把高美美扔到床上,就要脱她的衣服,这时我腰里的传呼机响了。在那个时候,通讯工具不是很发达,手机是很少的,传呼机也不多见,所以有手机的人就在手里提着,有呼机的人就把呼机挂在腰上,这是身份的证明。
高美美说:“有人找你了,快看看又是哪个妹妹吧。”
“去他妈的吧。”我把呼机拿出来摁了一下扔在床上,呼机不响了,我仍去脱高美美的衣服,可能因为是夏天穿得少的缘故,高美美的衣服一下子就被我脱下来了。这时呼机又响了,我不去理睬,又去脱高美美的裙子。高美美一边装模作样地用手去挡一边伸手拿过呼机看了,笑起来:“哪来个250啊,就这天还东北风啊。”起初我的神经被肚子里的酒精和一副浪样仰在床上的高美美刺激得云里雾里的,没听清她说的什么意思,但嘴里还是顺口问了一句:“谁发的?”
高美美又看了看呼机说:“刘大哥。哪个刘大哥呀?”
似乎真的感觉有一股风掠过,我脑袋有些醒了,松开去摸高美美的手,抢过呼机翻看留言:“今天东北风。刘大哥。”两遍一样。我的激情一下子荡去了,酒也清醒了大半,我知道我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推开了缠上来的高美美向外冲去:“我得走了。”
我想我当时冲出门时的速度一定是神速无比的,因为当我最后一个字还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站到店前的门口处了,这时我看见水皮和大涛正一人手持一瓶啤酒在“拼刺刀”。我正要喊他俩,突然一声刺耳的警笛在店前炸开,只见店前停着的几辆车上同时冲下十多人,谁也没注意,什么时候店前就来了这么多车。车上冲下来的人直接就把水皮和大涛摔在了地上,有几个人冲到后院去了,我想那肯定是在找我。我低头拾起门边的一把笤帚,装做做清洁的服务员,几个人影快速地从我身旁穿过去了。
突发事件让一九九八年夏天的“美美”烧烤店前的食客们“哄”地就炸了锅,跑进跑出的人还有满地乱滚的酒瓶子使场面混乱不堪,我趁机混入乱哄哄的人群中,消失在小巷中了。穿行在小巷中时,我的头脑异常清醒。我清醒地知道,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署名“刘大哥”的这条留言无疑已经为我们的幸福+an9sOnx6levfno1NqKNrQ==生活划上了一个句号。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这条留言只有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才允许使用的,相当于战时的明码电报。
我知道我今后的日子将会是异常艰难的。果然,随后的日子里我就如同一只被猎人追赶着的兔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发现危机四伏。我给眼镜打电话时,他还在家里吃饭,在我刚到达眼镜楼下的那个胡同时,我看见两个警察架着反手被铐的眼镜从楼上拖下来扔到了车里,身后追着他快八十岁的奶奶,但警车并没有等她,尖叫着飞驰而去,刺耳的警笛声久久不散,把眼镜奶奶的哭声都拉远了。趴在我们家前面公园的那片丛林中的时候,我看见一大群警察堵在我家门口,其中一个警察还不停地用手推搡着我年老的父亲,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我年迈的父亲只是摇头,一言不发,而我的母亲却在一旁嚎啕大哭,周围站满了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
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突然发现,在这个经济发达、楼房林立、人口众多的城市里,竟没有一处属于我的地方。而就在几天前,我们还都坚定地认为,我们才是这个城市里的主宰,我们就是这个城市里的主人,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里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地做一切事情。而现在,我们却只能如同一条条丧家之犬,东奔西跑,东躲西藏。
在发现我在这个城市里真的无处可去后,我来到了西河子巷的拐子明家。拐子明在巷口处摆了一个小烟摊,他的一条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平时他就坐在板凳上卖香烟。见我到来,拐子明高兴得都哭了。他已经听说了我们的事情,整个夏天,整个海城的空气都在传送着我们的事情。但拐子明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犹豫和不决,他坚定地把我藏到了他的家中,从此让我这个丧家之犬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
拐子明并不是我们的人,有一次几个地痞来买烟,烟拿了却不给他钱,拐子明就追着他们要。拐子明腿不好,一瘸一拐地追着他们,几个坏小子转着圈子逗他,还把他的烟摊也踢翻了。那天正好我路过,我和拐子明不认识,但看他一瘸一拐地俯着身子去捡散失在地上的烟我就想起了我的三叔,我三叔也是个瘸子,死了两年了。我拦住了那几个坏小子,起初那几个小子还不服,但我一报名号就都老实了,乖乖地赔钱了事。在海城的黑道上,这点名气我还是有的。从此明就视我为恩人。我看他可怜,也偶尔去看看他。
我不想连累他,可我实在找不到可去的地方了。
此后的日子里,我就如一只见不得阳光的老鼠整日蜷缩在明的小窄屋里,看似无所事事,内心却备受煎熬。外面稍有风吹草动,就能让我心惊胆跳半天,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如此胆小,我还是原来那个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东哥”吗?
在这段日子里,明源源不断地给我带来外面的消息,但都是些坏消息。从明嘴里我知道,这次事情的导火索是在衡哥身上。衡哥在政府招待所里为一个女孩子和人打起来了,本来这也不是件什么大事,衡哥和人打架就像撒泡尿一样随便,他进出派出所如履家门。但问题在于和他打架这个人是新来市长的儿子,关键的又是衡哥把新来市长儿子的“那个东西”给打坏了。在某些方面来说,弄了市长的儿子有时比弄了市长本人还要让市长难看,更何况还弄坏了市长儿子的“那个东西”,让市长从此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新来的市长对海城的治安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
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就开始了。在这次全城性的大拉网中,我往日的弟兄几乎无一遗漏,而我到现在还能待在这朗朗乾坤,只能说是个奇迹。感谢高美美。现在再提高美美,我对她除了感激再没有任何一点感觉了。这天,明又带给我一个坏消息: “衡哥被处决了!”我听了眼泪立刻就涌了出来,衡哥这么快就被处决了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知道我也到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对明说:“明,去给我买一张今晚到K城的火车票吧。”
明很吃惊,说:“你要走?现在外面还是挺严的。”我说:“管不了那么多了,再呆下去我会发疯的,是福是祸由天定吧。”
明望着我,最后还是点点头,走了。
明走后,我就想衡哥。衡哥是我今生中见到的第一条好汉,在海城这个地方,再不可能有第二个衡哥了。而现在,衡哥却死了。衡哥,永别了!我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傍晚时分,明回来了,递给我一张火车票,又从腰里拿出一沓钱,说:“东哥,刚才我在朋友家里借了一千块钱,你拿着路上用吧。”
我很感动,明辛辛苦苦一年,也不过就挣个一两千块钱。我说:“明,我这有钱,你挣不多,还是还给人家吧。”
明固执地伸着手,说:“东哥,你一定要拿着,出门在外没钱怎么行?我在家好办,大不了出点力。”
“那好,我拿着。”我拍拍明的肩,努力挤出一副笑脸接过了钱。
吃过饭,时候已经不早了,我站起身。明难过起来,说: “东哥,我送你走。”
“不用,别连累了你。”
“我不怕!”明固执地说着就去拿衣服了,我趁机把那一千块钱又塞到了他的枕头下,然后迈步走出门去。
到了车站,时间还早一些,我们就在车站不远处找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躲了起来。明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叼一支,点了火,我们二人就对吸起来,彼此无话。我四下望望,海城的夜晚,几盏昏暗的街灯照着,人却不少,然而这芸芸众生中却只有明一人是我的朋友了。有好几次,我想对明说声谢谢,但我终于没有说出来。有些话,不说,也许比说了更能让人记住。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看只有几分钟了,把手伸向明,明握着我的手说:“东哥,保重!”我摆摆手,提起行李一步步向检票口挪去。
车站里的检查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严,年轻的女检票员冷若冰霜,对拥挤的人群视而不见,眼睛只是盯着伸到眼前的票,嘴里机械地念叨着:“别挤,排好队。别挤,排好队。”两个穿警服的男人远远地站着,并没有过来。我随着拥挤的人流一起上了车。
在硬卧车厢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下铺靠窗,位置不错。我四下看看,一切正常。等我放好行李后,火车已经徐徐开动了,我就走到车窗前趴在玻璃上往外看。列车正在加速,站台越来越远地向后退去,看着车窗外远远近近一晃而过的灯火和黑黝黝的楼房,我知道我就要离开海城,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离开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去走一条不归路了,而前方等待我的将又是什么?在这一刹那,我的心竟怅怅然生出了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来。
火车全速行驶着,海城已经永远地离去了。我将留恋的目光收回,扭头却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猛一抬头,对面站着的却是明。
“你怎么上来了?”
“我不放心,等你出了省界我再回去。”
我鼻子一酸,说:“你有票吗?”
明得意地亮了一下票指指我头上的铺位,看来他是早有预谋。明坐在我的铺位上,我们说话。我说:“明,不要再同我们这种人往来了,没好处的。”
明说:“同你在一起不是挺好嘛?”我苦笑笑,没说话。明又说:“东哥,其实你可以不走,投案算了,大不了判几年,出来还不照样做人?”
“别说了,明。”我站起身,“有些事你不懂,快睡觉吧。”
明起身往上铺爬去,但明实在是太矮小了,腿又不好,爬了两下都没爬上去。我拉住他,把他按在下铺,自己一跃身上了上铺,躺下身去,将毯子整个地蒙到身上,却不敢真的睡去。我觉得我一直是在半睡半醒中,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像是在放电影,一会儿是衡哥,一会儿是警察,马上又出现了我爸我妈还有高美美,甚至连死去多年的城北大眼狼也出来了。人很多,事也杂,却又乱糟糟的没有一点头绪。无数的人物和镜头走马灯似的晃荡在我的眼前,我的脑子被膨胀得乱七八糟。睁开眼,头顶上的灯已经关上了,车厢里只剩下一点昏暗的光亮,火车正快速行驶着,外面的景物被月色断断续续地挤进来,斑斑斓斓,光怪陆离的,让我一时间恍如隔世。就这样我静静地躺在火车硬卧的上铺上,任思绪自由地飘忽,可能是这几天实在是怕坏了也累坏了,再加上火车反复不止咣当当、咣当当的声音,我终于熬不住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了。下床发现明不在,我去洗脸,对着镜子发现自己这几天憔悴了许多,模样也变了许多,心中颇觉伤感,但一想到就要脱离险境了,我又轻松了许多。
回到座位,明已经回来了,他买回了两瓶啤酒两只扒鸡,我忽然想到下一站我们就要分手了,心中油然而生出一股恋恋不舍之情。我们坐在窗前,一起喝酒吃肉,我说:“明,你回去后可以订点报纸摆在烟摊旁,夏天你再批点冰棍,一起卖。”
明听了眼睛一亮,说:“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东哥,还是你有头脑,等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开个超市。”
听明的语气,好像我这次出走就是一趟轻松平常的旅行,而我,还有以后吗?海城我还会再回来吗?想到这些我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就不再说什么了,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也不说话了。就这样,我们谁也不说话了,谁也不说话。就这样两只鸡两瓶酒在我们的无声无响中落进了我们的肚子里。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要分手了,从此以后,我们将天各一方,也许还能再见,也许就是永别。明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我鼻子也有些酸,却终于忍住了,拍着明的肩说:“别哭了,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明说:“东哥,到了K城不好混你就回来。”
“我有数。”我说:“你也要好自为之,别逞强。有谁欺负你,你不要和他们打,你打不过他们。”
“我知道,东哥,你也保重。”
我忍住泪水,扭头去看车外,车外是一片一片的田野,庄稼早已收过,而新的庄稼还未上来,于是田野就那么一片片的裸露着,匆匆而过。偶尔闪过一两个零落的村庄,有渺渺的炊烟若立若飘竖在天空。远处那些巉峻绵亘的山峦被烟雾笼罩着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显得既神秘且虚幻。望着窗外,看见有树一闪而过,有如匆匆的赶路人,我忽然想,我们就如这车外匆匆的树,一闪就不见了踪影。衡哥是这样,海城的那些兄弟是这样,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急匆匆地赶路,哪里又是我们的终点呢?转过前面的那道弯,就是K城所在的地界了,那里真会有我的世界吗?
突然,明抱住了我,哭着说:“东哥,你不要走,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投案吧。”
我去掰明的手:“别这样,明,好多人在看,会被人怀疑的。”
明听话松开手,但语气却异常坚定起来:“东哥,外面世途艰险,你一个人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我实在不放心,衡哥死了,我不想你和他一样,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投案!”
“明,我不能回去。”我力图劝说明。我的苦衷他是理解不了的。
“东哥,我不让你走,你要不回去,我就跳下去!我就去死!”明说着竟然真的冲到车窗前,猛地掀起了车窗。
“不要……”我抱住明,脑子里一片空白。车外是匆匆而过的田野,村庄,还有一闪而过的树……
我被劳教八年。八年里,明每个月都来看我。明每次来时都背着一大包的东西,硕大的背包压在明的身上,明瘸得更厉害了。一年后的一次探视,明说:“东哥,我们把巷口的那个超市盘下来了,我给它起名叫‘东明超市’。”又说:“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帮你存起来了。”
我理解明的心事。我只是失去了八年的自由,而明付出的或将是一辈子。八年的劳役生活是艰苦的,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没有半点的怪明。我常想:如果没有明那刹那间的冲动,如今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况且,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明从火车上跳下而无动于衷。只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火车上那密封的车窗,明怎么一下子就打开了呢?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