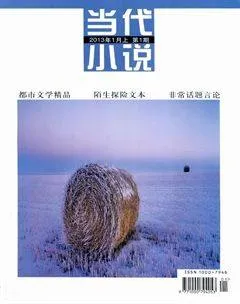漫川谷雨
1
谷雨是镇上的女司机,二十多岁。
镇不大,但很古很旧,青青的石板, 白白的围墙,还有古戏楼翘着飞檐,立在黄昏里。有时,剧团来了, 戏楼上,就会响起咿咿呀呀的汉剧二黄声,还有胡琴和笛子的声音,流散到小镇的角角落落。
镇叫漫川,因为是建在一川土湾上。土湾外是树,柳树最多,长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一根一根的绿线一直扯到水里,水也就绿了一片,清幽幽的。
树的这边,就是公路。
谷雨的车,就在这条公路上来回地跑,织布梭子一样。
漫川镇虽不大,可处在水旱交接处。木船,也有机帆船,沿着水面上来——轮船不行,水浅——到了镇上,就是车路。由上而下的车路到这儿,一分两处,向下走去,愿坐船的坐船,愿坐车的坐车,随便。
这儿的人因为这也就慢慢稠起来,小楼商店,酒吧宾馆,一个挨一个。人一多,车也就多了,向上,三百里是省城。向下,不到百里,就是外省,也是一个名镇,叫上津,也是黑瓦粉墙,石板小巷,和漫川如一对孪生姐妹。两镇于是联起手,趁着旅游热,打造起双镇一日游来。
广告一打,小镇上,更是游人如织。
小镇没车站,一个个司机都开着车,停在车路旁,使劲地叫喊着,去上津的,请上车。喊着不算,还热情地拉,甚至,给客人提包拿行李,服务到位。
这些司机中,谷雨是个例外。
谷雨披着头发,红唇亮眼,扭着细细的腰肢走到车路旁,停了车,软绵绵地喊一声,去上津旅游的客人,上车哦。那个“哦”字,扯得长长的,仿佛还泛着薄荷味。“哗”一声,车子就满了,有女乘客,但更多的却是男的。谷雨笑了笑,对那些个司机一挥手,说,先走了。一样的腰肢一扭,上了车。车子“呜”一声,向下驰去,很快地,如一条银鱼儿,消失在水一样的阳光中。
阳光,也仿佛泛出一丝丝粉色的涟漪。
那些司机都伸着脖子,向谷雨驶去的方向望去。不一会儿,啥也看不见了,只有一条路在延伸,一条水依着路,平平展展地向下流去。水上,有几只船儿向下面驶去,有人打渔,网撒下,再捞起,有几尾鱼儿在闪亮。
一个司机回过头,吐了一句,这个谷雨,妖精。
另一个道,瞧那鼓鼓的胸那胖胖的腚,勾引客人呢。
前一个回道,当然,谷妲己嘛。
一群男人听了,就嘎咕嘎咕地笑了,心里的气也泄了一些。随后,一个又一个拉了客人向上津驶去,留下的只有小镇,在一片水色的围绕下,静静地卧在阳光下。
镇后的寺庙里,钟声响了,沉沉地,漾入阳光中,一圈又一圈,仿佛波纹一样。
2
谷雨不是小镇人。谷雨的家,离小镇五十里,在山里,一个叫塔元的地方。塔元这地方,绿树成阴,密密丛丛,并没有塔。听老辈人说,过去是有塔的,后来被人扒了,一共五座,呈梅花状竖立。
塔没了,可塔元还是塔元,叫得有名有姓的。
谷雨的家,在塔元村的中间,一窝儿树,几间白粉房子。谷雨嫁过来,和男人良志一块儿上坡种地,下田栽秧;一块儿回家做饭。天黑了,唧唧哝哝看罢电视上了床,把那事儿也做得有滋有味,其乐无穷。
但是有一天,谷雨蹲不住了,想去镇上了。
谷雨要去镇上,是因为荷子。
荷子和谷雨是邻居,也是好姐妹。荷子近几年不在家,和男人山子一块儿去了镇上,经营起生活。山子借钱买了一辆小面包车,专门拉人。荷子也没闲着,开了一爿小铺,卖个针头线脑日用百货的,还别说,小日子过得水响磨转的,很红火。
前两天,荷子回村了一趟。
山子开着车,两口子一块儿下了车。谷雨简直认不出荷子了:披肩发,长长的眉眼,白白的脸儿,穿着白裙高跟鞋,把一村小伙子的眼睛都点亮了。荷子一笑,红了脸,还没改变过去那种害羞的样子,拉着谷雨的手,唧唧哝哝没完没了。
晚上,谷雨就提出,和良志一块儿去镇上做生意。良志正忙着呢,顾不上回答。谷雨生了气,一脚,把良志踹了下去,问,我说的话听到没?
良志哎呀一声,爬起来问,啥哩?
谷雨气得一翻身,向里睡着,给了良志一个脊背。良志急了,爬上床来,求爹爹告奶奶,问啥事哩?好谷雨,你倒说是啥事哩。
谷雨说,我们去镇上。
干啥哩?咋活哩?良志愣了一下,苫兮兮地挠着脑袋问。
谷雨忽地坐起来,说荷子都行,我们就不行?有双手,到哪儿也能活!
在家中,良志当不了家,谷雨定的,良志不愿意也得愿意。几天后,小两口就来了镇上,谷雨高兴得嘎嘎地笑。开始的时候,摆了个豆腐摊子,是荷子和山子牵头找的。摊子的地位很偏,在一座拱桥边上。这儿的人爱建桥,遇水就架,有木桥、石桥,更多的是水泥桥。
由于摊子靠桥,一边被水挡着,荷子怕生意不好,说,只有这儿了,先做着,以后再找一个好一点儿的。
谷雨点点头,搭起了摊子。
谷雨也学起小镇女人的装束,一头披肩发,一条超短裙,一双眉眼亮亮的,笑也不嘎嘎的了,而是咯咯的,小母鸡下蛋一样。见人来了,谷雨一笑一点头问,买豆腐吧?来一斤。一天下来,卖了五十多斤。第二天,增加到一百多斤。
谷雨的生意竟然一点儿也不冷清,相反,还很红火。
荷子听了,特意赶来看,看着看着,看出了门道,悄悄拍了一把谷雨的肩膀,附着她的耳朵,悄悄叽咕了几声。谷雨咯咯笑了,说,胡说啥呢?不会的。
荷子说,真的,我看出来哩。
谷雨眨着眼睛想想说,让你一说,我想起来了,现在电视里干啥都有模特,有手模,还有车模哩。看荷子望着自己,眼睛里罩满了疑惑,就说,你傻啊,我就做个豆腐模特啊。说完,也把嘴对着荷子的耳朵,悄悄嘀咕了几句。荷子脸红了,拍了她一巴掌,悄声道,亏你想的,那不卖色相吗?
现在,那是时——时髦,叫模特。
荷子摇着头,说你——坏的。说完,走了,沿着石板街巷,向远处走去,一边看着墙头时时冒出的花儿,或栀子花,或一挂紫藤。身后,是谷雨的叫声,豆腐,水嫩的豆腐。
3
在小镇站住了脚,谷雨卖豆腐。良志整天窝在家里,泡黄豆,打豆浆,做豆腐。良志叫苦叫累,谷雨眼睛一白,你去卖,我来干家里的事。良志点点头,去了,一上午卖了四、五斤豆腐,回到家,有气无力地说,我还是在家吧,这些家伙,是买豆腐哩,还是来眼馋我老婆来啦?
谷雨咯咯笑了,下午把剩下的豆腐拿去,一个下午卖完了。
有时,豆腐卖完了,闲下来时,谷雨也去荷子的小店坐坐。
谷雨那天,是穿着一件旗袍去的。
镇上人爱穿旗袍,尤其这个夏天,流行旗袍。谷雨也买了一件,藕荷色的,回来一穿, 良志眼睛就大了,抱住谷雨揉捏了一气,然后说,别穿了!
谷雨说,为啥?满街都穿呢。
良志说,人家是镇上人,我们是卖豆腐的。
谷雨眼一白,偏不,卖豆腐的贱啊?
谷雨去了摊子,结果,豆腐卖得更多。良志酸酸地说,那些家伙,不是买豆腐,是看白白的大腿来了。谷雨笑弯了腰,咯咯咯地说,看吧,看不折,是你的还是你的。
良志摇着头悄悄道,小妖精。
谷雨说,妖精好,能勾人魂哩。
良志让谷雨逗得满身鬼火乱窜,来抱谷雨,谷雨一转身,穿上高跟鞋跑了,来找荷子了。两个女人在镇上,没有别的朋友,买了衣服总要泡在一块儿,指指点点,评说一会儿。但是,这次却不是的,谷雨有别的事,最近谷雨私下里听人说,荷子在镇上暗暗有个相好的了。她不相信,咋可能呢,荷子不是那样的人啊。
她想去看看,顺便问问荷子,是不是得罪人了,别人故意泼脏水。
远远地,谷雨就看见了荷子。荷子正坐在柜台后,一个胖胖的男人,在和荷子说笑着。荷子脸上挂着笑,没说话,眼睛却在望着外面。那男人拍了一下荷子的腰,荷子看见谷雨,脸红了,白了胖子一眼,站起来笑着夸谷雨,呵,都赶上女明星了。
谷雨看那个胖子也在盯着自己,眼睛白了他一下,笑着对荷子说,也去买一件吧,穿上了,还不把有些男人的眼珠子拽掉。
荷子听了,拍了谷雨一掌,说别胡说啦。然后拿了个凳子让谷雨坐了。荷子的铺子前,就是一渠水,一排柳树,凉凉的。过去,谷雨爱来坐,一会儿工夫,身上就凉凉的,比空调还好。可是,这会儿,她有点坐不住啦。因为,那个胖子的眼睛转过来,有一下没一下悄悄向自己的腿上扫瞄。
谷雨冷了脸,心说,见过眼睛贼的,没见过这么贼的。她微微收拢双腿,用手压了压旗袍。胖子并没感到尴尬,反而问荷子,这位妹子是谁啊?
荷子装作没听见,问谷雨,最近忙不?
谷雨说忙哩,从这儿过,顺便来看一下,没打扰你吧?
荷子没说话,忙着倒水。谷雨觉得自己的话过头了,心里有点不落忍,站起来,准备走。荷子拦住她说,谷雨,咋的?坐一会儿吧。怕她要走,一把拉住,硬是不放。
谷雨回头,看到胖子仍坐在那儿,眼睛仍瞄着自己,心里本来不高兴,这下更有点火了,故意问胖子道,想买啥吧?说吧,走进铺子拿过荷子柜上的烟,说,来一条。胖子感到谷雨在下逐客令,站起来,讪讪一笑走了。
谷雨轻声说,见过没皮没脸的,没见过这么没皮没脸的。
荷子问,谁呢?
谷雨嘴一翘,用眼一斜,瞥向走向远处的胖子,说,不就是那个人。说得荷子哧地笑了,说你啊,嘴像刀子一样。
谷雨说,咋的,不高兴啦,别是喜欢上了那个人?
荷子又红了脸说,说啥呢,别听旁人瞎说。本来,谷雨想劝说荷子几句的。荷子这样一说,谷雨反而不好说什么了。一时,两人静静地坐着。外面树上,有鸟儿跳跃着,叽叽喳喳地叫着。
4
卖豆腐,在谷雨来说,只是暂时的。
谷雨想模仿荷子,也买辆车,再开爿铺子。在镇上呆了一年多,攒了一笔钱,又借了一点,凑在一块儿,买了辆面包车,让良志开,可良志不会。谷雨一发狠,白了良志一眼,亏你还是个男人,活人能让尿憋死。
谷雨自己去学开车,十几天就拿了驾驶证,然后上车,“呜”的一声,把车就开走了。
谷雨让良志一个人经营豆腐摊子,自己开起车来。
每天,天一亮,谷雨就起来了,把车开到车路旁,放在那儿,喊一声,去上津的客人,上车哦。“哗”的一声,车就满了,谷雨一笑,钻进车子,“呜”的一声,车子走了,转过几个山弯,就不见了影子。
这时,太阳才刚刚升起来,照红对面的山尖尖。蓝色的雾浮起在小镇的河面上,还有树林里,还没有褪尽。包括山后寺庙,也隐在淡蓝色的雾中。
等到其他司机载上人,动身走时,谷雨又回来了,车上满满一车人,是上津来漫川的客人。
这些司机很无奈,也很不舒服,实在弄不清,为啥谷雨生意就那么好。最后,还是一个叫旺儿的发现了秘密,这谷雨,长得妖嘛,看人家那肥肥的腚,那鼓鼓的胸,还有那狐媚子脸,哪个男人不想看?
其他司机“哦”了一声,都醒悟过来,点点头,顿时失了锐气,比不了,也没法比。
就这样,谷雨得了绰号——谷妲己。有人说,叫谷西施得了,马上,就被别的司机推翻了,还是谷妲己好,瞧那骚到骨子的样子,咋是西施?明明是妲己,是个狐狸精嘛。
山子听到了,没有吱声,回去告诉荷子,让荷子劝劝谷雨,悠着点,别太张扬了。
荷子打了手机,告诉谷雨,谷雨听了,咯咯地笑,连声答应。可是,出车时,仍是原来的样子,一条旗袍,在车旁靠着一站,车模一样,喊一声,去上津的客人,上车哦。
人一下子拥来,又满了。
不只是客人爱坐谷雨的车,镇上的小伙子要到上津看个景什么的,也爱坐谷雨的车。甚至,有的男人没事找事,也要去趟上津,不为别的,就是想坐坐谷雨的车嘛。镇里的女人们都是醋缸,醋坛子打得稀里哗啦的,一个个眼睛瞪圆了,看着自己的男人,逢着男人外出,提前嘱咐,记住了,不许坐谷妲己的车。
男人伸着脖子凶道,为啥?哪国的法律?
女人说,不为啥,你要敢坐谷妲己的车,我也出去找个男人,用摩托带着到处转,我还搂着人家的腰哩。
男人顿时软了腰,忙连声保证,一定不坐,绝对不坐。可是,出了门,撇过女人,就直奔谷雨的车:不坐划不着,同样的车费,坐了车,还养了眼,傻子才不坐哩!
5
旅游旺季时,山子竟然停止了出车。
谷雨是几天后才发现的,最近几天,没和山子照过面。她看见别的司机,就问,山子呢,咋没见他开车?被问的人一例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谷雨很生气,白了一眼,说吃了老鼠药啊,那样毒人?说完,腰肢一扭走了,然后拿了手机,打通荷子的,问是啥原因,你们山子不开车啦?荷子不说。问急了,荷子说,谷雨,你就甭问了吧。
谷雨很纳闷,关了手机。
五月的小镇,并不是太闷热,镇外一片水光,漾进镇子。水多,树也就多,柳树之外,有杨树、槐树,四季常青的白蜡树。风从水面吹过来,凉悠悠的。可是,谷雨仍感到有些热。她想,咋的,不会是生我的气吧?我可没抢山子生意啊!谷雨的眉毛皱了皱,停了车。有人喊,谷雨,去上津吗?谷雨回头一笑,说不呢,今天歇车。过去,谷雨说话爱带“哩”字,现在学镇上人,带“呢”字,软软的,有一种江南音。
那人说,咋的啦?我去就不下上津啦?没劲!
谷雨笑笑地走了,走出一路柳色飘摇。
到了荷子那儿,荷子卖东西。山子坐在旁边,吸着一根纸烟,闷低着个头,见了谷雨,点了点头。荷子见了谷雨,仍然笑着让谷雨坐,略带惊奇地挑着眼睛问,咋的不出车啊?
谷雨说,过来看看,山子咋的不出车呢?
荷子不说话了,长长细细的手指拂了一下头发,说算了,不开了,一个铺子够生活啦。
钱多咬手啊?谷雨问。
荷子不回答,给谷雨拿了一筒饮料。谷雨不喝,要喝茶。荷子泡了一杯,放在谷雨跟前。谷雨望着荷子说,荷子,不是我抢了山子生意吧?
荷子笑了,说看你想的?那多的人,你咋能抢生意啊?
谷雨喝了口茶,是本地茶,一股清香淡淡散发开,很清醇。谷雨娘家是茶农,因此,她也学会了喝茶。她望着荷子,等着她说出原因。可是,荷子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就是不说话。
咋的啦,说啊?谷雨说。
开不成啦。荷子绞着细长的手指,轻声回答。
为啥?
车被交警队牛队长扣了。
在谷雨一再盘问下,荷子才红着脸,告诉了谷雨事情原委。那个牛队长——就是荷子那天看见的那个胖子,有个坏毛病。谷雨点点头,到了镇上,开车不久,隐隐约约她就听说,牛队长这家伙,没事的时候,爱沿街转悠,看见哪家小媳妇大姑娘眉眼水一点的,模样周正点的,就挪不动脚了,就坐下来,一聊就是半天,也不管别人嫌不嫌。
他经常来荷子的铺子,没事了,说些黄段子。荷子很烦,可仍得笑笑地听,自己男人开车,饭碗子攥在人家手里,没有办法。一来二去,镇上的人就嚼舌头,说自己和牛队长好上了。自己知道了,这些事也没法去说明啊,只是想,自己是清白的,是白黑不了。所以,也懒得去辩解。
开始,是讲黄段子。然后,牛队长就动手动脚,摸摸揣揣,荷子也只得咬着牙忍着。可是,前几天,这家伙看荷子没躁,竟然大了胆,瞅见没人,抱起荷子,就向屋里抱。
荷子让放下,他不放,反而用手去解荷子裤带。荷子急了,啪的一个耳光过去,打在那张胖脸上。牛队长一愣,松了手,过了一会儿笑了笑道,还怪厉害的啊,小妖精。说完,哼了一声,走了。
第二天,山子的车就给扣了,说是违章行驶。怎么违章?牛队长眼一瞪,吼道,咋的?你是谁?我还要给你汇报啊?
山子无法,只有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谷雨听了,鼻尖上沁出汗来。她想说什么,张张嘴,又没有说。然后,劝了荷子几句,站起身来走了。风从水面吹来,薄薄的,凉凉的,可怎么也吹不平谷雨烟一样皱着的眉。
6
交警中队,在镇的另一边,一圈儿水一抱,只有一条路进入交警队大院。牛队长来后,开车的很少在这儿出现,怕牛队长看见。牛队长一瞪眼,开车的心里就直忽悠。
开车后,听到山子介绍,谷雨也尽量少来这儿。在外混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办证,也是趁牛队长外出时,谷雨和良志一块儿来的,办了之后,转身就走。办证的年轻交警笑笑,放心,牛队长今天不回来。
谷雨笑笑,对交警挥挥手,吁口气,和良志走出交警队。
司机们赌咒时,总是说,我要哄你,让我下次开车撞在牛队长手里。
因此,开车半年,谷雨尽量不去接触牛队长,即使见了,也远远躲开。山子见了,连连夸,谷雨,有眼色,这事,千万不敢逞能。
谷雨明白,该逞能的逞,不该逞能,千万别露面。
可是,最近,谷雨的车多次出现在交警队院外车路上,那儿有一丛树,一片儿绿阴,有时也有外出的人蹲在那儿躲阴凉的。那个年轻交警见了,皱皱眉,走过来,说开走吧。谷雨笑笑,说听说这儿有客人,想捎几个。
年轻交警摇着头,说,走吧,别找亏吃。
谷雨点点头,说就走就走,谢谢了。可是,就不走,靠着车,一头长发墨黑地飘,身上的旗袍水一样闪动。年轻交警摇着头,走了进去。
谷雨等了一会儿,没人来坐车。她把手拢起来,放在嘴边喊,去上津的客人,上车啊。声音脆脆的,在凉凉的风里播散开。然后,又喊了几声。声音还没歇下,院门前出现个胖胖的人,是牛队长,吼道,怎么的,叫到交警——吼一半不吼了,眯着小眼儿乐道,哪儿去,上津吗?
谷雨点点头,拢了一下头发,侧着头问,牛队长想去上津吗?
牛队长小眼睛又是一亮,认识我啦?
开车的不认识你,那不是说笑话嘛!谷雨哧哧地笑了,瞥了牛队长一眼。
牛队长轻飘飘地上了谷雨的车,说,走,我也去上津,今儿个给美女压车。谷雨一笑,说,哟,我可不敢当啊。说着,就上了车,沿途拉了几个,就向上津跑去。到了地方,牛队长找车费给谷雨。谷雨挡住了,白了一下牛队长,说,队长,你在骂我,我再看重钱,也不能收你的。
牛队长拍拍谷雨的手,点点头走了,告诉谷雨,回去还乘谷雨的车。谷雨忙答应了,然后靠着车,笑笑地喊,去漫川的客人,上车哦。
不一会儿,车上就满了。
7
一来二去,谷雨和牛队长熟了。牛队长很高兴,告诉谷雨,妹子,跑车时有事,找哥,哥帮你解决。
谷雨听了,就笑,咯咯噜噜的,一个水一样的身子,就水一样地波动。牛队长也笑了,拍了一把谷雨的腰肢,说好细,只一把哩。谷雨更笑得厉害了,谷雨怕痒痒的。
这以后,没事时,牛队长不沿街转了,坐着谷雨的车,上津漫川来回转。其他司机见了,说,这个妲己,找了个保镖。当然,牛队长面前,大家不敢大声说,都侧着眼望着,笑着点头。牛队长不在了,就问谷雨,你哥呢?今个儿没来保驾护航?
谷雨笑笑,说,咋的,你很想见我哥?
那人慌了,忙摇着手,说开玩笑,你别当真,我——啥也没说。
谷雨说,我咋感觉到你啥都想说。
那人更慌了,低着头,仿佛做贼了一样,没了声音。那几天,开车时,小心又小心,生怕出岔子,被牛队长抓个正着。好在,事后,并没出现什么。也不知谷雨没给“她哥”说,还是“她哥”突然念佛成仙了。
小镇的小媳妇大姑娘都有点轻松了,因为,牛队长没兴趣转街了,现在,一门心思放在坐车上。每天早晨上谷雨的车,当天下午回来,例行公事一样。
牛队长来了,大刀金马地坐在谷雨旁边,到了地方,下车后,照例掏出二十元,算做车费。谷雨仍然一笑,仍然是那句话,队长坐车,是给我面子。
渐渐地,熟络了,关系近了,牛队长的手,慢慢不正经起来,总是暗暗搞些小动作。每次,谷雨都侧头一笑,队长,人家开车呢,出不得事的噢。那声音,像一只只蚂蚁,在牛队长心上爬动。
那天,回来的路上,天黑了,车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谷雨,一个牛队长。车子走了一会儿,牛队长突然说要解手,让停下。谷雨笑笑,停下了车。牛队长并不下车,猛地一把抱住了谷雨,压在车厢中,又揉又啃起来。
谷雨说,停手。牛队长不停手,喘着粗气。
谷雨又说,停手。牛队长仍不,手乱揉乱捏,而且准备进一步深入。
谷雨扬起手,一爪子挖过去。牛队长的脸上火辣辣地痛,一摸,还有血。牛队长停住了手,一句话不说,一双眼在暗夜里放光。
第二天,谷雨的车被交警队扣了,原因是违规。走时,牛队长甩下一句话,除非谷雨到交警队把违规的事说清,否则,车就别想跑了。
谷雨无奈,第二天早早去了交警队。看到谷雨,牛队长眼光闪烁。
队长,人家来了。你干嘛扣人家的车嘛?谷雨噘着嘴唇,一条旗袍把一个身子箍得水光闪闪,一波三折。
牛队长的喉结动了一下,板着脸,很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
说啊,怎么了嘛?谷雨眼睫毛上挂满了委屈,用小手摇着牛队长的肩。
你,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你——牛队长喘着气,满眼饥饿。
答应什么啊,你?
我喜欢你,你答应我吧。牛队长站起来,来抱谷雨。
谷雨一笑,一拍掌,响起了敲门声。门一开,谷雨男人良志站在门外,眼睛瞪得彪圆。谷雨媚媚地笑着说,
良志,牛队长说喜欢我,我要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就给我们车。
牛队长急了,说胡说!诬陷!
谷雨取下肩上挎着的一个精致的手袋,打开来,取出一个小小的手机,一按录音设备,谷雨和牛队长的话,一句一句,清晰如水地流淌出来。牛队长红着脸,塌了腰,没有了威势。良志撸起袖子,握紧拳头就想动手,谷雨一笑,拦住了道,人和牛一样见识,掉价。说完,拉了良志,对牛队长挥挥小手,软软绵绵地走了,到了院子,开了自己的车,“哧”一声走了。
几天后,牛队长被调走了。走时,刚刚开上车的山子,组织小镇司机,买了几挂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放了起来。几只白色的鸟儿,停在沙洲上,被鞭炮声一震,
展开长长的翅膀飞了起来,一下又一下,在晴朗朗的天空下盘绕。
大家再望谷雨,眼睛里没了过去的意味,明显地有感激,也有惭愧。谷雨仿佛没看见一样,拢了一下头发,旗袍如水靠在车旁,仍旧软绵绵一笑,喊,去上津的客人,上车哦。
一声,车上人就满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