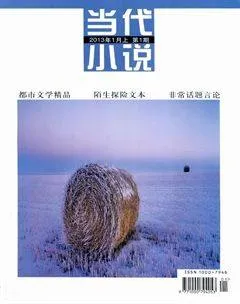经过
天刚蒙蒙亮,三亚便推开了大门,又回身把门关上了。再回过身来,目光便落在了他的车上。
三亚的车是一辆出租车,就停在大门旁边,虽然停在了一棵树下,但现在是深秋,树上的叶子早就落光了,车身不可避免地落上了一层露水,密密匝匝的小水珠遍布车身表面,在灰蒙蒙的天光里晶莹剔透,闪着光亮,便让那车给人一种簇新的错觉。但三亚知道,天亮了,露水干了,那车就会变成一张大花脸。这是三亚不能容忍的。
三亚当过兵,是团机关卫生队的卫生员。虽然机关不像连队要求那样严格,但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卫生员的宿舍里从来都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此,卫生队那个曾经在老山前线丢掉一只眼的独眼龙队长,有一回便用那只好眼斜着三亚,跟他开起了玩笑。三亚啊,看你那么费劲儿,搞得我都压力蛮大的。又觉得这话不太像领导该说的,便呵呵笑着补充道,也好,当兵嘛,就该有个兵样。当时三亚还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着,但过后还是老样子。这样坚持了两年,三亚就多少有了些洁癖。虽然这时三亚退伍已经好几年了,但那种洁癖多多少少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了下来。
以往,三亚也是这个时间出门的,他要赶去火车站。有趟火车将在不久后进站,停下,然后又开走。他要赶在旅客出站前把车停到站前的路边上,等候他一天里的第一个乘客。两年来,他的每一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的。
出发前他会把车从头到尾检查一遍,看看机油和冷却水,看看轮胎的气压,确定没有问题了便把车发动起来,先热着,再把车收拾一番。盛水的小桶是出门时就拎出来的,就放在车身一侧,他会先把车的四门全部打开,把里面的浊气完全地释放出来,再把脚垫抽出来抖搂干净,放在旁边的水泥地上,然后便开始擦车。他总是擦得很仔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甚至连轮毂的缝隙里,到最后,也会用剩下的水冲洗得锃明瓦亮。等做完这一切,那车,好像便洗去了一天的风尘,重又焕然一新了。等他再坐进车里,把车开上路,扫一眼一尘不染的车内空间,心情也会跟着明朗起来。
可是今天,三亚却没有做这些。离开大门,他朝灰蒙蒙、空荡荡的街上望了一眼,能看到的范围里只有一条不知谁家的狗一嗅一嗅地沿路边走着,远远地望他一眼,便心虚似的夹起尾巴跑掉了。望着那狗消失的地方,更加空蒙的街巷,三亚的脑袋里突然闪过他已经去世的父亲的面庞,那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他父亲投向他的眼神,眼神里的那种凄惶,还是一下子击中了他,让他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酸到了心里。但他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收回目光,快步走到了车子跟前。
已经开了车门了,三亚还又回过头,望了一眼他刚刚离开的大门和院子。
大门是那种最简单的门楼和两扇铁皮门,门楼上长满了杂草,铁皮门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得有些斑驳。院子里几乎全是房子,或者有一些也算不上房子,只是在房子和空地上搭建出来的棚子,乌乌压压、摇摇欲坠的模样。开发商和政府已经跟村里签订了拆迁协议,不久后所有这些都将被拆掉,按面积给予补偿,那将是一笔很大的款项。
但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三亚看着这个两年多来,被所有人称为他家的地方,此时,他却清晰地感觉到了一种隔阂,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他看到的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已经泛黄的,与己无关的旧照片上的景象。
三亚把车开出了村子。一出村子也就进入了市区。
当年三婶跟他提到这家人的时候便是这么说的,紧挨着城里,没准哪一天就拆迁了,就成了城里人,政府给的拆迁补贴还有占地费啊什么的,这辈子都花不完。
可他最终来到这里真的是为了这个吗?那时他退伍回来已经三年了,他用退伍费学了驾照,在一个建筑公司做司机。除了刚回来那阵子,三年里他几乎没回过家,即便过年他也只是让人把钱给他母亲捎回去。他只是会抽空,开车去他父亲的坟上一趟。他父亲的坟在远离村子的河滩上,一个孤零零的坟堆,才几年,已经风化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他到了那里也就是在坟堆旁边的空地上坐一会儿,抽一地烟头又回来了。他是不愿进到村里去的,那个他出生并长大的村子,让他感到的只有耻辱。
但是现在,这些似乎都已经淡了,只有不时出现在他眼前的父亲的眼神,一下一下刺痛着他。那眼神的出处是他退伍前最后一次探亲时。假期结束,父亲送他去村外路边上等去城里的客车,临上车了父亲却突然对他说,三儿,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吧,留在部队上。说完这句父亲眼里突然闪出了泪花,又赶忙用袖子抹了,勉强冲他一笑。但是马上,他却从父亲望向别处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份说不出的凄惶。后来,这凄惶在他退伍离开部队时,也曾在他心里出现过。坐在送退伍兵去往火车站的大卡车上,望着越来越远的营区,他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其中甚至还包含了生离死别的决绝和无奈。也正是那时,他突然明白了当时父亲眼神的含义,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那时就已在父亲的预料之中了。
他其实是可以像父亲希望的那样留在部队的,临近服役期满独眼龙队长就找他谈话,让他不要做退伍的打算,队里要留下他,他还为此开心过好一阵子,不时的就会憧憬一下父亲期望他留在部队签个合同兵的愿望实现时的情景。可是他的好心情却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戛然而止。消息是回家探亲的王可然带回来的。王可然家就在与他家相邻的村子里。同时带回来的还有王可然的愤怒。王可然说他父亲是喝药死的,之前被老光棍刘小顺给打了。王可然还想说点什么,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只是咬牙切齿道,弄死他,回去,弄死他!
三亚给他大姐打电话,原本他大姐是不想说的,被他问得紧了,大概也是想这事早晚也是瞒不住的,便吞吞吐吐地说了,咱娘那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不知道顾个脸面,她和刘小顺那个熊黄子在一起,被咱爹碰上了,咱爹骂了他们,结果被那个熊黄子给揍了一顿,想不开就喝了药。完了大姐还一遍遍叮嘱,这不管你的事儿,咱娘愿意的谁也管不了,人家又没有灌咱爹喝药,你在部队好好呆着吧,千万别回来,再说现在他们也跑了,也不在家了。可是大姐还没说完,三亚便把话筒砸在了话机上,他感觉自己的牙就要咬碎了。如果这时刘小顺站在他面前,他一定会一刀捅了他的。
等平静下来,他也想不管了,怎么管呢,丢人呢,可是他一这样想,父亲的那双眼睛便在他眼前不停地晃着,他心里的怒火便会重新被点燃。他想怎么也得好好教训教训刘小顺那个熊黄子,他就想到了打斗的场面,万一要是控制不住呢,他想他也许会打死他的,他心底里是有种要打死他的渴望的,甚至这渴望还特别强烈。他就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就想还是脱掉这身军装吧。他不想给这身军装染上哪怕一丁点的污点。于是宣布退伍前几天他找到了独眼龙队长,坚决要求离开了部队。但是后来,事情却没有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
他回来不久便在城里的一个出租屋里,找到了他母亲和刘小顺,可是他挥起的拳头最终却没能落下去。那时候他娘就跪在他的脚边上,抓紧了他的裤腿,她说你打吧,你把我们都打死吧!她说,他是你爹!
他举起的拳头便悬在了半空里,被他抓住领口的刘小顺还保持着躲闪的架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但那眼神里除了一点点害怕,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反倒顺着他娘的话说,没错没错,你娘说得没错。透着说不出的讨好和巴结。
其实从小到大,三亚没少听了村里人对他娘和刘小顺的风言风语,甚至说他不是他爹的种的,可这时从他娘嘴里说出来,一时间,还是让他感到震惊、茫然、无所适从。他再次感到自己的牙就要咬碎了,可是拳头却失去了落下去的方向。
他甚至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他一拳砸在自己的另一只拳头上,甩开他们,从屋里跑了出来。站在大街上了,他的身体还在不停地抖着,筛糠似的,根本控制不住。那时正是隆冬,风一吹,让他的身体好像整个都洞开了,风一直灌进他心口里,说不出的冷。
后来他母亲和刘小顺又回到了村里。他们原本就是为了躲三亚才跑出来的,既然三亚没把他们怎么样,再说他们也没钱再呆在城里了,也就脸一抹回去了,索性还住到了一起,两口子一样过起了日子。也就是那之后,三亚再也没有回过村里。
他三婶来找他时说,像你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还不如找个好人家倒插门算了。后来三婶就带他来到了他现在的这个家,见到了后来成zuCalofYFJYCiegOCnxEpQ==了他老婆的魏月芝和她的父母。魏月芝的父母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前边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剩下最小的魏月芝,就打算让她招一个上门女婿,老两口也好老了有靠。
那时三亚觉得这家人还是不错的,魏月芝的爸爸是个退休教师,虽然是民办教师熬上来的,可还是比一般他这个年纪的村里人显得有文化多了。而那时魏月芝在城里一个服装店打工,看摊卖衣服,加上本身就是城郊长大的姑娘,很会收拾,看上去跟城里女孩似的,很洋气。魏月芝和她父母对三亚也没什么意见,怎么说三亚都是当过兵的人,看上去就非常精神。或者在魏月芝的父母看来,三亚有家不能回的情况,对他们一家反倒不是什么坏事儿。
后来三亚和魏月芝便订了婚。
进市区不久三亚便把车停在了一家银行门口的路边上。天已经大亮,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多了起来,但街上的嘈杂好像跟他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相隔的不仅仅是车门,好像是一堵厚厚的、难以穿越的城墙。
银行还没有开门,电镀的卷帘门仿佛水银泻地,安静、光洁,冷冷地反着光亮。三亚坐在车上,把那盘灌满《打靶归来》的歌带塞进了录音机里,响起的歌声仿佛又把他带回到在部队的日子,跟着救护车去靶场保障,时不时他也会打上几颗子弹,射击的快感让他迷恋,但更让他迷恋的还是打靶结束,撤离的队伍在调整好步伐后一定会唱起这首歌。一个队伍伴着步伐的合唱雄浑、苍劲,那种震撼显然不是录音机里的歌声可比的。事实上,这时响在三亚心中的,也许正是那穿越时光而来的歌声。
平时,三亚都是早上刚把车开出来的时候放这首歌的。他专门买的空白磁带,把整盘磁带都录满了这首歌,这保证了只要他把磁带塞进录音机,响起的就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只是他每天听这歌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每当他一天里的第一个乘客上车时,他已经提前把它换成了收音机里的交通台。这首歌,他似乎不太愿意与人分享,或者潜意识里,他是怕乘客会对这首歌指手划脚,或者有不恭的言辞,那样可能会伤到他。
某种意义上,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歌。
歌声里,他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下来。以往听这首歌时,他也会有这样的冲动,但他马上便会自嘲地笑一笑,让泪水也就是在眼眶里打个转儿,就回去了。但这时,他却丝毫没有把眼泪阻断的念头,反倒希望它们尽情地奔涌出来。汹涌而出的泪水好像正把他心里淤积的某些东西不断地带出体外,渐渐地让他心里好像湖水一样越来越安静、澄澈。当眼泪自然而然地止住时,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他的对面,太阳从一个房顶上探出头来,红彤彤的。阳光穿过前挡玻璃晃着他的眼。他随手把遮阳板拉了下来。遮阳板背面的小镜子映出了他的脸,但过了好长时间,镜子里的脸才在他的大脑中清晰起来。同时清晰起来的还有他额头上的伤痕和两天前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三亚收车到家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堂屋里仍灯火通明,不时响起麻将和笑闹声。土地卖完了,有了钱,也有了闲的村里人便把打麻将当成了职业,不知从哪天起,他们家便有了个固定的牌局,从早到晚,总会聚着一些人,把堂屋里弄得乌烟瘴气。
但三亚已经习惯了,或者也并不关心,他跑了一天车,累了,晚饭还没吃,回到家,堂屋也没去便进了厢房,也就是他和魏月芝的房间。换下衣服,又去了厨房。如果没有剩饭他会下上一碗面条,以往他也都是这样对付的。没想到这天他刚刚走进厨房,魏月芝便从堂屋里跑了出来,怒冲冲地叫着他的名字,三亚,你给我说,那钱哪来的?
三亚一时没反应过来,但很快也就想到了他放在床下盒子里,又塞在一件旧军装口袋里的一千来块钱。那是他从每天的收入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每天收车回来,魏月芝都会把他包里和身上的钱翻出来,留下些零钱,剩下的便都收了去,几天凑个整数再存到银行里。开始是说这样存着,凑个大点的数就把买车借的钱先还一些。买车的钱一部分是三亚攒的,还有一部分是向他大姐和王可然借的。可银行卡在魏月芝手里,一年多时,想想也该有几万块钱了,三亚想先还一部分,可每次三亚一提出来,魏月芝总说慌什么,放银行里还能生些利息呢。三亚第一次跟魏月芝发生争执就是因为这事儿。三亚觉得钱是借人家的,既然有了就该还给人家。可魏月芝好像并不这么想,看她那眼神儿,就让人觉得,到了她手里的钱再让她拿出来,简直比割她的肉更让她心疼。一开始,银行卡放在他们房间的抽屉里,魏月芝在上面加了把小锁。有一天三亚便瞒着她把锁撬了,拿了卡,又拿了她的身份证,准备到银行取了钱,先还了再说。可那天他刚刚出门,便被魏月芝发现了,追出来,把他堵在了离他家最近的她存钱的那家银行里。那时三亚正在排队,魏月芝冲上来,把他拖了出去,银行卡也到了她的手里。三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但那次他却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产生了很深的质疑。后来他站在银行门口,望着魏月芝骑上电瓶车远去的背影,突然觉得属于他的那颗心似乎被人丢在了脚下,属于它的温度正一点点的被什么抽走,这时他看到了地上的树叶,冬天里枯干的树叶,在地上,胡乱地被风吹着。他感到自己好像就是一片那样的树叶,没有了依附和重量,没有了水分。
三亚也没想到自己会对魏月芝动手。他抠下这钱是打算给他母亲和小爱国的。小爱国是今年春天他跑车时,在路边捡的一个小男孩,当时才出生不久的样子,被他送到派出所,又被送到了福利院,起名福爱国。这时小爱国已经七八个月了,见了他就会笑,还朝他挥舞着小手,找他抱的样子。三亚经常去福利院看他,给他带点吃的和钱过去。只是三亚没把这事告诉魏月芝,他只是对魏月芝说,那钱是他准备让人捎给他母亲的,无论他母亲怎样,这都是他做儿子的该尽的义务。可魏月芝根本就不想听他解释,她似乎更想把事情还原一下,便揪着三亚的衣服把他拽进了卧室,把钱从床下他那件旧军装的口袋里摸了出来。显然,为了想象中的这个场景,她提前并没有把钱收起来。魏月芝把钱拿出来之后便在三亚眼前不停地晃着,不停地嚷,行啊三亚,你真有办法啊,你就这样对付你老婆啊,你娘那个熊样你还给她钱,我给要饭的也不给她。这样说时,她手里的钱几次都碰到了三亚的脸。
三亚就是这样被激怒的,他一把将钱从魏月芝手里夺了过来。魏月芝伸着手扑过来,也许是想来抓三亚的脸的,也许只是想把钱抢回去,但她的手还没有够到三亚,便被三亚一把推倒在了她拉开的床盒子里。
魏月芝的母亲听到动静先跑了过来,随后她父亲也跑来了。
她母亲还只是嘴里叨叨着,怎么了?怎么了?而她父亲,到了门里,看着坐在床盒子里扭动着身子,哭嚷不止的女儿,又看着三亚,眼睛里突然便冒出火来,那样子,就像谁动了他的心头肉一般,突然便将手里拿着的一个玻璃茶杯,连水一起,狠狠地砸向了三亚,并大吼了一声,滚!给我滚!然后又叫嚣道,什么东西,还反了你了!
但是现在再想起来,三亚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愤恨,好像那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好像他穿过他父亲的眼神所看到的景象一样模糊和虚幻,倒是后来,一家人都将自己心中的不满发泄完了之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那种感觉依然清晰。他躺在床上,却明显地感到心已不在了那里。可是心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又想起了他和魏月芝第一次发生争执时,他在银行门口看到的那些地上的树叶。
那些树叶被风裹着,飘起又落下。
那天晚上之后,魏月芝便睡去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接下来的两天里,三亚出车回来,也没有主动走到她和她父母的跟前去。两天里,大家甚至都没有照过面,冷战一样。有时三亚穿过院子去房间时,还听到过从堂屋传来的显然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一些话,那些话里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确的,好像是如果不是他们,他三亚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他这样对魏月芝让他们很气愤,后果很严重。
三亚也觉得后果很严重,他甚至很清楚地看到了一道裂痕,横在他和他们之间,很清楚地感到了这道裂痕的不可弥补和难以逾越。
三亚的计划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也想过别的办法,比如直接提出来离婚,比如干脆不声不响地搬出去算了。但是,他马上便否定了自己的这些念头,他觉得很累,心里似乎已经聚不起处理这些事的力气。昨天他路过一家药店时,便下车把药买了。药是两种。当年的卫生员三亚对各种常用药品的药性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两种药品合在一起,将产生足以让人致命的剧毒。
银行的卷帘门终于被人推了上去,运钞车开来又开走了。下车前,三亚又看了一眼额头上的疤痕。才两天时间,上面已经结了一层硬硬的痂,呈现出暗红的颜色,假以时日这层痂会逐渐脱落,露出泛白的底痕,再逐渐跟周围的肤色变得一致。可三亚知道,这个过程可能已无法完成了。想到这里三亚甚至还苦笑了一下。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苦笑了一下。
三亚下了车,锁上了车门。上班的人流高峰已经过去,街上已经安静下来。这个秋天里明朗的日子,阳光很好,空气虽有些凉了,但却干净,清爽,可以看得很远。大团的云彩把天空衬托得很高,远处的山峦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三亚怔怔地朝远处看了一眼,似乎那峰峦叠嶂处,那无法明确的远方,给了他很大的勇气。他这才走进银行,在一个柜员窗口前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以及他和魏月芝的身份证。有了他撬锁那件事之后,这张卡便被魏月芝放在了随身的包里,这时,卡上似乎还带着她包里各种化妆品的气味。这气味也许曾浸到了三亚心里,也许没有。这味道同样让三亚感到茫然。
印象中,魏月芝在他心里始终是有些陌生的,结婚时他们才认识两个来月。结婚后他便开始跑出租了,早出晚归,也就是晚上才能跟她聚在一起。开始,他对那样的相聚是有所期待的,毕竟在魏月芝之前,他甚至连女朋友都不曾有过。他是想给她那种他想象中的丈夫对妻子的宠爱的,可慢慢地他却发现,魏月芝对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热情。他甚至搞不懂魏月芝对他的那种态度,好像夫妻就是那样一个身份,丈夫做丈夫该做的事,妻子做妻子该做的事,除此之外都是多余的。
三亚也想过,除他之外魏月芝是不是还有别人,但他也只是那么想想,毫无头绪。在这个家里他就是一个外来者,他对他们生活的圈子知之甚少。清晰的只有他和魏月芝之间的那种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
这么胡思乱想着,三亚把银行卡和身份证从窗口递了进去,让里面的柜员,一个面无表情的中年人,帮他查了卡上的余额,又帮他计算了两笔款项加利息的总数,然后他才报出取款的数目,还又多取了一些。
里面的中年人几次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不时地扫一眼外面的大厅,如果大厅人多,有人排队,三亚知道他的不满一定会发泄出来,但现在还早,大厅里冷冷清清地,几乎看不到几个人,于是他的不满也只好憋了回去。看着他的模样,三亚感到心里突然像秋天里的这个日子一样通透起来,他朝窗口里面保持了歉意和卑恭的神态,直到完事。后来,三亚已经开车上了路,还在努力回忆着他这时的心情,他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会突然变得明朗起来,但是他希望自己能保持这样的心态,这至少会让他看上去要正常一些。
三亚的大姐家在一个叫刘王庄的村子里,离市区十几里路。但就是这十几里路,却让这个村子跟靠近城市的村子有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城边的那些村子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新房了,多的是各种建材搭建的棚子,在死心塌地地等待着有一天被铲车推倒。而这里的人们还要继续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和希望。可以看到,很多二层三层的小楼从老旧的平房里伸出头来,仿佛枯草中冒出的新枝,高挑,雀立,生机盎然。
这个季节,麦子种下后,地里没什么活了,村里人起床都晚,三亚进村时很多人家都还没有起床,但很多人家的大门却是敞着的,三亚知道,那一般是家里有上学的孩子的,孩子早早起来,吃点东西便去了学校。三亚记得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走时总忘了把大门关上,回来便少不了被爹娘训斥一顿。
但那样的训斥没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再想起来,甚至有种说不出的温暖,细细地在心里流转。于是父亲和母亲的样子就又晃动在他的脑袋里了。
父亲总是胡乱地坐在那里,抽着烟默不作声,看到他却会突然冒出一句,饿了吧,你姐做饭呢。母亲总是不在家的,她在别人家的大门口,在街角的大树下,袖着手,跟街上的男人女人们在说话,不时便会爆出哈哈的笑声,她笑和说话的声音隔着半个村子都能听见。然后风风火火地回来,嚷着小菊,你个死妮子,你死哪去了,要么就嚷赵大河,地里的草都把庄稼吃没了,你还有闲心在那里抽烟,少抽棵能死人呀。赵大河是他父亲的名字。听到他母亲的吆喝,父亲也只是用鼻子哼一声,继续又没了动静。
小菊便是他的大姐秀菊。三亚的印象中大姐是没有上过学的,大姐总是呆在厨房里,咣当咣当地拉着风箱,烟雾从厨房的门檐下溜出来,散开,家里便有了烟火味。那味道让放学回到家肚里叽里咕噜的三亚,感到特别踏实。
他还有一个二姐的,叫小惠,可是三亚没见过二姐,二姐被人领走时他还没有出生。那还是他长大了才听人说的,送走二姐就是为了给他让路,不然他是没机会出生的。那时已经开始计划生育,超生是要被重罚的,有些人家甚至因此被扒了房子。
二姐是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带走的,那是腊月里一个家家都在准备年货的日子,那女子穿着貂皮大衣,戴着金项链和耳环,手里拎着一个很小的、亮闪闪的银色的包包,从一辆黑色的两头长得一样的车里下来,在村里一个叫二得子的人的带领下,扭啊扭啊地便进了他家,再从他家出来一个手里便牵了小惠。那时小惠才三岁,边走边哭,向后扭着身子,叫着爹和娘。很多年后,对面胡同里眼睛已经半瞎的大奶奶再说起这一节,烂桃子一样的眼睛里仍会有眼泪流下来。连个年也没过上呢,大奶奶总是这样说。
三亚心里对从未见过面的二姐是存了一份很深的歉意的。当兵回来,三亚去省城找过在那打工并已安家的二得子。他没想把二姐找回来,只是想见上一面,可是二得子告诉他,当初把小惠送给人家时便说好了的,不能再联系,另外那女的是他刚到省城打工时的老板,十几年没联系了,他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地方。
三亚把车停在了大姐家门口,要下车了才发现自己脸上全是泪水。他用袖子抹了抹,拉下遮阳板,从镜子里看了看,眼睛有些红肿,他便把两只手附在上面使劲儿按着,他不想让大姐看到自己这个样子。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他是把大姐家当成了自己家的,把大姐当成了心理上惟一可以依赖的亲人。这样想着,他心里便禁不住一阵绞痛。
大姐秀菊推开大门看到三亚的车时,三亚在车里已经坐了很长时间。秀菊是出门去赶集的,她和她丈夫农闲时贩卖鸡蛋,平时用三轮车拉了走街串巷,逢集便拉到集上去卖,他们的儿子小镇已经上了初中,住在学校里。
两口子看到三亚的车,便高兴得嚷了起来,叫着三亚的名字,跑过去。他们都快到了跟前了,三亚才发现了他们,忙朝镜子里看了一眼,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从车里下来。可是先跑过来的秀菊还是从他脸上看出了事儿来,问他怎么了,三亚笑笑,说没事。秀菊显然不信,叨叨着,却是无力的,他们没欺负你吧?又说,你在人家家,凡事得让着人家。三亚只是应着。
到了家里,三亚把钱从包里拿出来,大姐看着那钱,又看着三亚,一脸的狐疑,说慌什么,三亚说有了,大姐便迟疑着问多少,三亚便说了加上利息一起的数目,一旁姐夫便不高兴了,姐夫说三亚,你要用就先拿着,要是不用了就当初拿了多少还多少,我和你姐要是拿了你的利息,你让我们还怎么出门见人。大姐说,听你姐夫的。
三亚不想跟他俩争执,他觉得只要一张口他就会禁不住嚎啕大哭。他从里面抽出一些把剩下的放在了桌上。从大姐家出来,大姐一直跟到他车门前,还不住地追问着,三亚,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因为还钱的事儿你们吵架了,要是那样你拿回去就是了,我和你姐夫也不是没钱花的。三亚只说了声没事,便坐进了车里,他是不敢去看大姐的,虽然他很想再多看大姐一眼,可是想象中大姐的眼神已经让他没了再多看一眼的勇气。
三亚又去了王可然家。等他赶到市里的福利院时已经是上午的十点来钟了。在福利院门口的路边上,他坐在车里给魏月芝发了一个短信。他告诉魏月芝,银行卡被他拿走了,还了借的钱,其他都留在了卡里。
发完短信他还又等了一会儿,并没有短信回过来,他知道她肯定还没有起床,或者忘了开机。但他并没有在意,按计划,今天里他还会给魏月芝再发一个短信,等他去福利院看过小爱国之后,他会直接开车去他父亲的坟上,到了父亲的坟上之后,他会用短信告诉魏月芝,找个会开车的人,把车从他父亲坟上开回去。
是的,在有了这个计划之后,他就已经把接下来的这些事情想了很多遍了,仿佛都已经成了发生过的事情。
到了父亲的坟上之后,他会用车上带的那把小铁锹在父亲坟堆的旁边挖上一个坑,不用很大,只要他躺进去,身体不会露在上面就行了,然后他会躺在里面,把准备好的药片一起吞下去。他甚至都想到了自己那时的心态,躺在那里,土里的凉气会一丝丝地透过衣服,刺着他的身体,那样子就像小时候他跟着父母下地,躺在地头上玩耍一样。他会看到天空、太阳,还有云彩,他会用最后的时间想着他的亲人们甚至他从未见过的二姐。
他觉得只有那样用力地想着他们,等他到了那个世界,才不至于将他们遗忘,才有可能在将来重新遇到他们。他甚至希望,如果可能,在另外那个世界里他们还是一家人,他们还是自己的姐姐、父亲和母亲,只是那个世界里,不要再有现在的这些事情。
他会泪流满面,但一定没有哭声。他甚至还想把车尽量开到离坟很近的地方,他会打开车门,打开录音机,把音量放到最大,那样,他躺在那里时耳边便会回荡着《打靶归来》那首歌的旋律。他就会想起他的那些战友们,独眼龙队长,还有跟他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的战友刘军。他会非常非常地想念他们。
想到父亲时,他心里可能还会冒出一点点就要见到他的喜悦,甚至对他想象中他们相见的场景产生了一丝迷恋。
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三亚想象的方向发展。
在福利院里,他没有见到小爱国,福利院那个一见了他便笑眯眯的院长大姨,仍然笑眯眯地看着他,说小爱国被送到省城的儿童医院做手术去了,是先天性心脏病突发。还说,当初小爱国被遗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只是并不严重,一直都没有发现。
从福利院出来,三亚已经忘记了他原本的安排,他心里几乎全被要看一眼小爱国的愿望给占满了。他不知道小爱国到底怎样了。虽然院长大姨笑眯眯的,可他还是禁不住担心,他甚至看到了小爱国躺在手术床上的模样,和他可怜巴巴的眼神儿。这样的想象仿佛一只大手紧紧地攥住了他,他想都没想便把车开出了市区,开上了通往省城的高速。
到省城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魏月芝给三亚打电话时他已经到了医院,但他还是没有见到小爱国。小爱国正躺在手术室里,手术要三个小时后才能结束。等在手术室门口的除了三亚和福利院的两个人,还有我。我便是三亚当年的战友刘军。
我退伍后便到了省城,三亚来这里寻他二姐时我们曾见过一面,一晃好几年了,刚刚在医院门口的停车场里,接三亚电话提前赶到的我,第一眼竟没有认出他来。站在我面前的三亚看上去异常憔悴、消瘦,整个人仿佛一张纸,仿佛一阵风便能把他吹跑。后来在手术室门前转来转去的三亚,还让我想到了在我们当兵的山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孤狼,在远处的山梁上飘来飘去,哪怕有一丝风吹草动,都会惊惶得仿佛没头的苍蝇。
这时,三亚兜里的手机响了。
突然响起的铃声把三亚吓了一跳。真的是吓了一跳。我看到,他的脚交替着离了地,再落下来,稳住神,才伸手到口袋里把手机摸了出来。三亚接起电话,刚喂了一声,电话里便传出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吼声,你在哪里?三亚没有回答她,只是赶忙把电话挂了,又慌慌张张地关了机。然后三亚便坐到了我旁边,眼睛紧紧地盯着手术室的门,两只手不停地在腿上绞着。已经稍微有些凉的空气里他的额头和鼻尖上竟然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坐在我旁边的三亚一遍遍地问我,没事吧?不会有事吧?我说放心吧,对这样的大医院来说,这都是很成熟的手术了。可他似乎还是很不放心,还是在一遍遍地问着。
小爱国的手术很成功,在儿童医院住了两周便出院了。我再跟三亚通电话时,他们已经回去一段时间了。三亚在电话里告诉我,小爱国恢复得很好,他已经离婚了,在城里租的房子,还在跑出租。听口气,他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我跟他开玩笑,问他,那两瓶药呢?
他就有了些不好意思,嘿嘿笑了两声。扔了,他说。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