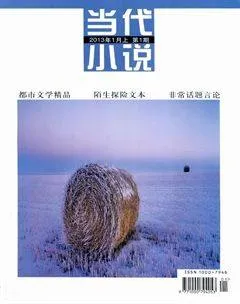老赵
老赵抱着个巨大的玻璃杯,有时是倚在门框上,有 时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他总是大开着门的房间冲着楼梯,无论谁上来了,谁下去了,老赵都一清二楚。
老赵手里的杯子真的很大,是个装水果罐头的瓶子,服务社的货架上摆了很多,有桃子的,也有苹果的、梨的,很受大家欢迎,吃完后留下杯子,喝水很过瘾。就像老赵,就用它作了茶杯、咖啡杯,甚至快餐盒,有时老赵还会用它泡面吃,吃得很香,甚至狼吞虎咽吃得很没有形状。如果那里面装的是冲好的咖啡,满满一大杯,就显得有点吓人了,让人联想到睡觉和失眠。可老赵说他从来不失眠。
老赵看人回来的差不多了,会抬起手腕看表。老赵手腕上是一只老上海牌的机械表,是老赵入伍时他爹买给他的,到这时已经在老赵手腕上呆了十七八年了,表盘的电镀层已经磨花了,露出了铜的底色,很有点时光岁月之类的沧桑感。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戴表了,但老赵却戴得有滋有味,还把这样一块老表戴出了一种民族自豪感。常说,老上海就是老上海,质量真的是没的比,给块英纳格都不换。没人反驳他,但他给块英纳格都不换的话估计也没几个人真信。
老赵频繁看表的时间一般是晚上九点来钟。九点四十就该吹熄灯号了,老赵召集开会通常是九点到九点十分之间,散会还能给大家剩点洗漱时间。
来车队干队长之前,老赵是学员队的队长。再之前,老赵在车队干过副队长代队长,算是车队的老人。只是我不知道,我从别处调来机关车队时,老赵已经调走了。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刚调来不久的那年夏天,我开大客车拉他所在的那个系的学员,去焦庄户参观地道战纪念馆。一个学员队一辆车,他那个队上了我的车,他便坐在了我的副驾驶座上。
从还没上车,他招呼学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特能咋呼的家伙,嗓门大,说话也粗鲁得不得了。而我印象里,学员队的那些队长们,大都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年龄也比他小得多。后来一上车他便跟我套起了近乎,尤其开车之后,他坐在那里,那模样很有点指点江山的味道。问我叫什么名字,哪年兵,家哪里的,甚至还夸我车开得不错。然后便说起当年他在车队干队长的事儿。说他在车队时,兵们跟他都很亲近,都很听他的话,接下来还说到他去西亚某个国家做技术顾问的事和那里的风土人情。一开始我还应付他几句,但他夸夸其谈,拿我很不当外人的模样,却让我很有些反感。
也是因为那天的天气实在不咋样吧,太阳很毒,我们出了北京一路往东走,都是侧迎着太阳的,老式的大客车里没有空调,很热,也很晒。开了车窗,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好久没下雨了,风里还裹着尘土,扑到脸上,皮肤上就有了那种让人讨厌的颗粒感。我的心情就显得有些焦躁和不耐烦。
后来我忍了又忍,还是没能忍住。我尽量用平静些的口气对他说,我看你还是坐到后边去吧,你这样实在影响我开车了,一车人,出了事儿谁负责?
我觉得老赵可能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奚落。尤其是,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少校军官,而我不过是个扛着一粗一细两道杠的小兵。
起初,正在兴头上的老赵愣了一下,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似的愣了一下。而后便显出一脸的尴尬来。呵呵——没错,当时他就是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类似干笑。然后便一连串说了几个好。又说,我不吱声了。
之后老赵果然安静了,只是有时会瞟我一眼。我故意不去理他。有几次,我感觉他又要对我开口说点什么了,可是我拉着那样一个不爱搭理他的脸子,他的话就又憋了回去。是憋了回去,有几次,我甚至听到了他使劲儿咽吐沫的声音,嗓子里的咕噜声。
这时我就觉得这人其实蛮可爱的,被一个小兵堵成这样,而且还是自己曾经做过队长的车队的兵。我心里有种恶作剧的快活。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老赵就要来车队干队长了。
其实也算不上特别突然。那之前有半年多的时间,车队原来的队长升职走了,分队长安林被提拔上来做了副队长,暂时代理队长的工作。原本大家觉得安林会被扶正,可是半年里连续出了几次事故,尤其有两起事故的用车,还没经管理处调度室同意,是队里私自派出去的。所谓队里私自派出去的,也就是那么个说法,其实也就是安林派出去的。于是上面便坐不住了。有一阵,管理处的吴处长差不多就住到了车队,代为管理起了车队的事务。安副队长被晾在一边,可怜巴巴的,好像变成了吴处长的小跟班。
也就是这个时候,有消息说,车队这摊子安林撑不起来,可能要来个新队长了。人选有几个,一个是训练团现在的副参谋长刘西武,他曾经在车队干过分队长。一个是管理处分管油料的助理李全。再一个便是老赵了。老赵全名赵建设。
可是听说三个人都不愿意来。机关车队负责全院办公、教学和生活用车,要跟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原本就容易招惹是非,而车辆又是容易出事故的东西,一旦出点事最后都会落到队长头上。这官不好当。
可是有一天,老赵还是来了。是这年夏天的一个上
午,大太阳在头顶上晃着,能把人晒出油来。车场的水泥地上腾腾地向上冒着热气。安副队长手里拿份报纸,遮在头顶上,满车场转悠着喊我的名字,听到喊声,我从车库里跑出来,站到了门口阴凉里,安副队长也到了我跟前。安副队长老家山西朔州的,虽然当兵也十来年了,可一口朔州话还是说得好像从鼻孔里哼出来的。他跑进阴凉里,先骂了句,操,真热。又撩起短袖衫的下摆,胡乱在脸上抹着,然后说,去接人,赵队长。
他的话已经尽量说得很普通了,但我还是一头雾水。或者去接人我听懂了,但后边的什么队长,我却没弄明白。一个是没听太清楚,一个是我开的是大客车,要接某个人也不该用到我。因此,他的话即便我已经听清了,也还是一头雾水。
于是安副队长便给我解释了一通,又把两只串在一起的钥匙从裤子口袋里摸出来,交到我手里。开三菱去,他说。
虽然我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但还是觉得有些奇怪,要接赵队长,队里有的是卧车,随便找个人去不就得了。即便要开三菱去,也有的是开卧车、开吉普的司机,或者他安副队长亲自去,好像也不丢他什么份儿,这差事怎么也不该落到我头上。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疑问,我已经接过钥匙,准备去开车了,安副队长又说,是赵队长点名让你去接他的。
听得出来,安副队长这么说,他自个也觉得有点儿奇怪。
老赵所在的系跟院本部隔了十来里路,我到时他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应该是他们系里和队里的,在等着给他送行的吧。大热的天老赵一身军装穿得板板正正的,黑皮鞋好像刚刚上了油,锃亮。
见我一个人敲门进来,大家似乎都愣了一下。伸长脖子朝我身后望,可能是没看到想看到的吧,又齐刷刷地把头扭向了窗户。从那里能看到我停在门口的车。而那里显然也没有他们想看到的,这才看向了我。
他们不这样我还没什么感觉,一这样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怎么说老赵也是去车队干队长的,按照惯例,即便管理处不跟个人来,安副队长也该跟来的吧。但这管我屁事儿呢。对,管我屁事儿呢!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我对这人还是没太有啥好感,他点我的名让我来接他,我也就是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对当初那点事儿耿耿于怀?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老赵不是那样的人,甚至因为当初那件事,老赵对我那种脾性竟然是有些欣赏的。
我接他回去,他还是坐在副驾驶座上。车一开,他的嘴巴便张开了,再不肯闭上。他先是高声大气地抱怨了一句,他奶奶的,连个鸟人都不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不过他的声音里却听不出多少怨气。看我没接他那个茬吧,他便把头扭向了我。对了周昕——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名字从他嘴里冒出来,那种熟络感,就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呆了很多年了。我就喜欢你这劲头儿,他竟然说,我开好我的车,我想听你叨叨就听你叨叨,不想,你就乖乖地给我一边儿呆着去,安全第一,我管你是谁。
他这么一说,我就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不好意思啊队长,我那天心情不好。
没事,没事,我喜欢!他竟然说。
老赵是七九年入伍的,陕西安康人。开始在训练团,八一年提干不久便随院里的一个工作组去了西亚,在那里呆了两年多,学会了开车,回来便到了机关车队,干分队长。在车队呆了十来年。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当初老赵对我自来熟的那个样子,我也就理解了,他对车队的那种亲近感,可能不是我能完全体会的吧。
老赵到了车队,跟回老家差不多,老兵们都很听他的招呼,新兵们自然就不敢奓翅。新官上任三把火也省了,只是把他干代理队长时的习惯又捡了起来——开晚上会。也不是每天都开,他整天就在车场和宿舍楼里转悠,尤其他靠在他宿舍门的门框上,看手下的兵们进进出出,如果他觉得该开了,就会让文书通知各分队,把大家集合到俱乐部去。
老赵晚上的会通常都开得很简单。往队前一站,先说大家都辛苦一天了,还把大家召集起来,实在不好意思,我就说几句话,说完了大家赶紧回去休息。然后口气便会变得严厉起来。不过,老赵说的话不外乎安全、车辆检查、严格派车制度等等,并无什么新鲜东西,而且一次一次也差不多。于是就有人觉得他絮叨,私底下便开始嘀嘀咕咕的。
这抱怨和嘀咕老赵应该也是知道的,但他依然是我行我素。说来也怪,就是他这样隔三差五地絮叨絮叨,还真有效果,后来老赵在车队呆了差不多两年,两年里竟然一起算得上事故的事故都没有发生过。所谓算得上事故的事故,部队对交通事故的定性是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来划分的,普通的小刮擦,不在事故之列。
后来,我已经退伍了,电话里再说起这事儿,老赵便不无得意地说,一群混小子,几天不敲打敲打就扬风奓毛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开会就是要给他们提个醒,真出了事故,哭鸡巴都来不及。道理还用讲吗?不用,来车队的兵,少说也都一年以上的兵龄了,该讲的道理之前早有人给他们讲过多少遍了,再讲,无非还是那些。再说,又不是幼儿园的小孩子,该懂的也都懂了。他们需要的是提醒,是警示。
老赵说,你看我靠在门框上,抱个杯子,好像很悠闲的模样,其实我是在看呢,看看又有哪几个小子想炸奓了。
老赵说,奓翅就得敲打。
车队老出事故,就是全院的焦点,走到哪都会有人打听,又怎么了?又出事了?严重不严重啊?不出事故也就变得稀松平常了。老赵在队长的位置上也就呆得有些平平常常,默默无闻。这期间老赵给老婆孩子办了随军。
其实按规定,副营职家属就可以随军了,而这时老赵正营都已经好多年了。可是原来他老婆一直不愿意来。一个是他老婆在老家有工作,而且是事业单位,来了,就有可能面临失业,至少也是短期失业。另外,据跟老赵相处比较久的老兵们讲,两口子关系很悬,他老婆很多年都没有来部队探过亲了,老赵回去的也不多。有过要离婚的传闻。
他们甚至猜测,他老婆可能在老家有人了。
还有人说老赵在这边也有个相好的,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就是驻地一个女的。他们说的那个女的我见过。
有一次和老赵一起开车出去,回来的时候,顺道,老赵就让我拐去了那个女的家。那女的和她老公都在,老赵和他们说话都非常随意,给我介绍他俩的时候指着男的说,我哥们,然后便说出了那哥们的名字,又指着人家老婆说,我媳妇。因此我觉得那传说不是太靠谱,至于老赵跟那两口子到底什么关系,我感觉也就是不错的朋友。
这时候办随军,可能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他们的女儿晶晶已经快七岁了,眼看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如果再不来,将来再转学过来,肯定对孩子不好。这是老赵说的。那时他们一家已经在家属院安顿下来了。那阵子,车队的几十号兵,谁没事了就三两成群地跑去他家给他温锅,空手去,蹭一顿饭回来,主要是去看望一下队长夫人和孩子。
开会的时候老赵就说,你们这帮小子,再这么下去,非把我吃趴下不行。他说他的,大家照去。他还是得留大家吃饭。温锅嘛,不吃饭怎么行。大家嘻嘻哈哈客气两声,就又嘻嘻哈哈、呼呼啦啦坐下了。等大家都去过了一遍,反馈回来的信息经过汇总、分析、总结,再加上各种想象力的发挥,还真就发现了他们两口子的一些问题。
老赵妻子姓什么叫什么好像没几个人知道,大家只是叫嫂子。嫂子对大家还是非常热情的,去了便忙着招呼,拿烟上茶。但她却很少跟老赵有什么交流,即便两人说话,说的也都是该说的那些。另外,老赵这个人性格里就有些人来疯,跟大家说话的时候,很容易嗓门就高上去了,常常还说得神采飞扬。嫂子有时就会在一旁皱一皱眉头,躲去了别的屋。更多的时候,老赵在那高谈阔论时,嫂子都不会在场。
而且,老婆来了,老赵却还住在队里。
老赵说,这帮小子,不盯着不行。
老赵的女儿晶晶长得很像她妈,很娇小,也很乖巧的模样。晶晶刚来北京那阵子,只要不上幼儿园,老赵就经常带了她到队里来。那段时间,大家出车回来,经过老赵门口,经常能看到父女俩在一起。
如果晶晶来了,出车回来的兄弟们,也喜欢跑去老赵屋里,逗晶晶玩。而以往,老赵屋里也就是分队长们、老兵们,经常会呆在那里,一般像我这样的新兵蛋子却避之不及,可因为晶晶大家都来了,老赵屋里就显得特别热闹,特别聚人。
可是忽然有一天,晶晶来队里的时间便少了。这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也没人太留意,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很少能在老赵屋里看到晶晶了。即便有时晶晶自己跑来了,呆上一会儿,老赵也会差个人把她送回去。
老赵说这是上班的地方,老让孩子呆这里不合适。老赵说得很有道理,大家也觉得老赵说得很有道理,可大家还是觉得老赵这么说时,是有点言不由衷的。而且大家觉得,老赵这么说时,即便脸上看不出什么来,可心里好像并不开心。当然,大家都是他的兵,好像也没太有人想钻他心里去,看看他到底想什么。
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吧,老赵迷上了写字,毛笔字。大家看到,老赵买来了笔墨纸砚还有字帖等一应家什儿,在他房间的桌子上摆开了,没事了便写上几笔。那个大玻璃杯就在他手边,跟原来一样,不是装满了茶水便是满满一大杯子的咖啡。他写几笔便会把杯子抱起来,长时间地看着自己写下的那些字,很严肃、很认真的样子,像在品什么滋味儿,喝几口水,有时还会在他写好的那些字上描上几笔。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老赵突然又不练字了。有一天出车回来的一个哥们看到老赵把他写好字的纸,从桌上抓起来,扯碎了,又狠劲地投到地上。那样子,恨不得再踏上一脚。看到门口有人,老赵还冲那哥们吼了一声,看什么看!
后来老赵给那个哥们赔礼道歉时解释说,烦死我了,越写越鸡巴难看。然后老赵就真的不再练字了。可是不再练字的老赵却像丢了魂儿。虽然还是抱着那个大杯子靠在门框上,抱着那个大杯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还是召集大家开会,可大家还是觉得这时的老赵跟以往不太一样了,可哪里不一样呢,好像又没人说得上来。
就这么过了段时间,老赵竟然又刻起了章子。弄了些石头、刻刀,没事了就抱着刻。让人觉得他还是放不下他的书法的,只是变了个形式而已。有次他竟然用刻刀把手划了条老大的口子,伤在大拇指的背面,很深,差不多把整个拇指都贯通了。我出车回来正好看到他在水房里冲洗伤口,我问他怎么不去门诊部处理一下。他竟然瞪着眼冲我吼,有那么娇气!然后朝水池里狠狠甩了甩流出来的血,回房间去了。
我觉得,这时的老赵真是有点怪怪的。
老赵离开车队时,我已经退伍走了。我退伍时老赵曾把我拽到他房间里,从床底下抽出老大一捆没有装裱的字画。说这都是那几个月练字时向人求来临摹用的,现在没用了,让我挑几张,回去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送送人。我就从里面挑了几张喜欢的。我没打算送人,只是想将来装裱好了挂在家里。但是后来这几张字画还真都被我送了人,现在想想,还真是有些后悔,怎么说都是老队长送的,留着,是个纪念。
老赵是转业离开车队的。老赵从学员队回来车队干队长,一年后刚调的副团,如果不是自己要求,是不会这么快被安排转业的。他转业离开前,我往回打电话找他聊天,他说起这事儿。我问他为什么要转业。他说烦了。问他单位联系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当时还想他也许不用着急的,我们院转业在北京的人那么多,他要找个像样的单位不是什么难事。没想到他竟然说他不想呆在北京了。我问他去哪。他说还没定。
我再次往回打电话时老赵已经离开了。电话是安副队长接的。这时候安副队长已经接替老赵成了队长。当初老赵虽然抢了他的位置,但毕竟老赵比他大几岁,后来他俩好像相处得还不错。只是这家伙那次办的那件事,让我一直觉得他不怎么地道。那次去接老赵,等我把老赵接回来时,他和管理处吴处长都等在门口了,我一把车停下他便冲我吆喝开了,告诉你等等我,你怎么一个人跑了。然后又上去握着老赵的手,一脸的歉意。
不过,一旦离开了,这种事也就淡了。想起更多的还是他的有趣,他说话的口音,他每次说完怕人听不懂都得解释一番的模样,想想都让人想笑。
安队长也知道我和老赵私交不错,就跟我说起老赵转业的事儿来。安队长说,真不知道老赵吃错什么药了,本来吴处长转业,他接替吴处长的位置已经成定局了,可是他竟然也要求转业。你走就走呗,正儿八经找个单位,也不错,可他竟然工作也不要了,还把老婆孩子扔北京,自己跑大连跟人开公司去了。
听得出来,老赵这事儿连安队长都觉得有些恼火,有些不可思议。如果老赵不是他的老上级,不是长他几岁,真该要骂娘了。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电话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尤其手机还是老板们专用的。老赵离开北京之后,我始终也没能跟他联系上。也就是,断断续续的,原来车队的兄弟们打电话给我,或者我打电话回去,才能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信息。
好像是,老赵去大连呆了一阵子,生意没有做成,就又一个人跑去了深圳。但是这期间他一直都没有回过北京,只是通过邮局往家里汇过一些钱。大概一年半的时候,他老婆在报纸上登了个寻人启事,然后到法院跟他起诉离婚了。
又过了半年,这应该是法律程序的原因,法院在老赵缺席的情况下判了他们离婚。大概就是在这之后不久,我去北京出差,顺道回去看了看,去了老赵家。老赵在转业前已经托人安排好了他老婆的工作,好像还是她的老本行,在一个工商部门。我去时她上班去了,只有他们的女儿晶晶一个人在家。
这时晶晶已经在学院自己的小学上二年级了。脖子上挂串钥匙。看到我竟然还认得,还高兴得不得了。但我的感觉是这孩子太孤单了,应该是妈妈上班去了,放了学她便一个人回家,做作业,完了就只有电视机陪着她了。
好像孩子们都喜欢发问,晶晶问我的问题都是关于她爸爸的,比如他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后来我离开的时候,晶晶突然跑去把书包抱了来,从里面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显然是从作业本上扯下来的字条,郑重地交到我手上,说,周叔叔,这是我从我爸爸汇款单上抄下来的,你能帮我把我爸爸找回来吗,我真的好想他。
字条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但我还是看清楚了,那上面的地址竟然是河南濮阳的,跟我所在的济南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怀揣着那张字条,从北京回来,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濮阳。
但我在濮阳没有见到老赵,那个地址是他早年退伍的一个战友的。我对他的那个战友说明了来意,但他却告诉我,钱是他帮老赵寄出去的,而且这钱还是他替老赵垫上的,但老赵人却不在濮阳,具体老赵在哪他也不知道,都是老赵打电话给他。
我相信他没有说谎。
我把晶晶给我的那张字条留给了他。我还在那张字条的边上写道:老哥,这是晶晶给我的,她让我帮她找你回去,她说她想你了。然后写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我对老赵的那个战友说,如果老赵来了,就把这个字条给他,如果他打电话来,就把这张字条上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他听。
然后我给他留下了我家的电话号码。
大概一个月后,半夜里,我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爬起来接了电话,喂了半天对方都没有吱声。但我明显感觉到,电话那边是有人的。我还以为是哪个哥们的恶作剧。我一起退伍回来的战友,尤其那些还没找上女朋友的家伙,他们就喜欢干这种鸟事。我正打算把电话挂了,就在这时,里面却哇的地一声哭了起来。
确实是哇的一声。那声音在安静、阒寂的夜里,即便是从电话听筒中传来,仍然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好像憋了很久。
是赵队吗?我问。
过了好长时间,哭声才终于停了下来,又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我之所以说那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因为我真的听不出那声音是老赵的,那声音孱弱得让我怎么都跟老赵以往那高亢洪亮的嗓门对不上号。
他说,晶晶,她不是我女儿。
说完,电话便断了。
再听到老赵的声音已经是十来年以后了。有一天老赵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老赵在电话里咋咋呼呼地对我说,没想到吧小伙?他的声音让我一下子便把当年他带学员去参观的模样想了起来,还是那样张扬。我说没想到,确实没想到,您老人家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老赵便嘿嘿笑了两声,有了些不好意思,然后告诉我他刚从国外回来,晶晶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他是特地赶回来送晶晶入学的。
据老赵说,他现在新加坡定居,开了一家书画店,卖别人也卖他自己的作品,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他也没有再成家。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