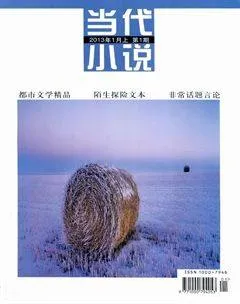老木在春天的理想
一
这个春天老木把墙上写满了大字,后来在墙上写他的倒计时,告诉棉花叔叔就要回来的时间。老木每写完一行大字就扭头看一次那只叫棉花的狗,严肃地教导棉花,一定要好好学习。棉花人模狗样地蹲着屁股,老木对棉花说:不好好学习,一辈子也念不会我写的大字。老木的脸很严肃,老木说:这是我春天的计划。老木挥挥手,用粗糙的手指点着墙上的大字,说这个字叫“唱”,这个字叫“戏”。这个字叫“找”,这几个字叫“村主任”。老木把墙上的字大声地念给棉花,一字一顿:唱戏,今年春天唱戏。然后老木说:我们去找村主任是为了唱戏,我一定要让你叔叔回来看一台大戏!你叔能听戏全村人都能听戏了。
老木后来又在墙上搞了个倒计时。老木竟然会在墙上写数学算式,这些算式在他儿子流浪回家的时候还写在墙上:33-1=32;32-1=31……老木对棉花解释说,庙会是三月十九,现在是二月十七,离你叔回来还有32天。老木说倒计时很重要,这对我活在春天是一种动力:香港和澳门回归,奥运会举办,全中国都搞倒计时;三叉家娶媳妇也搞倒计时。人有念想活着才有意思,就像一头驴看见了前边的青草,像我的棉花看见食盆子里的鸡骨。
老木反复强调着:我在春天的理想,就是村里唱一台大戏!
那个电话是几天前的一个清晨打来的,老木接电话的声音把棉花吓醒了。老木简直在对着电话喊,你真是老二,是我的兄弟老二啊!你怎么舍得打一个电话啊——老二在电话里的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老二说:我又梦见老家了,我在梦里听见了敲锣声,戏台上的长号,还梦见了那个当年的青衣。哥,我想咱家的戏了。棉花把门拱开,听见老木说:你,你回来吧,老,老二。咱村年年都有戏,还有青塘、槐塘、柳塘都唱。哥和你一起去听。棉花看见老木的眼角挂上了一层泪,浊浊的,像爬在泥墙上的一串蜘蛛。老木撂下电话,一双粗硬的手掩住脸,棉花的眼也酸酸的。老木的皱纹终于挡不住泪珠,泪蛋儿扑扑嗒嗒地砸到地上。他搂住了棉花,棉花代替了老木的儿子,老木的儿子在一个遥远的城市打工。他搂着棉花呜呜地哭了一阵,冲着棉花说:儿呀,你叔他可要回家了,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回家了啊。他问村里唱戏不唱,我已经满承满揽了,我对他说唱。我都不知道认不认得他了,我的棉花都长老人斑了。你叔他其实一直想回来呀,你奶奶病重的那一年他的腿被一个卖菜的撞断了,幸亏卖菜的骑的是辆三轮,不然老二这混蛋早就丢命了。你奶三周年他本来准备起程了,可他的血压又高了。他的腿瘸了,他身上的肉却长起来,你叔肯定又白又胖了。老木说:叶落归根,这个混蛋要回来了,还想那个青衣,那个青衣都老了。他呼呼站起来,往街上走。往常出门都是棉花的头先伸出街门,可这回老木的头先出去了。走了几步,老木用袖子使劲地抹了一下眼,对棉花说:我得往坟上去,告诉他们,老二就要回来了。
那天清晨后,老木就躺下了。这是老木的习惯:他老婆不在的那年他在屋里躺了三天,等儿子对他说路上的白幡都被风刮到地里被风吃完了,老木才起来;老娘不在的时候老木又在屋里躺了三天,第四天的清晨刮了一场大风,风裹着雨把院里和路上都扫净了,老木才走出屋子。老木说:我真不愿意看到飘在路上的那些黄纸,不愿意看到我滴在路上的那些眼泪,那些泪硌得我脚底板疼。十指连心,我的脚疼我的心就不会不疼。
这是老木的习惯,有心事的时候就在屋里躺上三天,像去阴间走了一回;而且基本绝食,不到第四天绝不出来。那条叫棉花的狗知道他的脾气,就趴到门口等,瞌睡了,把头蜷下去。墙上的字是老木第四天写上的,北屋的墙上被他涂得热闹得很,像趴了一堆绿头苍蝇,成了花墙。老木那天教育棉花后,瘪着肚子去汪小画的小卖部买了两盒粉笔,一副长远打算的派头。他庄重地对棉花说;这两盒粉笔都是用来写字的,写满了,咱家的墙就成花墙了,过年的时候就不用买年画了。老木把两盒粉笔拿给棉花看,一盒红色的,’一盒杂色的。棉花理解老木为什么买彩色粉笔,因为墙本身都是白的,虽然墙上的白已经不再多白了。老木把粉笔搁在饭柜的顶层,探出头往门外睃几眼,门外是一棵已经绽开花瓣的桃树,桃树下是一个破瓦罐做的狗食盆子,盆子被狗舔光了。太阳从盆壁上射下来,在盆底下打转转,老木探头时盆壁映出他的光头。老木看看棉花心里疼一声,软软愧愧地对棉花说:我会把这几顿给你补过来的。
老木和棉花共同吃了一顿饱饭后,从过道的顶棚拽出了锄头,拾了一块瓦片把锄头的锈气擦抹掉,再用一块破布把锄把擦了两遍。他开始修理院里的地,把院里的杂草都铲除了,把院里藏在旮旯的树叶弄到了一堆儿,用一把火把树叶烧了。树叶积存一秋一冬又半个春天的香气在院子里弥漫,袅袅绕绕地飞过院墙。老木移着碎步,盯着树叶烧出的烟瞅了半天,想起几天已经没有吸过烟了,他的胃部开始痉挛。他抽了抽了鼻子,拽过棉花的头,从贴身的秋衣兜里掏出两块钱塞到棉花的嘴里,对棉花比了个吸烟的动作,让棉花去汪小画的铺子里买一种叫蝴蝶的烟。烟气慢慢地弱下去,渐渐虚弱得连树梢也缠绕不上了。老木开始收拾院子、收拾菜园,计划种上几枝月季、凤仙花、向日葵什么的。老二要回来了,院子里不应该再那么寡冷。
接着他开始找村主任,说唱戏的事儿。老木不知道村主任遇上了棘手的事。
二
穿过整整一条大街,老木看见了那座小黄楼。小黄楼的四边是蔓延几里长的瓦塘村工业园区,小黄楼的大门口吊着一个镀金的大铜牌:瓦塘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村主任兼着瓦塘纸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老木被保安挡住了,保安说:董事长不在楼上。老木说:在不在楼上我进去看看。保安说:不行。老木说:咋不行,我就进去看看!保安说:真的不行!老木不认得保安,保安肯定不是自个村的。老木说:我们村的主任我咋不能见见?保安说:董,董事长真不在楼上。保安喊村主任不叫村主任叫董事长。老木推着门往里挤被搡出来,棉花想替老木进去找村主任,可是门缝太窄钻不进去。老木拽住了棉花,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棉花,我们在外头等,我他娘的不信就见不着。春天的太阳不太高,但晒得身上痒痒燥燥的。老木和棉花往墙根的阴影里钻,上午站这边,下午往那边挪,墙体的阴影正好把他和棉花遮住。老木有时候困得想打瞌睡,头慢慢地往下磕,身子捣蒜样往下坠,头被膝盖一顶又醒过来。他问棉花:我睡着了吗?棉花摇摇头。他说:明天再来的时候得拎瓶“一块辣”。老木说的“一块辣”是小卖部里卖的一种零酒。第二天起床时,棉花已经把一个酒瓶叼到老木的眼前。老木懒得去接,老木说你再转给我干什么?棉花就叼着瓶脖子去汪小画的小卖部,半提酒把酒瓶灌满了。老木不让棉花叼了,老木怕棉花把酒洒了,也怕醉了棉花;棉花是醉过的,那次看他独自地喝酒,已经多了,棉花探着头把他脸前的酒咕噜噜地喝下去,像一个人一样醉了,头低低得很温柔,然后死死地睡着了。
村主任其实看见了老木。他昨天已经让保安问了,这个老木原来就因为一场戏。他没有答复,他没有答复是因为纸厂目前的命运危在旦夕,他顾不上这些小事情。他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化险为夷,不知道度过这个春天他站在楼上一览无余的纸厂还能否保存下去。他站在楼顶上,这是村主任或者董事长任小贵的习惯。几年来他习惯这样的居高临下,在夜色里俯瞰楼下的村庄,他看见他盖在村里的那座小楼,看见了那座楼后的空旷,紧贴楼墙的一棵大杨树、飞在杨树上的鸟儿,甚至能看见父亲的身影。耸在村庄的另一座楼是老地主家黄玉安的,小炮楼一样,现在差不多成了一座荒楼,楼顶上长满了野蒿。他更多俯瞰的是楼下的厂区:多气派啊,几公里长的厂区,那些串来串去的天车,冒烟的大烟囟,穿梭在路上的车辆。他坐下来,楼顶上有他的一个座位。每天都有人把他的座位擦拭两遍,在厂办的楼里大家都知道他的习惯,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跨上楼顶。可是这些厂又使他太累,每年需要摆平的事太多了:机械事故、产品争端、价格争议;更主要的是环保,纸厂的污水处理,这是纸厂面临的一件大事。几年前,按照国家政策,小纸厂要被砍时瓦塘的纸厂保留下来:这要感谢乡里和他的运筹帷幄,在1万吨以下规模要被砍时,瓦塘的纸厂合并成了长龙一样的生产线,规模又扩大了几倍,得到了年产几十万吨,成了省市挂号的造纸企业,生意如日中天。用当时镇长的总结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因祸得福。小黄楼就是这时候建起的,钱挣得多挣得快,那些分厂不在乎合伙抬一座小楼。也是那年投资2000多万的污水处理厂建了起来。纸厂在村西,污染处理厂建在村东,蜿蜒的水渠从各个厂区流出来汇到污水厂里。
现在任小贵遇到了棘手的事情:污水问题被暗访的记者发现了。其实他刚扳平市、县环保部门的一次暗访。然而,这次是七八家报社的记者,突然袭击,黎明的时候站在那个排水口,没有听到污水处理的机器声。瓦塘的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次真的被盯住了。
夜幕越深时他从楼上下来,看见了一辆小车。
从窗口看一眼老木,老木正和他的棉花往村里回。
三
老木又计划着躺下了。一计划躺下,他脑子开始发浑,身体面条样软起来,眼也睁不动了。他看了看凌乱的床铺,床铺好像已经在等待他了。老二又打过来一次电话,他和老二说了半个小时,告诉老二村里的变化大了:老坯房掀完了,路修了几回,村西是一大片厂区。老二问到村外的芦苇。他颓丧地说:没了,多好的苇子没了,小片的芦苇还有,小得可怜。老二说:几十天就回去了,回去再好好唠吧。老木说行,恋恋地还握着话筒。儿子也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儿子原来是在村厂里干,后来,跑到城里去了。
老木准备在家闷三天。老木往墙上瞥一眼,三天,三天以后一定要找到村主任。一定要得个准信,不然我卖房也要唱一台戏,不再指望他村主任个龟孙了。其实村里已经几年没唱过戏了,他对老二说村里年年唱戏,是说了谎的。村里人早对这个主任有意见了。要不,我去求村里人,以前村里唱戏就是村里人集资唱的。老木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把棉花的食盆子装满。然后他走向温暖的床。
老木是第二天晚上被棉花叫醒的。老木听见了街门被棉花拱开,棉花站在他的床边汪汪着。他坐起来时,棉花已经把鞋从地上叼起来,他知道这是棉花要他跟着走了。
村主任正蹲在房顶上,他刚送走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魏瞎子。每一次遇到棘手的事情他都会请那个神秘人物魏瞎子来,魏瞎子如果说能逢凶化吉,他就觉得棘手的事情处理得有信心。今天晚上,他从魏瞎子的神态看出了迟疑,他的心忐忑着。他坐在瞎子的对面,也把眼闭上。落地大钟敲响十下的时候,魏瞎子说:你不要泄气,你要静。他长舒了一口气,听出了魏瞎子的意思,其实几天来的征兆也是这样的,县里领导和环保局,甚至地税、国税、工商都在为他着急了。说透了是为这些厂着急,这毕竟是他们多年培养的纳税大户。其实在小黄楼里今天还有一场交锋、一场对话。县里的领导说:如果污水厂正常开就不会有今天的场面,国家的环保政策是抵抗不住的,再说老百姓也不愿意,都什么时代了还想糊弄。他说难啊,开与不开有时候真不好左右。开,开支太大,思想不好统一,20个分厂,加上每个厂的股份牵涉上百家几百个人啊。县里的领导说:看这次造化吧,如果能保住,污水厂必须正常开,然后,是企业准备好改产。他还想说,被制住了。
送走魏瞎子他踱上楼,俯瞰着夜幕里的厂区。机器的轰鸣停了,但各个厂里的灯还亮着,村里和厂区的路灯连成一条橙色的河流。他听见了春天的风声,原野里的树一簇簇在深夜涌动,他坐在楼顶闭目沉思。他想着他的小黄楼,一次次在小黄楼里的较量、小黄楼里的交易、那个神秘人物的光临和魏瞎子的到来。他在楼顶上坐着,望着村庄,听着远方传来的夜声。
棉花盯着楼顶,棉花忽然爆发了,棉花的汪汪声在野外回荡。老木在棉花的鼓励下朝着楼顶喊起来,他嗓门都喊哑了:村主任,我等你半个月了,我只求你一件事儿,村主任啊,你好歹给个话儿,不然我就不求你了……后来,楼顶的火星没有了,棉花叫累了,棉花的嗓子哑了,它瞪着楼顶,失望地伸着舌头,尾巴直棍样戳在路上。
天明了,春天的曙色慢慢地伴着早晨的清凉。棉花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小铁轮的滑动声。棉花的耳朵竖了起来,它警觉地睁开眼。它的头往上抬,它漫长又矫捷的身影被头拉动,臀部像一座小山,尾巴拖动着峡谷。棉花整个地醒了,它从鼻腔里发出一种闷闷的叫声,足以撼动一条峡谷的低吼。老木疲倦地躺着,身子可怜地蜷在一个墙角。昨天晚上太累了,没有回家,老木把身子蜷下的时候,棉花也紧挨着老木踡下来。后来,起风了,棉花看见主人蜷得越来越小,像麦地里的刺猬。棉花怕冻坏了主人,身子往主人的身边靠,挡在风刮过来的方向。
现在,它的耳朵竖成两只大喇叭,搜索着大门的响声。它呼地站起来,像平地上拱起的一座小山,两眼火炭一样燃烧。开门的是一个保安,接着它听见了从楼上下来的脚步声,有节奏但透着疲惫。锃亮的小车前站着一个精干的小伙子,车门打开,小伙子的手恭敬地扶着车门。棉花的身子又往上耸,臀部上隆,耳朵抖动,身下的阳物也透出红红的阳头。棉花使劲地拱醒了老木,而且叼住了他的衣裳。老木听见了大门声,汽车已经发动。老木从地上跃起来,一个身影在往小车里拱了。棉花就是这时候冲过去的。老木跨了几个箭步,甚至在跨第一步时打了个趔趄,他的一只手抓了一下大门。村主任没有想到老木和棉花都没有走,在他扭头的一瞬间老木已经奔到他的身边,而且嘴里喊着村主任、主任。他扭回头,手里捏着一个金黄的手机,他伸出手,来推老木。一只手去开车门,做出了弓下的姿势,想躲开老木。老木粗糙的手又拽过来,还在喊着村主任、主任,而且和他一起按住了车门。就是这一次,村主任把老木推了个趔趄,老木的身子晃了几下;昨晚的疲惫、凉风的侵袭使他像一棵草一样虚弱,终于在几经晃动后趔倒在地。发动机的声音大了起来。棉花声嘶力竭地汪了一声,凌空扑了上去,它整个身体飞起,浑身的毛奓了,眼喷射出一股烈火……它把晚上的失望、多日等待的煎熬一起发泄了……
四
老木的头沉,浑身酸得发木,屁股后像坠着个山。老木感觉自己发烧了,胸口烫得像一块炭火,眼皮抬一次像掀动一块井盖。老木想自己这次不能再躺三天了,我还要去找棉花呢,没有棉花我怎么活啊!但他想起棉花又害怕起来,他在心里知道这次棉花凶多吉少了,虽然村主任至今没有派人来找棉花,但他还是把棉花赶走了,让棉花躲躲,棉花不走,是他把棉花赶跑的。他说:你走,你得躲啊……村主任和他的保安是不会让棉花活下去的。他望望门外,天阴了,棉花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他拖着酸胀的身板往屋里回,望望墙上他写下的字,那些字像一条条壁虎在墙上钉着。他继续写上了他的倒计时:距庙会还有31天。他又在墙上写:棉花是在这一天前跑的。他又写了一句:我想棉花。他久久地盯着墙,盯着墙上的粉笔字,字仄仄歪歪都不像字了。他烧得有些发晕,他勉强撑起身,他说:我不能倒下。他想把这一句写在墙上,写在倒计时的中间,这是对自己的支撑,自己倒下就彻底地完了;恐怕连老二也见不着了,儿子回来也见不了爹了。他从地上撑起来,两只手抠着地,屁股使劲地朝上撅,一寸一寸地撅高,然后手摁到了墙上,手一点一点地往上扒,头慢慢地抬起来,光头又在阴影里晃了,屁股和头又在一条线上了。得熬一锅酸汤,熬了酸汤发一场汗就好了。这样想着他把腰弓下去,在碗柜里翻腾着,拼命地想找到一块老姜,碗柜里的碗筷呼啦呼啦,像涨潮的水翻卷着乱石。终于,翻出来一块老姜。不小。老木自语说。那姜像狗蹄瓣一样,他又想起棉花了。接下来,老木找到了半瓶醋,老木平常不大喜欢吃醋,醋瓶子里已经泛起了白沫。葱是很快摸到手的,两条长长的大葱,他慢慢地剥去大葱的干皮。他支起了锅,烧起了柴火,那些葱、姜、醋都搅到了一起。他烧着锅,半眯着眼,火时断时续地燃着833RFWuXEHiqOsnuFt5qJljLge+7hkk7AEho6MnYba8=,精神提起来时就把火加得旺一些,提不起精神了火就燃得弱了。火苗子忽忽悠悠,有时差不多已经灭下去了,只有一星两星的火在灶里挣扎着。一锅姜汤终于熬好了,他却蹴在灶前挺不起来,身上的火炭越发烧得厉害了,烧得他要化成一块炭。他的身体拼命地想往一疙瘩蹴,蹴成一个蛋儿。没办法了,他知道自己必须眯缝一会儿,然后再把姜汤喝下去,然后就该出去找他的棉花了。
李柿把他从灶前弄醒时,他的眼前是几个几十个李柿在眼前晃。李柿是在村里跑腿的,村主任去小黄楼办公后,他守着原来的旧村部,还巡逻那条排水渠。李柿这小子噙了一口凉水往他的脸上喷:老木打一个激灵,凉水还真管用,老木的眼真睁开了。老木,你把你的狗交出来吧,这样唱戏的事可能还会有戏。李柿又往他的脸上喷了一口凉水。李柿又说:老木,别迷糊,把你的狗交出来吧!把狗宰了让村主任消消气。老木困得不想说话,李柿拍了老木的头,老木的头发像刚被太阳晒了一样,烫手,而且头发尖上沾满了一层水气,冒着一股烟。李柿把嘴里的一口水咽下去,李柿说:你是熬的姜汤吧?老木有气无力,说:是。李柿说:还是把狗交出来吧,我再劝你一句。老木说:李柿,我的棉花呢,你见我的棉花了吗?李柿说:老木,你的狗你还能不知道,你像它爹一样,你想法把你的狗交出来,让村主任把狗肉吃了,不就是一只狗吗?难道你不想听戏么,不想让你家老二回来听一场戏吗?难道狗日的狗比你的心事还重要么?倚着爬满烟尘的墙,老木的眼又挤上了。李柿又去噙了口水。但没等李柿喷出来,老木举起了烧火棍……
老木把那锅姜汤喝了,他憋着气,一连喝了几碗。然后他往床上躺,他在躺下去时说:棉花,爹醒来就去找你,找你,爹身上得有劲,不然到半路上说不清我都累死了,让别人家的狗把我吃了。喝了姜汤他又往身上捂了床厚被子,在他迷迷糊糊地睡去时,姜汤的能量爆发了,千万条小溪在他的身上汇流,他的背、他的胸、他身上的每一个枝都成了一条大河一条大海了,股股的热气从被窝里往外排往外流;他把胳膊伸了出来,胳膊上裹了一层浓雾,像一窝盘盘绕绕的蚯蚓。真管用啊,老辈子传过来的姜汤、偏方。他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电话是儿子打来的。
他还迷糊着,接电话时鼻音很重。儿子说:你是我爹么?老木才彻底醒了,他的眼窝里洇上了一股潮湿,他简直想哭给儿子听,但他忍住了。他还没有问儿子有事没有,儿子迫不及待地说:爹,我昨天做梦,我梦见棉花站在海边,绝望地瞅着大海,还梦见你站在大海的礁石上,爹,棉花和你都没事吧?没,没有。爹,棉花呢,我想听棉花叫两声!老木吞吐了,老木说你等等。老木下了床,他不知道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他得去看看院子里是不是站着棉花,他身上轻快多了。只是一出被窝,落下去的汗在身上凉嗖嗖的,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霉味,嘴里显得很淡,牙觉得使不上劲。他没有看见狗,他喊了几声棉花,没有棉花答应的声音。他在地上找,看见了隐隐约约的蹄子印,看起来棉花是来过家了,这让他更不放心狗了,真得赶快去找棉花了。他扭回身,又抓起话筒,骗儿子说:儿,棉花不在家,棉花可能去撒野了,没事,刚才我还见了棉花的,你在外保重。·儿子说:那我挂电话了。可是儿子没挂,儿子又问:爹,真没事么?老木又抓紧了话筒,他真的不想丢话筒。他想起那个早晨老二的电话,看见了墙上的倒计时,忽然对儿子说:儿子,庙会上提前回来,儿子,爹求你一件事,你想法攒两场戏钱,爹想听戏,不,是你叔要回来……老木的泪水终于哗哗地淌成了河。
五
老木去了坟地。老木盘腿坐在两个坟墓的中间,四周的麦苗在风中发出细微的响声,只有夜深里,这声音才听得真切。麦苗拔过了节,长到膝盖高了。老木裹了件衣裳,在等他的棉花,跟了他10年的棉花。老木木木地看着坟墓,把眼闭上了。他在心里盘算着一些名字,刘锁、李仁、秋林,都是在村里有些名气的人,还有那些经常蹴在一起的老家伙。后来他不想了,双臂慢慢地松开,一只手插进身下的土地,土地的凉气浸入五指,他又把另一只手插下去,土地的凉气又浸入五指。他没有把手提起来,他相信土地的凉气会马上变暖,或者手会把土地焐暖。他仰头看见隐约的村子,他心里一股一股地蠕动,像火车的奔飞,终于要奔突出来。他把头伏下去,终于发出了呜呜声,那种憋了太久的低吼,呜呜呜,呜……
麦苗慢慢闪开,麦地里弓起一个巨大的黑影。棉花披着露水弓起身子,伏得太久了,它抖了抖身,毛发上的露珠砸向麦苗,眼在夜色里如两道火光。它一步一步地穿过麦地,撒开蹄子,朝着那个呜呜的声音奔去。老木听见了,听见了棉花的脚步,听见了棉花踩在麦苗上、踩在土地上,听见了棉花在奔跑中的喘息,听见了棉花耸动的耳朵、伸出的舌头……他和棉花对着脸,脸上挂着潮湿的泥土:棉花瘦了、棉花的身子发长了、棉花的毛乱了,乱蓬蓬像一蓬鸟窝。孩子!他站起来扑向棉花。棉花的泪水滚了出来,看见主人更加憔悴。它伸出前腿和老木拥在一起,用嘴舔着老木脸上的泥和脸上的泪痕……
后来老木推开棉花,捋着棉花的毛,抚摸着棉花的耳朵,拽拽棉花的尾巴。老木说:棉花,再躲躲吧,你一定要和我一起等你叔回来,等我儿子回来,我去求村主任饶了你,你放心,庙会上的锣鼓一定会响起来的。棉花,无论如何你要保住你自己,你不要让我失望,让我痛心。不,我去求村主任的爹吧,求村里的老人,求刘锁、李仁……棉花!棉花!棉花啊!他伸出手和棉花告别……
夜色里棉花的鼻凹明亮得像一口深井,棉花抖抖身,它没有走,四条腿往地里使劲地扎下去。它抬起头,汪汪、汪汪地吼了起来。
……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老木又在写他的倒计时:距庙戏还有3天。老木把粉笔换成了红色,字在墙上一片喜气。然后老木领着棉花往村口走,老木说:棉花,今天你叔叔要回来了,还有我儿子也要回来。老木看见了小黄楼,看见了大片的厂房,只有几家的烟囱在冒气,那些不冒烟的厂都要改产了,大势所趋。村主任已经不再是董事长了。3天的大戏是村里人集资唱的,像往年一样,庙会前两天开锣。老木碰见了李柿,李柿和老木打着招呼,说:老木,我们都去搭戏台啦。老木没理李柿,棉花扭回头,对李柿叫了几声。村外已经是热热闹闹的景致:麦子秀穗,油菜花黄灿灿地开了。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