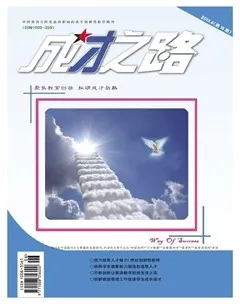新课程改革中课程范式的转换
“范式”是著名哲学家库恩创用的术语,出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库恩认为范式的本性是革命的,它存在于常规科学中。科学家用一定的范式解释疑难问题,当科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足够多时,科学革命便发生,继而产生新的范式。随着新范式的产生,科学便得到发展。
由库恩的观念看,课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改革实质就是课程范式的变迁。课程范式存在于常规课程之中,当常规课程出现了足够多的问题,课程改革随之发生,在改革中萌生出新的课程范式。
我国有学者运用时间间距递减指数函数的计算数据,指出当代课程是课程变迁史上产生质的飞跃的断裂期,当代课程改革是课程范式演变的另一个大周期的开始。而影响我国当下课程改革的课程范式主要有现代课程范式与后现代课程范式。那么,处于课程变迁断裂处的基础教育课程究竟在何种课程范式的指导下才能够获得新生呢?
一、对当前课程改革及其指导范式的简析
(1)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①国际上改革潮流的冲击。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较大的课程改革。这几次改革均关注学生的发展,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措施,无论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管理上都做了很大调整。这样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新课程改革。
②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实问题。反思我国传统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培养目标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课程结构不合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课程实施重“教书”和“背书”;课程评价重选拔、轻发展;课程管理过于集中。这些问题无一不影响着基础教育的质量和阻碍素质教育的进展。
(2)新课程改革的指导范式简评。
以上理由无一不昭示传统课程范式非改不可,但究竟以何种范式指导新课程改革的问题众说纷纭。在众多说法中,最有代表性的非后现代课程范式莫属了。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总体上说,它是对现代体系哲学、文化的一种否定。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主要特征:①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②不确定内在性。③对科学理性的质疑。④告别整体性、同一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理论被逐步引入课程研究领域。
后现代课程理论流派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姆·E·多尔的理论。多尔认为,后现代主义课程有四个基本标准:丰富性、循环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从这种观念出发,后现代课程将课程从文本扩展到师生的实践活动——教学对话。另一位后现代学者派纳认为,师生交流与沟通的内容是信息而不是知识,课程要促进学生个体意义的建构。他认为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是间接关系,提出了“概念重建”论与“理解课程”论。
应该说后现代课程范式中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对于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课程内容偏重科学知识忽视人文知识、教学手段单一等均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后现代课程范式之于我国新课程改革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①对真理、知识的怀疑:虽然后现代反对知识的绝对权威,但在提升学生主体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后现代学者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表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就是否定客观知识的传授,削弱科学知识的教育。这无疑会使学校教育陷入迷茫。从我国社会发展及对教育的要求来说,现实的迫切需要还是科学知识。我国掌握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比例很小,广大劳动者从事物质生产时基本上凭借的是技能而非科学知识。
②后现代课程范式之于我国的适配性问题:后现代产生的基础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而我国还远未进入后现代社会。虽然出现了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但更大范围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因此以后现代课程范式作为新课程改革指导范式难免有“三岁娃娃穿成人时装”之嫌。
那么,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审视当前课程改革与课程范式转换,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看待纷繁的理论,采用怎样的范式指导新课程改革呢?
二、态度与指导范式
(1)态度。笔者认为,但凡是成体系的理论终有它合理的成分,但绝不能因为此便颠倒主次,置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于不顾,而应吸取各国经验和历史的教训,切实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为促进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落实,我们需要持辩证的态度,既不能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也不能将败絮与金玉一并收入囊中,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的状况,审慎地借鉴。
(2)指导范式。笔者认为,课程改革应该以学生“全人”的发展为目标,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范式就是我们需要的范式。
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并非定式,课程的发展在于兼收并蓄,我们必须走出单一化、绝对化的思维误区。顾此失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经适应不了现代教育的要求。教育工作者应该让“分化和综合同时并进,多样和综合互相规定”“用多样规定综合,用综合规定多样,就是说,每一综合必须建立在多样的基础上;每‘一样’不是原始的单一,而是经过综合了的‘一样’”。综合并不是拼凑式的综合,而是仔细分析具体问题、进行辩证的综合。以讲授学习与探究发现学习为例,针对教师长期以来偏重讲授、忽视学生的主动性而提出的探究发现学习,将教师与学生的因素均考虑在内,是课程改革中的一个亮点。但如果将它与讲授学习对立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奥苏贝尔认为,无论是接受学习还是发现学习,都有可能是机械的,也都有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教师讲授教学得法,并不一定会导致学生机械接受学习;同样,发现学习也并不一定是保证学生有意义学习的灵丹妙药。如果学生只是机械地记住解决问题的“典型的步骤”,而对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却稀里糊涂,他们也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但这并不比机械学习或机械记忆更有意义。笔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大体上还是应以教师讲授、学生接受学习为主,学生探究发现学习为辅。教师在讲授时不能为了传授而“满堂灌”,而要讲究传授的方法,将讲授学习与探究发现学习辩证地综合在一起。
总之,我们对于任何理论范式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将其视为万能灵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辩证地综合。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致力于依据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的状况,创造出“本土”的课程范式,让我国的课程摆脱传统弊病,于断裂处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
[1]黄甫全.论课程范式的周期性突变律[J].课程·教材·教法,1998(5).
[2]程黎曦.教师与新课程[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4.
[3]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4]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辽宁省瓦房店市第二初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