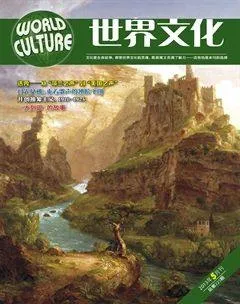《十日谈》今义
卜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先驱人物。他的小说《十日谈》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标志着近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的正式诞生。
谈到《十日谈》的意义,人们通常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歌颂个性解放,热情讴歌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第二,反对禁欲主义,对天主教会的荒淫无耻作了有力的讽刺和批判。《十日谈》出版至今已有750多年了,当初作者反对的对象或者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早已势单力薄:而作者当年所歌颂的对象业已发展甚至膨胀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成为现代青年生活的核心原则和处世准则。教会的权威早已不复存在,真正的强者从来无所求助于上帝,甚至连仅仅作为旗号也不需要。而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时髦,男女的爱情已经变得陈腐,早已失去了新鲜刺激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十日谈》还有意义吗?或曰:《十日谈》还有多少意义?
当然,如果仅从以上两个方面来思考和认识《十日谈》意义,那么,我们尽管还不能说它意义全无,至少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十日谈》的意义自然不能局限于以上两点,它的历史意义,在思想史及文化史上的意义,在小说史或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它在其它方面的意义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茅盾先生在论及卜伽丘时这样说道:“他并没受到檀德(但丁)的被压迫的痛苦,所以他从来不游檀德所游过的地狱;他只游当时治者阶级的‘天堂’。他的短篇小说集名为《十日谭》的,写了许多当时的支配阶级所喜爱的事情——奢侈淫靡以及俏皮的讥刺,他很快地成为富有阶级的宠爱者。”(茅盾《西洋文学通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卜伽丘曾潜心研究过但丁,著有《但丁传》和《地狱篇》注释。“但丁的著作第一次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五光十色的人类现实的总体世界。”卜伽丘一生都摆脱不了道德、女性和古典学这三大情结的纠缠,而在这三个方面,但丁无疑都是一个信马由缰的大师。但丁对卜伽丘影响巨大,可以说,“没有《神曲》,《十日谈》永远也写不出来。”(埃里希·奥尔巴赫《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相对于但丁的《神曲》,卜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一部“人曲”。这部“人曲”自然不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但无疑也提供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色彩斑斓的风俗画。这幅风俗画即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饶有趣味的,并且设若仔细察看某些地方,也还能另外发掘出一些深意。譬如,《十日谈》对妇女地位和身份的描写,对当时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婚姻伦理道德观念的再现,即便在今天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卜伽丘在该书《原序》中写道:“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警世小说’,一百段‘野史’,你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份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十天讲述的……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读到情人们的许多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古往今来的一些离奇曲折的事迹。”(卜伽丘《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以后所引该书译文均同此书,除在文后注明页码外,不再另注)具体而言,小说讲述的是,1348年佛罗伦萨流行可怕的瘟疫,居民死亡无数。十个青年(七女三男)在教堂相遇,他们约好到郊外一座别墅避灾。为了消遣,大家决定每天每人轮流讲一个故事,他们共讲了十0WioyluZJNiGTZONeOX1VQ==天故事。合起来正好100个故事。算起来,加上周末休息,他们一起在乡村共同生活了15天。在这15天中我们看不出任何男性处于中心地位的迹象或端倪,反倒是女性更受到尊重和赞扬,更加鲜亮夺目。
整个计划是一位名叫潘比妮亚的女士提出的,她在这群女青年中年龄最大,27岁。作为发起人,在到达乡间别墅后她又提议:“我们最好推个领袖,大家应当尊敬他、服从他;他呢,专心筹划怎样让我们过得更欢乐些。为了使每个人,不分男女,都有机会体味到统治者的责任和光荣,也为了免除彼此之间的妒忌,我想,最好把这份操劳和光荣每天轮流授给一个人。”大家听了她的一番话都非常高兴,于是一致推选她做第一天的女王。这里,推选领袖和统治者与性别完全无关,男女平等意识毋庸置疑。
在小说中,这种男女平等意识还体现在许多故事之中,夫妻之间、父女之间、兄妹之间男性并非总是处于上层或中心位置。在第六天故事第七,讲述了一个“菲莉芭胜诉”的故事,耐人寻味。“在普拉托地方,从前有这么一条法律,说来真是严酷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凡是妇女与情人通奸被丈夫捉住的,其罪与有夫之妇为贪图金钱而卖身者同,一律活焚,不加区别。”这时,有一位名叫菲莉芭的美貌多情的夫人爱上了城里的一位美少年,他们的私情被丈夫当场发现了。于是,丈夫就依据该条款将妻子告上法庭。在法庭上,菲莉芭慷慨陈词,她说:“法律对于男女,应该一律看待,而法律的制订,也必须得到奉行法律的人的同意。不过拿这一条法律来说,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条法律是完全对付我们可怜的女人的;其实女人的能耐比男人强,一个女人可以满足好多男人呢。再说,当时定下这条法律,女人并不曾同意过,而且也没有征求过我们女人的意见。所以这条法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公平的。”菲莉芭一番话引发满堂笑声,法庭内的听众都认为菲莉芭“讲得有理,讲得好”,“大家得到了法官的同意,当庭修改了这条不近人情的法律”(第567-569页)。法律条文中如果包含有男女不平等内容,是可以随时更改的。
在夫妻两性关系上,卜伽丘笔下的意大利远比今天更为开明,也更为松散。一夫一妻固然是当时普遍的婚姻形式,但是,在情爱或性爱方面,丈夫有情人,或妻子有情人也属正常,并常常得到作者的欣赏或赞赏。“小说家们和喜剧诗人们使我们了解到爱情只是在于肉欲的享受,而为了得到这个,一切手段,悲剧的或喜剧的,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越厚颜无耻和越肆无忌惮地使人感兴趣。”(第432页)在第八天故事第八,柴巴发觉妻子和自己的好友私通,立即威胁妻子,把那好友骗进家里的柜子,再把好友的妻子骗来,在木柜上行欢作乐,以报还报。但是,完事之后,四个人竟然在一块儿吃饭,说不尽的和好。“从此以后,这两个女人,每一个都有了两个丈夫,而每一个男人亦都有了两个妻子,从来没有过吵嘴骂架的事。”(第754页)这种二夫二妻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仿佛是身处当时历史条件下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方式。
总之,卜伽丘在小说中以“平铺直叙”手法,描写了意大利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刻画了众多鲜活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刻画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热情歌颂了女性的善良、深情、机智和勇敢等优良品质。在卜伽丘看来,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值得歌颂,他自称“天生是个多情种子、护花使者”(第352页),从小时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个儿心灵献给女性。这也就是卜伽丘写作《十日谈》的重要目的之一。为此,许多学者将《十日谈》与《红楼梦》《金瓶梅》进行比较研究,看来并非没有道理。
19世纪瑞士著名学者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指出:“这一时期的高级形式的社交,我们必须先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第387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妇女和男子的水平相等”。“在上层阶级中间,对于妇女所进行的教育和对于男人所进行的教育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毫不迟疑地使儿子和女儿都受到同样的文学乃至语言学的教育。的确,意大利人把这种古代文化看作是生活中最珍贵的事物,他是愿意他的女儿们也分得一份的。”由于教育的作用,上层阶级的妇女,在个性上是和男子一样地得到了发展的。因此,在那个时期的意大利,“不存在‘妇女权利’或妇女解放问题,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理所当然的。”(第389页)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似乎不存在妇女解放问题,因为妇女解放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事实。
当然,《十日谈》不仅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第四天故事第一,卜伽丘讲了一个悲惨的恋爱故事。萨莱诺的亲王唐克莱有一个十分俏丽的女儿,名叫绮思梦达,出嫁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做了寡妇的绮思梦达只得重新回到父亲家里。不久她偷偷爱上了父亲的侍卫,一位出身微贱的青年。他们偷偷约会,后被唐克莱发现。面对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恋情,父亲愤怒地斥责女儿。绮思梦达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同样的效用,同样的德行。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煞掉……”(第363页)唐克莱一意孤行,杀死了女儿的情人,取出心脏,盛入金杯,送给女儿。女儿把毒液倾注在心脏上,和泪饮下而死。唐克莱只得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在绮思梦达看来,如果从才德方面看,她的情人无疑是高贵的:而满朝的文武官员不过是鄙夫而已。
这一群青年男女离开佛罗伦萨共15天,作者写道:“虽然我们所说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多半都容易撩拨人心;虽然我们—直都在吃喝作乐,唱歌跳舞,这对于那些意志不坚的人,很容易受到诱惑,因而做出败坏德行的事情,可是照我看来,无论是你们小姐或是我们少爷,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没有半点儿不得体的地方。”(第966页)他们一直都十分正派,相处得十分和谐,像兄弟姐妹一般真诚亲热。并且,他们懂得见好就收,他们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时机,回到了当初他们出发的地方佛罗伦萨。在离开佛罗伦萨的日子里,这帮青年男女整天吃喝玩乐、唱歌跳舞,为打发无聊时光轮流讲故事。“仿佛人类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在那恋爱的十天里找回自我、与喜爱的女子和时髦的男青年一起讲述一百个小故事。”他们生活完全无忧无虑,从不为生活的小事儿烦恼。在他们外出的15天中,从未出现过食物短缺,或钱财紧张的问题。他们居住的环境总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他们之间除了偶尔有一点戏谑和逗趣之外,从未有过任何矛盾或争吵。他们之所以能过上如此悠闲自在的生活,因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显然全都是些出身高贵的”青年,当然,他们还带去了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这些仆人负责他们的日常起居事宜。原来秘密就在这里!这也许是卜伽丘也未曾想到的小说的又一层意义。如果没有这些仆人精心伺候,这帮青年人的“十日谈”大概会难以为继,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快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