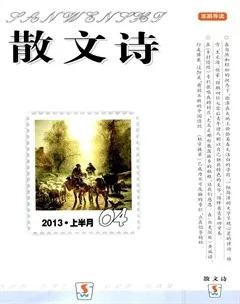赏析
国内推介哥尔说他的诗是从表现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转变,表现主义是美术流派,以德国画家为主,到法国,野兽派和表现主义一脉相承,表现主义更强调主观激情。狂野的笔触破坏一切。诗歌则沿着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派,发展到超现实主义。伊凡·哥尔有表现主义画家朋友,在巴黎又加入超现实主义群,应该说,和阿拉贡、艾吕雅是一伙的,和他们齐名,国内除了董继平先生的译本,介绍得比较少,其实,哥尔的诗作是独树一格的。
超现实主义是诗歌的一场革命。是决裂传统、破坏既成秩序的“愤青”所为。哥尔后来和布勒东闹翻,自行发表另一份宣言。究竟其间的差异在哪里?无非是些非原则性的感情用事。哥尔晚期的诗作便是按自己的宣言,更超现实主义化了。和画家达达派、立体派、未来派均有不同的视角,超现实主义诗歌往往突破邻近的转喻和隐喻,不相关的事物置于同一时空,切断联想链,造成荒诞的效果,以喻现实世界的荒诞。随便择取哥尔的一句诗,如:“狄安娜的雉鸡和海蛇的黑色碟子的蓝色碟子/或者蛤蟆的金色之弧”让人费解。又如:“我购买我吃掉黎明那紫色的肉体”,稍稍可以解读,黎明为紫霞笼罩,拟人化如横陈的肉体,但为什么要购买而吃掉,因为诗的开头是购买这个购买那个,商品化什么都购买,包括购买紫色的黎明和我自己。这里选的两章略不同于晚期的作品,具有我们散文诗铭句小诗的特点,前面《在记忆之井边》,记忆如井暗示着它的深,须挖掘和打捞,我只在井边浇灌你的影子之花。如果勾勒成图画,便是井边的阴影草丛中黯淡的花,深井中只有水没有花的影子,那花,吐露着尘世所无的别一世界的浓香,使我醉死。下一章《神庙一片白色》,黑白对比强烈,神庙边的水塘,碧水也使用黑以衬神祗的白;我周身流动的血液也变成黑的了。运用扭曲的艺术技巧使对象陌生,使理解变得困难,正如什克罗夫斯基说的,读诗的过程就是审美的过程,“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
我们创作散文诗的语言是第一位的,必须强化日常语言,有时凝聚,有时故意扭曲对象,有时向式缩短,有时伸长。使日常语言“陌生化”,更新我们的审美准则,以此达到散文诗的创新。这就是读伊凡·哥尔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