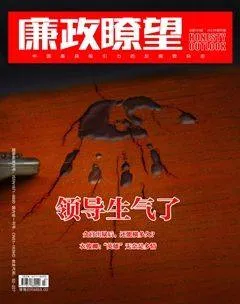富兰克林的“权衡”智慧
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说,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数字把大屠杀给抽象掉了。
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我们不再记得住:大屠杀不是六百万,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我们对悲剧如何感知?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
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它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空洞、模糊、抽象的概念,而最终,也往往是用数学来终结对灾难的生理记忆。
有次饭桌上,在座一个记者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他很兴奋,“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数字之冷漠!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当剧情达不到高潮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
然而,当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2005年1月23日,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近700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
2012年4月6日,11541张红色椅子在萨拉热窝街头排开,仿佛一条鲜血河流,以纪念波黑战争爆发20周年,每张空椅子代表一位死难者。
2010年4月,奥巴马参加西弗吉尼亚州矿难悼念仪式,一一念出29名矿工的名字,他说:“尽管我们哀悼这29条逝去的生命,我们同样也要纪念这29条曾活在世间的生命……我们怎能让他们失望,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因工作就付出生命,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在寻找美国梦吗?”
2012年7月26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音员用沉痛而缓慢的语调、逐一宣读北京暴雨灾害中已确认的遇难者名单,61个名字,耗时1分35秒。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微博发表《向北京“7 ·21”特大自然灾害中已确认遇难人员致哀》。
这些事件的伟大在于,他们不再抽象,不再是一个数字,他们有了人间的地址,有了姓名、身份和面孔……这是生命应有的待遇,这是悲剧应有的尊严。只有这样,生死才得以相认,我们才能从悲剧中领到真正的遗嘱,才能在别人的命运里找到共同体的痛,只有这样,悲剧才会把它的正能量传递给生,并转化为活着的勇气、路标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