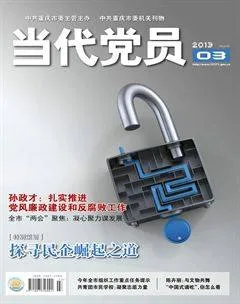民企抱团难在哪
1932年6月29日,德国萨克森州开姆尼斯。
四家汽车企业齐聚于此,缔约结盟。
此后,这个以“四环”为标志的汽车联盟横扫欧美,崛起成为与奔驰、宝马鼎立称雄的业界巨头。
这次抱团,缔造了“奥迪神话”。
IBM、美孚、百胜……在工业文明史里,众多超级企业的崛起,都曾以抱团为阶梯。
然而,在过去十多年里,重庆民企在这条阶梯上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却频频遭遇败绩。
起事难
2012年初,忠县东溪镇。
这天风大。金龙船业公司大门前,沙尘在风中飞旋。
“金融危机爆发后,订单直线下降。”金龙船业老板黄安钿苦笑,“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接到过订单。”
于是金龙船业被迫停产。
这是重庆民营造船企业的缩影——2012年,订单整体下降41%。
转型升级,方有生机。但转型何其难。
“重庆100多家造船企业中,上规模的不到30家。由于规模小、档次低,船企无法独力完成转型。”市船舶修造协会会长何喜云说。
为此,何喜云支招:“抱团发展,能推动技术和管理的全面升级。”
市经信委军工综合处也支招:可以考虑抱团取暖——共同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船企提供融资担保。
招是好招,但实现很难。
“中小型船厂抱团,在金融担保等方面必须有大企业保底。”一位业内人士说。
可是,没有哪家大企业愿意挺身而出。
“没大企业出面,想抱团也抱不起来。”中小船企老板一脸郁闷。
而在数千公里外,浙江台州同行已开始突围——在造船业商会协调下,万隆船厂等“领头羊”挺身而出,与90多家民营船企抱团结盟,在技术改造、资金运转、订单分配等方面互帮互助,成功突破困境。
没“组织”出面协调,大企业不愿挺身而出——这是重庆造船业的尴尬。
“一批民营船企将死在这种尴尬中。”有人预言说。
而小船企的大量死亡,必然会重创从零配件到组装的整个产业链。大企业也将被“殃及池鱼”。
这便是渝商抱团的第一难——没“组织”协调,“领头羊”难寻,所以起事难。
合作难
李瑞已在重庆生活多年。
他老家在云南省文山州,从那越过天保口岸,就是越南河宣省。
2000年,李瑞回老家探亲,顺路到越南一游。
河宣省首府河边市,摩托车往来穿梭。
滚滚车流中,李瑞见到不少“熟面孔”:“力帆,隆鑫……”他数着,兴奋起来,“十辆摩托车,有七八辆‘重庆造’!”
李瑞越南游一年前,在力帆、隆鑫等业界巨头领导下,重庆摩帮结成“价格同盟”,仅用一年时间就击败日本同行,占领了90%的越南市场。
2006年,李瑞故地重游。
河边市,摩托车依然往来穿梭。只是,车流中已难寻“重庆造”身影。
2003年,越南进口关税骤增。为抵消激增成本,宗申集团倡议同行同进同退——涨价。却不想,此举未得到同行呼应,反引得中小企业趁虚而入,蚕食宗申市场份额。
价格大战于是爆发。越战越烈后,于是次品频出。
次品频出的结果是车祸频出,重庆摩帮由此信誉大跌——日本摩托借机收复失地。
这样的合作尴尬在重庆屡见不鲜。
这种困境凸显出渝商抱团的第二难——合作机制难建立。
“缺少合作机制,就无法拧成绳。”李瑞说。
浙江能崛起这么多民企群落,靠的就是商会、协会、联盟等行业组织穿线搭桥,建立了抱团合作机制。反观重庆,这样的机制十分缺乏。
重组难
“团体分工越细,创造财富的效率越高。”亚当·斯密曾这样论述分工的意义。
对抱团企业而言,就是需要形成多层次的生产经营体系。
2012年7月,沙坪坝区回龙坝镇。
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内,由于只有一半工人在岗,偌大厂房显得有些冷清。
在回龙坝,数百家纺织企业大多是此等光景。
由于以作坊式小企业为主,多年前,回龙坝纺织企业就组建了纺织协会,希望抱团做大。
却不料,反而因此共陷泥潭:60%的会员企业都在生产低端产品——白胚布。
金融危机爆发后,回龙坝纺织企业陷入极度严寒——白胚布全面滞销。
就在各企业束手无策之际,当地政府伸出援手——通过规划纺织产业园,引导纺织企业进行分工,分别进军高、中、低端产品。
这年底,纺织企业因此渐渐复苏。
回龙坝纺织企业很幸运,因政府出面引导重组分工而走出困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出面引导重组分工绝不应成为主流。“这得靠协会、商会、联盟等行业组织,江浙民企群落的分工就是如此。”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谢祖墀说。
“如果抱团企业不能实现重组分工,就无法形成坚不可摧的产业链。”谢祖墀说。
不少渝商抱团,先抱后散,正是因为遇到了第三难——商会、协会等行业组织,没能发挥重组分工的引导作用。
协调难
2005年10月,重庆医药行业协会办公室冷清下来。
上个月,其会长递交了辞职信,和他同时辞职的,还有秘书长。
“谁也不愿当这个会长,因为没一点经费,怎么运作?”市药监局工作人员说。
此时,市蔬菜协会会长汪有良同样郁闷。
“以前靠市农业局拨款,现在拨款没了,怎么运作?”汪有良说。
2005年,重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颁发了两份文件——《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的实施方案》。于是,5000余家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与党政机关脱离开来。
在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成了主管部门的钱袋子,不给钱不办事,故被民众称为“二政府”。因此,进行脱钩改革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拿掉别人的拐杖,却没教会人家走路。”汪有良说。
“脱钩后,一些政府部门害怕协会、商会与其争利,又不舍得放权。于是,行业协会、商会成了‘无用’的代名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唐尧说。
一大批行业协会、商会只好被迫“关门”或“无为”。
“行业协会、商会,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在帮助民企做大做强上,可发挥四大作用。”市工商局中介监督管理处原处长胡轶说。
在完善生产上,协会、商会可建立生产性服务平台,解决成员企业技术升级、经费短缺等问题。
在完善流通上,商会、协会可建设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参与专业市场升级改造,建设流通性服务平台,降低成员企业商品流通成本。
在对外交流上,商会、协会可以帮助成员企业进行宣传推广,打造品牌。
在维护权益上——如今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商会、协会可以帮助企业在摩擦中争取最大利益。
但是很遗憾,在这四方面,重庆的行业协会、商会、联盟都缺了位。
“几年前,我们提出一种思路:就是将产业集群发展的理论,运用到行业协会、商会的培育中——打造一个园区,作为行业协会孕育发展的家园。”胡轶说。
按这个规划,整个园区分成办公区域、会展区域和商业区域三大块。在办公区域,让各行业协会、商会集中办公,解决其脱钩之后驻所分散、工作开展不便的问题;还可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行业协会以购置或租赁方式入驻其中。
“把行业协会集中起来,不仅可以增强协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还可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络放大,达到更好的效果。”胡轶说。
但这个规划,因各种原因而中途夭折。
2012年,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我的资金链要断了。”机械配件生产商李德辉急得直搓手。
无奈之下,李德辉想到一个办法:在行业内寻找一个可提供金融担保的联盟,实现担保融资。
“这种联盟在东部很流行。”李德辉说。
多方打听后,李德辉绝望了——重庆没有这种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