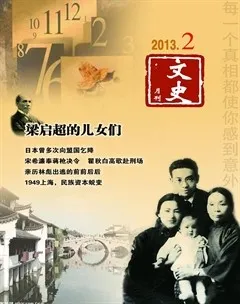相同的事件,不同的眼睛

在近代中国,教士藉以政治特权,凌驾于地方之上,有的教民常常仗势行凶,而当地民众则通过加入地方会党的方式,来寻求保护,并藉此与教会抗衡。民教龃龉,积怨颇深。至晚清时期,浙江地区会党遍布,成为影响地方统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会党的号召下,民众纷纷加入会党,与教会势力进行抗衡。
1902年,浙江西北部发生了桐庐教案。
桐庐教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汪林茂在《浙江通史·清代卷》中说:“庚子后7年间,反教会斗争是各地民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2-1903年濮振声领导的白布会反教斗争。”
著有《浙案纪略濮振声传》的陶成章认为,白布会反教斗争名为反教,实为反清,后来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记述也多如此。但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眼睛,近来通过新资料的发掘与解读,特别是新的史学方法的引入,笔者拟对这一历史事件重新解读。
一、桐庐教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关于教案发生的原因,有这样几种记述:
陶成章认为是濮振声以仇教为名进行的抗清起义;
“官方”认为,起源是附近金华县的民间会党成员郑锡斋散卖票布,郑锡斋被拿获后,谎说他是濮振声的同党,而桐庐县的仇教者以此为借口,带有强迫性地拉拢濮振声,导致濮振声参加了此次仇教运动;
桐庐知县刘肇甲认为,教案本不该发生,是因为抚宪得到天主教司铎的电报后派兵,激发了民变,才形成了数万人聚集,与之对抗的情景;
1902年12月《申报》描述:“向有天主教中人在彼建(教)堂传教,偶值教民龃龉,县主不善判断,以致士人积愤难平,迩者粮价(出)奇昂(贵),民难果腹,匪徒遂述言布散(谣言),指为外人贩米出洋,愚民信以为真,于是句进两邑匪徒私立社会名曰‘地主’,专与天主教为难,放火焚烧房屋,而(对于)耶稣教中人(却)并不伤害,以示(与天主教徒)区别(对待)。”
由上可知,天主教在桐庐当地与绅民之间矛盾重重已是既定的事实,教民龃龉加上外人散播谣言成为导火索,最终导致教案发生。
桐庐教案的领导者濮振声,是六县客民(编者注:客民,既可指客家先民、客家初民,也可指现在客家人)总董事,又是白布会的首领,在地方素有威望。当地民教互相猜忌,积怨已久,官府袒教抑民,百姓情绪压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晚,风雨交作,濮振声率领会党突袭了位于枫埠的精胜军左旗营垒,然后乘势攻破了横村清军守备营,后又击败吴忠选的援军,并攻占了分水、桐庐县城。
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啸聚至万人之多”,绅耆描述为“职等探听情形,见旗帜林立,枪炮雷鸣,不可终日”。
其间,聚集的会党队伍将“桐庐、分水、建德各乡教堂纵火焚毁十余所,执获教民数名,惨将戮害”。至于传教士,则在会党进攻教堂之前,桐庐县令刘肇甲已经将“教士护送至省”。
十九日,省城派统领黄书霖至桐庐县,随即对濮振声进行围攻。二十一日交战中,濮振声领导的会党队伍受到重创,在退守百岁坊时,被清军围住。
濮振声见势已去,于十二月八日只身赴清营费金组处自首。后被押解到省,判处永远监禁于仁和县,1907年病殁杭州狱中。
桐庐教案以清政府的顺利剿办而告一段落,濮振声被永久监禁,其子濮贤厚被清政府判处死刑,从犯王寿元、麻兆兰原本被刘肇甲判处就地正法,后解省确供后,改为暂时监禁一年,再视调查结果和有无乡民控告而定罪。
桐庐县县令刘肇甲因“办事轻率,几陷无辜”,被革职回家,闭门思过;对教堂的破坏,“仅恤教堂洋银三千余元即得和平了结”,天主教传教士得以“重返桐庐,照常传教”。
经过此次教案之后,白布会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陶成章、魏兰所重视,他们到狱中看望濮振声,并得其名片数张,为联络会党提供便利。他们认为桐庐教案实为反清。
国民革命政府时期,追溯濮振声为“革命先驱”。
笔者通过对新资料的读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柯文书中所描述的直接经历者、神话制造者、历史学家重塑历史有着不同程度的默契,遂利用这一史学分析方法,重述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二、直接经历者这样说
桐庐县令刘肇甲是目前可见唯一留下文字资料的经历者,他曾在教案发生前“单骑亲赴分水石清塘濮振声家,反复开导,喻以利害”,而在当时的桐庐县境内,已是“数百里内风闻响应,匪党不下万人,其时风鹤皆惊,省城亦为震动,匿名揭帖遍列通、衢,约期十六日寅刻入城焚毁教堂,戕杀教士,绅民避祸迁徙一空”。
作为一名早期亲自处理此次事件的参与者来讲,他掌握事件的直接信息,通过上面的引述,则不难分辨当时情势紧迫,而事件的起因则是“教民报营会,拿票匪郑锡斋一名,指为分水贡生濮振声党羽,濮遂借团防为名,拥众自卫”,刘肇甲调节后,民众虽“至十月初众渐解散”,但此时适值“天主教司铎魏殿培初八日到桐,教民纷纷奔诉,谓濮聚众与教为难”,而当时的抚宪“以为事在危急,不及委员查察,连夜委参将吴忠选带兵两哨,于十二日抵桐”。因为参将吴忠选邀功,“日以杀濮为词,濮党中亡命之徒,又不肯遽散,且以危词耸濮之听”,遂导致“匪党乘风雨交作,遽至枫埠劫营,军装尽失,更乘势至横村埠与防勇开仗”。
作为桐庐教案的经历者,他的这番记述为我们后来者留下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画面。他一直在强调民教之间有冲突,甚至“民间之报抢案者日必数起”和“穷治起意劫狱烧堂,以图一逞”,与后人对桐庐教案的界定发生了冲突。
在他看来,这就是一起地方仇教,且可以通过调节避免冲突的民教冲突案件,但因官员的操作失当,引发了一场军民冲突。而他却被认为办事轻率,几陷无辜,被奏参革职。
晚清教案的处理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清政府多通过撤员的方式,一则向西方表示处理的态度,二则惩戒地方官员要慎重对待此事。作为事件的经历者,刘肇甲被撤职,也正是因为刘肇甲撤职后为自己鸣冤,才有幸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描述。
三、神话制造者从历史中汲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
教案的领导者濮振声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追认他为‘革命先驱’”,陶成章在书中形容濮振声是一位家资殷厚、颇有声望、善医卜星象、仗义疏财的白布会的领袖,并指出其创办的宁清团‘言欲以绥靖清室,盖为掩饰耳目计,其实意则反清’”,并认为名为仇教实为反清。这也正是濮振声被称作“革命先驱”的最直接证据。
但是从事件经历者的记述和处理结果来看,并非如陶成章所言。陶成章在书中提到濮振声在起义之前曾申明不准“教民亦不得无故杀害,仅取其家中粮食充军需以示薄惩”,而麻兆兰、梅发奎、王寿元是在教民家中抢劫财物后被抓,此时民教之间已经有所冲突,教民和教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教民将此情报告知司铎魏殿培后,魏殿培向省里请兵,地方政府“将教士护送至省”,事后“仅恤教堂洋银三千余元即得和平了结”。
综上可知,桐庐教案的发生起于民教龃龉,但此次地方政府处理较为及时,遂至破坏程度不大。这也反映了庚子事件以后,闽浙总督许应骙在庚子事件时是一位主张遏制义和团势力的政策的支持者。
桐庐教案在当地至今广为流传,濮振声被视为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典型,桐庐民间学者何铸老人根据口口相传,回忆说“起义聚众了2500多人,在高翔的殿山庙里开誓师大会,随后烧毁了高乡村的这个天主教堂,并击毙了宰杀牛的野蛮教徒”。口述史料有其特殊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弊端,讲述人可能会因为记忆的问题或者自身的因素,使讲述的过程成为制造神话的过程。
《申报》在报道此事时称“票匪游兵,乘机窃发杀人越货”和“土匪滋事”,并将“教堂纵火焚毁十余所,执获教民数名,惨将戮害”。而清政府同样是将此教案定义为“匪徒煽惑滋事”。虽然《申报》由外国人创立,但在1905年以前仍然是倾向于支持清政府,论述者也同样是在制造了叛乱神话。
制造神话会偏离历史本来面目,而“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
陶成章为了彰显会党在浙江起义复兴中的作用,将濮振声领导的桐庐教案归结为抗清排满起义,而桐庐地方则把濮振声神话为抵抗地方天主教势力在地方作恶的一个典型事例,《申报》则将其视为匪徒,是地方安靖的不安定因素。
四、历史学家的作用和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但他们在重塑历史的同时,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神话
面对以上问题,历史学家需要适时地站出来了。
历史学家的作用和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但每位历史学家叙事化的处理又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瘠富程度,以不同的角度和层次重新塑造了历史,当然也可能会受时代和个人喜好的影响。
目前的历史著作中,对濮振声领导的桐庐教案的描述,多是来自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里关于濮振声的描述,也沿袭了陶成章的说法,将此次民教冲突定义为假仇教为名的反清运动。
作为研究晚清教案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多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以倒叙的手法重塑历史,而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同时,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创造了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