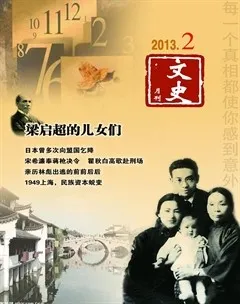使用语言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言意之辨本为中国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将“得意忘言”论自觉地引入文学理论,这种被汤用彤称为奥卡姆剃刀的方法论一进入文学领域,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得意忘言”论与“言不尽意”论,相应地形成了两种文学创作态度。
正如李泽厚在《美学三书》里所说:“这个哲学中的唯心论命题,在文学的审美规律的把握上,却具有正确和深刻的内涵。”
一、善于使用语言,找到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我们无限丰富的意识内容,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言意之辨涉及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而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人类的思维大体可分为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相对于人类的思维形式,我们的日常语言发展出了形象语言和科学语言。但是,语言在表达人类的思维活动时仍然是不称职的工具。
人类的感性活动是无比丰富、细腻、鲜活与生动的,而语言总是带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不可能将人类的感性活动充分体现出来。而于理性思维,科学语言也有它的局限性。数理逻辑方面的许多高度抽象的理论,往往只能用符号公式来表达,而很难用语言做出确切的表述。
言意之辨所提出的“言不尽意”揭示了这一客观存在。
但是,我们又不能离开语言来进行思维,于是,善于使用语言,找到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我们无限丰富的意识内容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
二、“药,酒,姿容,神韵,还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辞章,才构成魏晋风度”
针对“言不尽意”,历史上自然地产生了两种文学创作态度。
一种是挖掘语言潜能,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就是要把我们的审美想象、情感意识外化为语言文字,所以作家们总是致力于炼字磨句,追求语言的充分达意,务求能将审美意象通过语言文字纤毫毕现地呈现出来。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作家们劳心苦思“罄澄心以凝思(排除杂念专心思考),眇众虑而为言(整理思绪诉诸语言)。笼天地于形内(将天地概括为形象),挫万物于笔端(把万物融会于笔端)”,锤炼字句“选义按部(完成构思,布局谋篇),考辞就班(选词精当,事理井然)。抱景者咸叩(有形之物尽绘其形),怀响者毕弹(含声之物尽现其音)”,务求增强语言的达意功能。
这种对语言的强调与重视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即是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而且是前所未有。“诗缘情而绮靡(诗歌本是因情而发,语言理当华丽艳美)”即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创作风尚。颜延之的“错彩镂金”式的创作风格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即使是为时人誉为如“芙蓉出水”的谢诗,在后人看来也是颇事雕琢的。曹植在当时受到特别的推崇,钟嵘曾将他比作“譬人伦之有周孔”,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他讲究诗的选词炼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等等),精心炼字(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等等),对句工整(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等等),结语深远(如“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等等)……无疑表明他已经不同于前人顺乎自然式的去作诗了,而是有意识地去作诗。而曹丕尽管有《燕歌行》为王船山誉作“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但是如同汉魏古诗一样,似乎出自天性而少修饰,远不如曹植诗的炼字琢句,“词采华茂”。因此,钟嵘把曹丕放在了中品。李泽厚说:“那是一个‘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代,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可见,药,酒,姿容,神韵,还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辞章,才构成魏晋风度。”
三、“言有尽而意无穷”
而针对“言不尽意”的另一种文学创作态度则是:认识到语言在表达意念时的局限性,巧妙地利用“言不尽意”带来的积极审美效果,不是去雕刻修饰语言,而是锻炼语言的韧性,拓展语言的生成空间,尽量用有限的语言去表达无穷的意念,增加“言外之意”的信息量,造成含蓄的创作风格,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人们对“言意之辨”的普遍关注,文学理论家对“言不尽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陆机在《文赋》中言:“恒患意不称物(作者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意念有时不能准确反映事物),文不逮意(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盖非知之难(大概这个问题,不是难以认识),能之难也(而是难以解决)。”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因此,他们也开始更加自觉地去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而刘勰在对“言意之辨”有了深刻的体味之后,也追求言浅而意深,言有限而意无穷,神思可与天地自然相接的审美境界,主张创作者用隐约的言词来包含“文外之重旨”,欣赏者则需调动自己的想象,进入那更为广阔、更富意蕴的“言外之意”的审美享受空间。
同样追求含蓄蕴藉表达效果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认为,五言诗优于四言诗,原因则在于四言诗“文繁而意少”,而五言诗“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他将滋味说引入文学理论,对诗之三义也进行了重新排序,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兴”置于首位,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极力提倡富有深意,品味不尽的诗风。
这样一种文学创作态度,表现在作品上,即是一大批富有玄远意味的诗歌的产生。他们多以玄入诗,追求语言之外的天道之意。如:郭静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孙绰《兰亭诗》第二首:“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云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前四句写景,春风煦煦,停云蔼蔼,莺鸣鱼戏,竹修水澄,表现了自然和谐的意趣,后四句转入抒写玄思,是诗之重心,重在言理,末两句尤集中地体现了全诗的写作意图,用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之典故,点出由风光物态感悟出微言至理。
陶渊明的诗将景、情融为一体,从中生发玄远之意,因此更具代表性。他在饮酒诗里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短短的一首诗里,却蕴含着道不尽的意味,给后人以无尽的玄理与哲思。
以玄入诗,期待以有限的语言容纳无限之玄理,但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玄理太重、形象性不足的弊病,钟嵘就曾批评两晋时期的玄言诗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为后来表达更为含蓄的诗歌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因此,我们不能否定其历史地位,而应给予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