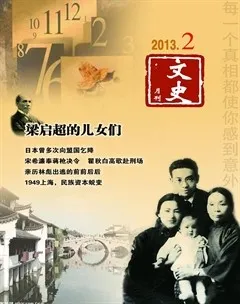我在大同县搞“四清”


我是1964年的秋天考入省委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省委党校有别于普通大学,是以党支部为建制的。我是在64级“培1支”。
1965年秋,我们支部的学员,每两个人领了一套从部队退下来的棉军装,这是省委给到高寒地区搞“四清”的同志们专门调拨的。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在那里摆着,因此,不管是拿上衣还是拿裤子,每一件旧军装要付两块钱。
我们坐火车来到雁门关外的大同市,负责大同县周士庄公社的“四清”工作。周士庄是京包铁路上大同县境内的一个大村,是人民公社所在地。
我们这支队伍,最大的领导是两个十级干部,一个是山西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一个是山西省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赵培心。和我们同在一个工作团的有省晋剧院的演员冀萍、王爱爱、田桂兰等名人,还有省卫生系统的干部、朔县的农村干部、大同工校的师生。
经过卧虎湾二十一军营房一个月的集训之后,我跟着工作队队长刘觉生老师,以队部资料员的身份,开进了王千户庄。同在一个工作队的有省委党校学员、大同柴油机厂的石英怀同志,他任工作队指导员;省委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王玉龙;大同工校的两个女生李改凤和薛改琴,还有朔县借调来的两名农村干部,朔县农机局干部胡昌,二十一军的谢九柱指导员和闻喜籍的支成森排长。
王千户庄,名不副实,只不过300多口人,耕地都挂在一面坡上,多数土地与农民是“一年两见面”。春天种上是“一见面”,秋天收割是“一见面”,打多打少听天由命。农民只要有高粱黏糕吃就满足了。花钱靠的是种黄花菜(即金针)或养殖。
要在这样的村子里揭露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很费劲的。一阵扎根串连之后,我们工作队不仅没有弄住“麻袋”(指粮食),而且也没有清出“票票”,急得刘队长坐卧不安。我们参加公社“三干会”的队员们通宵达旦地给“四不清”干部加压,会开了一天一夜,还是不见多少成果。几个在村里留守的队员,围住一个姓杨的上门女婿。杨氏开始还能沉住气,可是队员们一再加压,杨氏经不起“人歇马不歇”的连续作战,防线被突破了。起初说他偷粮食是用口袋扛,后来又改成平车拉,最后干脆交代是赶着牲口皮车运。工作队员以为打了一个大胜仗,核算了一下,足足够个“万字号”了,喜形于色地到“三干会”上汇报。队长一听,说:“坏了,赶快回去,此人要出事了。”年轻人们回去一问,昨天晚上杨氏交代完问题就根本没有回家,一口气跑到京包铁路线上,冲着飞驰的4次国际列车血洒钢轨了。
我在王千户庄工作队当了一段资料员,刘队长见我工作细致,让我也带了一班人查冯吉老会计的账。岂知,想从结结巴巴的冯会计那儿打开缺口谈何容易?一个一年纯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小山庄能有多少油水供干部捞呢?我们几个查账的,只是从账物核对中找到了两副皮车轮带的问题,不足700块钱,还是三个人分赃的。
在王千户庄搞“四清”,生活十分艰苦,农村寒苦人家出身的我,也实在忍受不了。这里的红黏糕是带皮的,人们把高粱连皮在碾子上碾成面,不去皮,用水拌起,蒸出来,揉成面团,就点菜或在酱油里泡一泡便下肚。外地人吃了这种糕,大便不下来,动不动就便血,人半月二十天就变样了。我当时每月领着国家的36元工资,除了往家里捎十几元,吃派饭贴了伙食,仍然有些剩余,当时我没有别的花销,于是就买饼干吃。实际上,饼干并不便宜,王千户庄供销点的农商们眼巴巴地瞅着我们的这几个钱,一角钱卖给七块饼干。我们开完会,饿了,互相照应一声吃“掐疙瘩”去,彼此心领神会,直奔供销点,一角钱的饼干,走不下供销社的台阶就吃光了。
我在王千户庄搞专案,做过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那就是给张保国复议阶级成分。张保国家土改时,定的成分是上中农,工作队为了政治成果,听从了一些人的反映,想把他家的成分划上去,按富农定。调查、取证结束之后,由我们三个人与张保国老汉接触,让他签字同意。我接到任务后,很是为难。是工作队别的同志给我出了个“好”主意。他吩咐:“你和他谈话,不可能一谈就成,起码得一个黑夜。要熬他,你们可以轮流休息,他不能。谈到成分,要出价高一些,想划他富农,就说要划成地主,最后是让他从地主、富农两个里边选一个,他选得再低,咱们也都够本了。”
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后,传唤张保国到场。老汉虽是庄稼人,但很有头脑。我把工作队的意见,照前面吩咐的如此这般地说了出来,他始终不吭气,只是用那大烟锅,一袋一袋地抽。已经到了次日凌晨一时许,我又追问:“张保国,你看怎么办吧?”他似乎专看工作队的态度和耐力,祈求到:“现在的成分不行吗?”几个工作队员见他说话了,又是一轮苦口婆心地开导,他却重操旧业,把已经堆起来的烟蛋蛋垒得更大更高。
还是事先的预见起了作用,工作队“对敌斗争”的成熟又一次在我们和张保国的较量中得到了验证。黎明时,张保国主动表白:“我现在的成分不行,但我不当地主,我当富农吧。”我们再三叮嘱他真是想通了时,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句话“同意把我家的成分划为富农”,让老汉笨拙的手一笔一划临摹,写到了一页生死攸关的卷宗纸上,并盖上了指印。
那一年,“四清”结束,我们回到太原不久,大同县派人到省委党校调查张保国的成分复议改划的情况,领导让我答复。我痛痛快快地给来人写下这样的几句话:王千户庄张保国的成分由上中农改划富农,完全是“左”倾思想的产物,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很是卑劣,伤害了人,应该道歉,纠正过来刻不容缓。
1966年的春节,我在王千户庄留守,搞了不少调查,调查报告写得非常精细。不知是谁推荐,我于1966年春节之后就被调到大同县“四清”专案组,在怀仁县刑警队长郭河大哥手下搞保卫工作。由于调动便恋恋不舍地将调查报告交给了工作队,至今心里直后悔,如果那些材料在,肯定有许多令今天看来值得珍惜的资料呢!
“四清”保卫组人少事多,属专案组领导,专案组成员是几个高智商的人,有太原重机学院的一位同志,有广灵县的检察长,有灵丘县的副检察长。保卫组组长郭河和我住一个家,经常指导我们几个人掌握做好保卫工作的要领。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大同县这一带有许多逃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刚解放时就到了内蒙古,成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赤贫,入了党,当了干部。“四清”清理出来后,大同县的基层去抓,保卫组的人便带上枪支、手铐跟着一起去了。有一次,我们三人就从内蒙古带回六个逃亡的“地、富”,把他们铐在火车的座位上。我们心里都很发怵,生怕他们逃跑或伤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况且胆子又小。一次,一个罪大恶极、有命案的在押犯要求上厕所,我们跟上他,他进了厕所,我们就站在车厢的厕所门口。他进去后反锁上门,把窗户上的钢筋棍弄掉,把玻璃打碎,从窗户上跳了下去。我从另一个窗口看到他,心里害怕极了,赶快报告车警,车警拉警报,火车停了下来,车警下去才把摔在路边的在押犯逮了回来。
保卫组的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就更忙了。“造反”造出来的东西,谁也不敢存放,都往保卫组送。送过来的有金银元宝,有各种各样的衣服,97a432696d6ac28e7fd1902d29e356e4有带着珍稀图案的摆设,有打卦、算命的神龛,也有成套的古籍。
我不喜欢穿戴,家里从小就没有条件培养我讲究衣着。长大了以后,我总认为人有没有本事不在外表。我也不喜欢金钱,尽管当时已经是当上父亲,负担家口的人。在王千户庄工作队时,吃块饼干还没钱,工校学生、榆次籍的李改凤经常买来点心,让我和刘老师吃。当时,我也不抽烟。在保卫组收到的“造反”物件中,郭河大哥让我拿点玩具——非常高级的麻将牌,我摇头。让我心里痒痒的是那一套一套的古装书。但我一看到这些书,就迅速地把头扭过去,咬着牙关把书装进麻袋里搬入仓库,一本都没有拿。郭河大哥给我留了一套《红楼梦》,我也坚持不要。那时候,如果拿上几本书,即使是拿上几个元宝,也不会有人追究。因为运动初期,谁还敢承认家里藏着这些“封、资、修”的玩意儿呢?而每当有机会占点便宜时,父亲的话就响在耳边:“人家的东西,咱千万不要拿,因小失大的事做不得!”
结束大同“四清”返校回太原的时候,我把铺盖和衣服摆在床子上,一件一件让组里的领导和同志们看过,这才捆绑起来,走到汽车站,乘上那开往大同火车站的公交车。
如今,距离大同县搞“四清”已有快半个世纪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是很能教育人的。我们这一代步入古稀之年的参与者,当年,学习、领会了许多;今天,也回顾、总结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