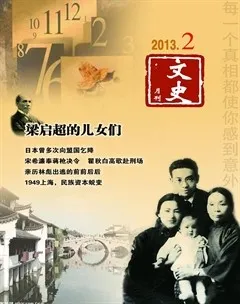中原猪市——河南乡间猪市上的牲畜经纪人








中国自古就有“粮猪安天下”之说,猪是农家的“六畜”之首。
在河南乡间的猪娃市场上,买卖双方都相信一条古训:“中间无人事不成。”于是就有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猪经纪”。这些老说家们在买方与卖方间居中说合,促成交易。古时,他们被称作“牙人”,所提的佣金称作“牙钱”,古代典籍中描述他们“南北物价定于其口,而后相与贸易”。
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
在河南农村,凡是稍大一些的村镇都有各种各样的集市和庙会。这些集会因庙而起,因地而兴,而今,庙不多了,会却比先前多了起来。每隔十里八里,只要有村镇便有会,以农历固定日,有逢九的,逢三的,逢六逢五的,月月如此,风雨无阻。每一个集会,都是一次乡间博览会,各种物什儿皆有相对固定的交易场所,猪、马、牛、羊等牲口交易也如此。中原地区的猪娃市场通常是乡镇集会的一部分,不过又相对独立,或在路边空地,或在村中街巷,交易时间也不长,俗称“露水集”,日出而市,日中即散。
集会上,有一个群体很活跃,那就是牲畜市场上的经纪人。他们都是本地农民,通常为中老年男性,但我也见过一位泼辣能干的女经纪。当地人他们称为“行户”或“经纪”,现在的官称是“交易员”。集会上,无论是买卖大牲口,如牛、马、驴、骡等,还是小家畜,如猪、羊等,都需要“行户”居中说合。他们因分工不同,有“牛经纪”、“猪经纪”之别。这些人是村民中的能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在买主与卖主之间说合,讨价还价,促成交易。他们通常还具有牲畜饲养方面的知识,庄户人家买卖牲畜也离不开他们的指点帮助。
牲畜经纪人是一种古老行业
1993年以来,我跑遍了平顶山方圆几十里各个乡镇的猪娃市场,有些地方去了不止十次八次。去得勤了,就与很多行户熟识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我去,大老远他们就喊:“来……了!”我答:“来……了!”然后各忙各的事儿,他们忙着交易,我拍我的片子。
中原腹地的河南,自古是养猪大省,民国18年(1929年)编撰的《河南新志》里有这样的记载:饲养之风以许昌、信阳为最盛。大河沿岸,乡民有恒产者家皆饲猪,而城市饲者则少。唯许昌、信阳则盛于城市。信阳居民有一家养猪数头,若他处乡民之养鸡。
平顶山所属的宝丰、叶县、鲁山、襄城、临汝数县,旧时就隶属于饲猪之风最盛的许昌之地。养猪成本低,农家以清汤寡水或野草瓜秧就喂得一头母猪,若下了猪崽儿,就有乡亲们“估堆儿”抱去喂养。乡民们总说:“家里不养一头猪,剩汤寡水的没法儿弄。”养一头猪,就等于存了一笔钱。猪长成了,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宰杀既实用又排场。一头母猪一年能下一两窝猪娃儿,养上一两个月长至二三十斤,就可上市了。一窝猪娃儿能卖千八百元,这对农家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在中原的乡间,买卖双方都相信一条古训:“中间无人事不成。”每个集会的行情变化很大,买卖双方都心中无数。猪娃儿买卖通常先由卖方出价,说高了,怕吓跑了买主;说低了,又怕辛辛苦苦养育的猪娃儿贱卖了,所以出价时总是虚虚地往高处要;买家儿也一样,不愿轻易透出自己的底牌,还价时通常是狠狠地往下砍,二者很难顺顺当当地完成交易。
这就给行户提供了用武之地。行户通常是一大早赶在买卖者上市之前就上会了,夏秋季节天不亮就要到场。所以从第一铺交易完成,当天整个集会的行情也就基本定下了,而后陆续来的买卖者到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行户打听行情。另有一层原因是很多乡民不善言谈,不会讨价还价,于是就把事情托付给自己熟识的行户。
若是遇到外地来看“猪娃儿客(kai)”,本地的卖家通常会抬高些物价,买家为了能平价收进,也需要行户居中说合。“客”是河南人对外人的称谓,在猪娃儿市上,人们把外地来的猪娃儿贩子叫“客”。“客”都是大买主,一次通常买上百头,然后运往异地出售。
这是一种古老的行业,古时称他们为牙郎、牙侩、牙人或牙子等,就是集市贸易中以介绍买卖为业的人。《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里都有这个行业的记载。明代有官牙、私牙之别。官牙由政府指定,私牙也须由政府批准并取得印信文簿后始得营业。牙商须领牙帖,按期缴纳牙税,并负有代官府征税责任。
这些人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太平广记》里就说他们:“性甚狡慧,词喙辩给。”他们中的一些人除了会有意哄抬或压低价格之外,有的人还会秤上做些手脚。一个老行户告诉我,以前的行户有秤杆里灌水银的,开秤时只要暗暗地控制着水银的位置就行了。
行户通常是骑着自行车上市,携一杆秤、一根棍棒,棍已摩娑得光亮,用来抬秤。再就是一张利嘴,乡民常称之为“臭嘴粘牙”,说合事儿的时候嬉笑怒骂,唾沫星子乱飞。所以他们虽然是“能人”,赚的也是辛苦钱,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以前称“行户”或“经纪”时,都有一定的贬义。
与世纪同龄的经纪人——刘群成
几年不来,我与猪市上的这些“老说家儿”们成了朋友,尤其是几位年纪大的。像井营村的老魏,别人都喊他“魏大眼”,1993年的时候已经86岁了,是个老鳏夫。据说从前他当过保长,后来自然落魄了,就靠当“行户”弄碗饭吃。还有一个被人叫做“老白套”的,那年也是80多岁了。这两个老前辈在第二年的集会上就见不到了,他们的同事说“年纪大,上不成会了”。倒是薛庄会上93岁的老“行户”刘群成在会上又“晃荡”了好几年。
老人身材矮小,背几乎弯伏成90度角,黑瘦的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几绺柔白的山羊胡须生动地翘着。老人通常斜挎一包一秤,逢会蹒跚而至。尽管他已口齿迟缓,比划价格时手臂抖动不停,但还是能说成些生意,弄几个零钱花花。他已不能独个儿提秤称猪娃儿,要在他人的帮助之下才能完成交易过程,这是猪市上老经纪人享受的优待。
1995年初冬,我来到刘群成家里。他家住在平顶山市郊的华山村。老头生于1902年农历九月初九,属虎,22岁起开始当行户。1995年,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猪年,他这个名副其实的“老说家儿”还在猪市上说合交易。他一生未离故土,与猪打了一辈子交道。
他说:“我小时候罪可受大了。俺爹就是行户,在我们12岁那年死了。我弟兄四个,我是老二。十来岁那一年,遇上年馑,没啥可吃,人们就把麦糠、榆树皮、豆腐渣、糖渣、荞麦花和叶子掺在一起炒,炒完了用小花磨一拐,然后和着清水吃。吃时怪美,吃完了可就受罪了,肚子里又麻又疼,直不起来身子,只能抱着头哭。民国18年年馑更惨,一春天都不下雨,到麦口起时麦苗干到地里能点着火,人们没啥吃就吃树叶,开始是吃榆树叶,后来吃桐树、椿树叶,苦也得吃。树叶吃光了,就吃豇豆棵子。那一年,一直到阴历九月二十才下雨,好不容易下雨了,人们赶着种荞麦,荞麦长大了光有秆没有叶,叶子都被人们捋吃了。”
老人说他曾经上过七天学,就七天。“没办法,家里太穷了。”后来他就“上会”了。说起会,老人滔滔不绝。“旧社会是一人江山,万人码头,会都大得没归结(意为大得很)。我从22岁开始和伙计们一起做生意,就是收猪,赶会当经纪,方圆百十里到处跑。香山寺的会是年年都去,像井营十月十,滍阳街三月二十八、七月十五和小满会,红石营十月十一,宋村二月二十四,徐营四月初四,曹镇三月初六、十月初十、十二月初一等地的老日子会,我都去赶。还有翟集、闹店、常庄、羊石、盆锅、陶寨等地也都去,没有洋车(指自行车),都是步行,几十里地来回跑。那时候猪多得很,汉口的猪娃客都来这里,除了收猪娃儿,他们还买大猪。他们来了把钱一掏,我们就下到村子里收购,也不过秤,估约摸,收几十头圈一圈,完了赶着回去。去的时候背一个褡裢,挣了钱了就装进去。另外背一兜馍,啥时候饿了,到人家门口掂一壶茶就着吃。有时候跑得远,到鲁山辛集一带,猪娃客也跟着,管他们吃喝,肉杂碎汤、面条管饱。”
交谈中,老人突然问我:“你见过官没有?”我说:“没有。”他笑了,说:“是没有,连他也没有。”他指了指坐在旁边的84岁的三弟刘全成。然后接着说:“我就见过,我还见过大官拜翰林。俺那一茬人就剩下我自己了。这世道也变化大了,我小时候是留辫子,干活碍事,砍秫秫砍玉米得盘到脑后,再用筷子别起来。后来到小禹州去卖花生,碰到人家要剪辫子,我吓得戴上草帽翻墙跑了,可回来后还是被剪掉了,还哭了一场。”老人说他那辫子有半斤重,这么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
他说:“我这一辈子啥钱都花过,元宝、碎银子、铜元、纸洋、小钱、现洋都经过手。我这人实受,一辈子不会捣鼓个事儿,就是干经纪挣钱吃饭,除了合作社时期是给大伙收猪,一辈子都干这,前后干了70多年,即使是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也没有间断。”
在《河南新志》中,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猪,河南各县均产之。猪之阉者谓之豚。据经济调查报告,民国7年,为3857500余头,且累年皆有增加,畜猪之家,大约一岁而成。各县城乡市镇,皆有售所。每逢市集之期,辄有贫民三数人主持其事,凡买卖者,为之评定其价值,双方皆取其佣金;时或易人,不为恒业。而湖北商人之来购者,或即其所住之店家请一人为导,自往各村定买。每群数十头或百余头。购齐之后,驱之而行,一人导行于前,一人执鞭于后,逐队奔驰,日数十里,贩至汉口及沿江各埠……
这与老人给讲的经历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如今再也见不到驱猪赶猪群的情形了,稍远一些的猪娃客,是雇了汽车,把猪娃装进箱笼运走。
热闹的猪娃儿交易
1994年5月的一天,太阳刚刚升起,我骑着自行车到了附近苗侯村白龟山水库大坝闸门南头的猪市。远远的就听到人声鼎沸,以及唧唧哇哇的猪娃的尖叫声。走近了被吓了一跳,这里猪娃儿真多,是我见到的规模最大的猪娃市场。
苗侯的猪市在大路边的树林子里,高大的梧桐和白杨树笼罩着一大片空地,路旁边有一个入口,由一个行户看守着,以防备没有交交易费的买主把猪拉出去。空地里挤满了人以及架子车、自行车、摩托车和带着特制笼子的小拖拉机,笼子里装满了猪娃儿,地上也一排一堆儿地放满了猪娃儿。那场面大得一眼望不到边。我是挤着才进去的,根本无法下手拍摄。
三三两两扛着秤的行户被买卖双方围着,人群中间是一车猪娃儿,猪娃儿喂得饱饱的,皮毛也是干干净净的,只是前蹄被捆绑着。时不时有人伸手抚摸着猪娃儿,那样子就像是抚摸自己的孩子。
买家反复看着一窝猪娃儿,问:“几块?”猪娃儿是论斤卖的,他的意思是多少钱一斤。
卖家回道:“你给多少?”
“你是卖家儿你先说!”买家就用眼盯住对方。
“我这可是好猪娃儿,吃得好,长得快……少7块不卖!”
“咦——算了吧,人家的才卖4块,你都要7块。你那是金猪娃儿?”
双方谁也不言语了。行户说话了,他问买家儿:“真要还是假要?来来来,我说说看。”
行户边说边把一只手伸进了买家的衣襟底下,这叫摸码子。买家儿也把一只手伸进衣襟儿,俩人悄悄地摸索了一会儿,众人也看不见。只见行户又把手伸向了卖家,如此反复了几回,双方的表情越来越轻松,大伙知道生意说得差不多了。只听行户说:“这样吧,零头去掉,五块钱一斤,贽吧!”“贽”就是用秤称的意思。末了说买家儿:“佣钱你出。”在千年前,这佣钱叫做“牙钱”。
买卖双方不再有异议,就开秤。行户站在车帮上把猪娃儿一只一只地仔细称了,一窝7只,猪娃儿一共170多斤。完了找会计算账开票。买家儿低了头,从裤腰里慢慢摸出一沓票子,一张张地数过交给行户,开始往自带的口袋里装猪娃儿。行户数过了钱交给卖家儿,笑着说:“别嫌少,可没少卖!”卖家儿接过钱,一张张地对着天空照,看是不是假币。行户的成交额也被会计记下来,集会散了以后他要凭当日说合的成交量分钱。当然,行户们分得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要上缴的。
拍摄间隙,我认识了交易员的头儿老王,他说曹镇乡共有24名交易员,其中17名在这里。他们都属郊区工商局管理,每人缴100元风险抵押金,经批准后才能上会。这有些像古代“牙行”的管理方式。每人在每个会的收入也不等,多的可以弄到二三十块,少了也就十块八块,甚至更少。老王是领导,基本上不说生意,空手吸着烟到处转,负责处理纠纷和维持秩序。他告诉我,全乡的猪娃几乎都在这里交易,10天才一个会,所以买卖双方都有些急。不过这里是交通要道,买卖双方运输都方便。
当年9月的一天,我去了市郊的焦店猪市。由于季节因素,当天的猪娃特别抢手,价钱也高,三块四五一斤。每当一车猪娃拉到,买主们一哄而上你争我夺,瞬时抢个净光。很多人苦于无猪娃儿可买,在市上盘桓许久。行户们总说:“今天再有100头猪娃儿也打发不住!”因为生意兴隆,交易员都忙不过来,买主和卖主都得求着他们。
到了10月份,苗侯猪市的猪娃儿已涨至7块钱一斤,贵得有些吓人。可是仍然很抢手,买主远远多于卖主,主要是当年的粮价高了。
变化中的猪娃儿市场
猪市也在一年年变化着,除了摩托车、手机、计算机进入猪市之外,交易的节奏愈来愈快,也愈来愈规范了。在今年初的苗侯猪市上,我甚至见到了雇了“面的”买猪人,更有穿西装打领带的经纪人在说合生意。
前不久,我路遇一个叫陈福泉的行户,当年去刘群成老人家就是由他带的路。他告诉我,老刘已经不在了,老人整整活了100岁。
薛庄的猪市上,我结识了经纪人徐欣,他是鲁山徐营人,与著名的五四诗人徐玉诺是本家。那年他40多岁,已干了十来年行户。他说他是跟他爹学的行户,一开始,就是说不成生意,时间长了才慢慢入道能挣些钱养家糊口。不过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大儿子已20岁了,中学没上完跟着他来贩猪娃儿,遇到集会上猪娃儿多便宜时就买下运往他处出手,辛辛苦苦挣不了几个钱。他说:“年轻轻的跑跑路长点精细儿,说啥也不能叫他走我的老路。”我俩熟了,他非要我收下他的儿子当徒弟,跟我学照相,然后“开照相馆挣钱娶媳妇”。我领着他儿子去买了一架廉价的相机,教会他基本的拍摄方法。没想到他居然在过年时跑到山里靠给人家照相挣回了买相机的钱。不过因为缺钱,照相馆最终没有开起来。一晃又几年过去了,也不知小伙子如今在干什么。
(摘自《民间,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