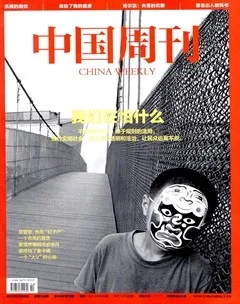民国教师节与教师处境
民国政府对义务教育和教师待遇发过不少誓愿,但“人不穷,不当小学教员”、“整脚没路走,才当小学教员”这些时语,或许更接近实际。
关于民国的教育和教师地位,近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美好的传说,比如:“那时的小学老师工资超过县长”、“中小学教师到县政府办事,县长是要亲自接待的”……
这些说法并非凭空而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而义务教育能否推行,取决于教师的薪俸问题能否合理解决。国民政府统一后,教育部于1933年3月颁布了《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学章程》,规定:“小学教职员之俸给,应根据其学历经验而为差别,但至少应以学校所在地个人生活费之两倍为标准。”
而在教师地位上,清政府把教师的地位提到与官员相等,民国教师待遇的规定也沿袭清制,参照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如1945年《行政院核定国民学校教职员任用待遇保障进修办法指令》规定:国民学校教员的最低薪金“得比照当地县市级公务员薪给标准支给。”
但如果把这些原则性规定全当作实际情况,未免太轻信。其实,探究一下民国时期的教师节,就能发现上面那些想象过于浪漫了。
中国最早的教师节是6月6日,不过这只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教师节,由时任上海大夏教育学院教授的教育家邰爽秋、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程其保等教育界热心人士于1931年5月倡议建立。他们当时发表的《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地位,增进教师修养”的呼吁,正是目睹教师薪俸微薄的穷困现状而深有感触。
正如1936年《我存》杂志上一篇文章所言:“教师节的产生在我国,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一个问题,或一椿事件发生,必定有他的背景,教师节当然也不能例外。按教师节的背景,是为改进和提高教师的待遇,使他们在生活问题上,不致彷徨阢陧,不致感受痛苦或困难。”“教师节的诞生,也很可以说是专为解决一般小学教师的生活问题,因为他们所领到的(即使不欠费)一些菲薄的薪金,委实够不上仰事俯蓄呢!”
教师节发起之后,社会的反应热烈。教师节发起人之一的邰爽秋1936年回忆:“宣言发布以后全国各地,闻风响应,五年以来,逢此节日,各地教师,多集会庆祝,休假纪念,或发表宣言,汇订工作,其情绪的热烈,令人十分兴奋,至于报章杂志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字,或为专家意见,或为教师自述,尤屡见不鲜,可见教育界同人和社会人士,都已觉悟到教师使命的重大,所以教师节的提倡,能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收水到渠成之效。”
但教师节的设立对教师的处境有改善吗?
令邰爽秋遗憾的是,教师节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再就教师节本身来说,政府方面,尚未曾正式承认颁布,缺乏政治推动的力量,所以每年机会也不过教师自动庆祝(甚至有被当局阻止的),既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又没有切实的工作,虽要入儿童节妇女节那般的热闹一番,亦不可得。”
1938年,国民政府终于颁布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不过将日子从6月6日迁移到当时考证出的孔子诞辰日——8月27日。教师节的宗旨也从原来的“改善教师待遇”调整为“鼓励教师服务精神、融合师生情感并唤起社会尊敬教师之观念”。
邰爽秋们等来了官方对教师节的承认,但官方对教师节的纪念方式,想必会让他们失望。因为官方的纪念重点转到了对孔教“人伦”观念的重提。1937年上海市教师节庆祝大会在文庙举行,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潘公展大讲“五伦”:“这个演讲堂,原来是明伦堂。所谓伦,大家都知道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或许有人以为五伦之中的第一伦君臣,现在已经不合时代,可以取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君主了。其实不然。君臣是一伦仍然需要存在的,因为君臣是代表上下的意义,一个公司里面有总经理有职员,一个学校里面有校长有教职员,一个机关里有长官有部属,五伦什么国体都有一个上下。既有上下之分,君臣一伦即不能废除。”
民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能说是虚情假意。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第二年五月就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义务教育》一案。193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立有“教育”专章,规定:“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
即使抗战爆发,义务教育也未搁置,因为蒋介石有一个“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的方针,要求将抗战与建国两步合作一步走,义务教育作为“建国”的根本举措,照常进行。1944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教育法》,规定6岁~12岁的学龄儿童应受基本教育。1944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又公布《强迫入学条例》,规定国民学校实行学龄儿童强迫入学,具体按照“劝告”、“警告”、“罚款”三个程序进行。
这些愿景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最大阻碍是经费问题。正如邰爽秋等人所说:“要使在职教师安心任事,当从改良待遇入手。”而就在南京政府“厉行义务教育”时,小学教师被欠薪等事却时有发生。
1928年,南京、杭州、吴淞、江都、阜宁等地小学教员为索取欠薪,纷纷辞职、请愿、罢教,要求改善待遇。1933年北平的小学教员要求当局还清积欠、按十成发薪未果,47校决定实行怠工,40余所小学教学停顿。
乡村小学教师的困窘生活,是当时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更可见问题的普遍存在。职位的不稳定也困扰着教员。民国实行教员聘任制,每到寒暑假,如果校长发给聘书,那么就继续留用,否则即默认为解聘。
导致教育经费拮据的头等因素是军费的挤占。美国教育家杜威1921年4、5月来广州讲学,发此感慨:“良以他们的大宗款项多用于军政,以致教育的经费不但不能保留原有的数目,还要时时裁减,军费与教育费的比较,差不多成八与一,至二十与一之比例。”徐特立也称:“说办义务教育没有钱的话,是不负责的话。若是拿养一个兵的钱养一个小学教员,以湖南计算,那还了得!”
由于教育经费常被挪用,各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最后汇成一场全国性运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立即下令要求各省保障教育经费的独立。南京政府后来又规定各省教育经费不得低于财政预算的30%,然而这一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
其实,民国时得享优渥生活的教师并非没有,但都集中在大学校园。教育经费偏重高等教育,忽视小学,是民国特色。大学教师的月薪往往是小学教师的十倍甚至更多。1931年,国际联盟考察团专家就指出:“按照欧洲小学教师与大学教授薪水之差,未超过1:3或1:4者,而中国则较大若十倍且超过此数”,进而批评中国政府“对于为大众而设之初等学校,较之中等学校,尤其较之高等学校,实异常忽视。”
小学教师的处境是评判一国基础教育完善程度的指标。民国固然有“不可失落”的教育传统,但脱离事实的缅怀并无多少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