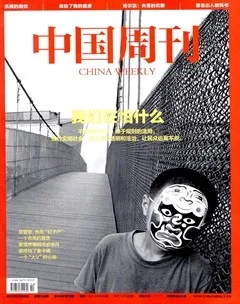秋忆如梭

我们都在四季的轮回里感叹着时光如梭。当冬雪初解,报春花就迫不及待地突破掩覆,露出嫩芽,春天踩着冰花降临了;而当油菜花8月中尚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盛开时,神州处处已是炎热难耐;一俟中秋,热带风暴还未退场,寒潮就在北方积蓄力量,不等树叶枯黄,寒流就从北向南席卷大地。秋天是成熟的季节,犹如人界中年,一切都是那么的匆忙。
中国的秋季是非常短暂的,不仅仅是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彼岸和最大的大陆前缘,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割裂了西风带,从而造就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季风气候。夏季风长驱直入,给西部和北部地区送去了丰沛的降水,也送去了高温,从而使中国北部地区夏季温度普遍高于全球同纬度地区;而冬季风也照样席卷了海南岛五指山以北的几乎全部地区,使南方位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城市冬季温度大幅度低于全球同纬度的城市。这就是中国春天的步伐迟缓无力,秋天的脚步却匆匆而过的主要原因。也许正是由于秋季的短促,才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著述里,留下了大量的对不同地区秋天的感叹。
屈原在《九歌·湘夫人》里用“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的词句,感叹洞庭湖一场微弱的秋风,就使翠绿的湖滨变成一片枯黄的树叶。汉刘彻在《秋风辞》里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用大雁南行记录秋天的到来,而曹丕在《燕歌行》中,引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以露水结霜预示深秋来临。唐王勃《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里“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用野鸭在晚霞里高下齐飞的场景,讲述江西鄱阳湖的秋景。唐代的诗圣李白在《秋登宣城谢朓北楼》里写道“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用人家缕缕炊烟,橘柚一片深碧,梧桐已显微黄,记述了安徽宣州的一片深秋景色。
宋代的苏轼也曾经用橙橘的色彩变化寓意秋季,他在《赠刘景文》里这样写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杜甫可以说是在感秋中最浓墨重彩的,他在《茅屋为秋风所坡歌》里,讲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反映了其时关中地区阴历八月就已经寒秋立显了。他还在“翟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词句里,以秋雾四起褪去了原有的翠绿记述长江三峡的秋景。他还用生态景观的变化,告示秋天的来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借鸟兽的迁徙叙述季节的变化,如“高鸟黄云暮,寒蝉碧树秋”和“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前者写生境的差异,后者说深秋季节江水下降,连岸边的曾经被水浸泡的白沙都露出来了。唐代的岑参用“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描述中原地区广大农耕地区的秋色。唐代白居易的“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和刘禹锡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词句,都是以山峦之上,树叶颜色的更改喻示秋意的加深。性极喜水和阳光的荷花更成为记录秋季步伐的物象,如“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杜牧)、“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来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南唐李)、“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秦观)。
也许秋色的短暂,触动了文化人的忧愁,传世的涉秋诗词曲赋多少透出些悲凉,如辛弃疾在《昭君怨》里写道“落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流露出仕途处处受挫的无奈。今人秋季最喜欢的恐怕就是观赏那山巅的红叶,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不啻是代代人对红叶记忆的杰作……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自然界的变化通常寓意着人生的感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其实也就是他们对人生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