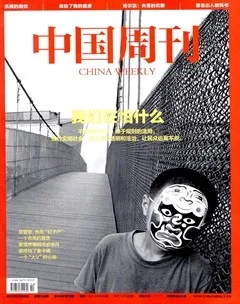案件为何“变脸”

民事纠纷或股权纠纷,突然变脸成为刑事案件,这是悬在企业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从1980年代,公安部、最高检不断发文,禁止此类现象。可利剑不断落下,斩断了人们的安全感和法律的尊严。
著名律师田文昌曾办过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台商在广东佛山做制鞋生意,产生了民事纠纷。一方不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而是出钱让当地公安介入,抓捕了另一人。在看守所里,遭遇刑讯逼供,办案人员毫不忌讳跟他讲是收了对方的钱,还称他出去后如果给钱,也能替他抓人。打了几年官司,被告最终被判无罪。
这并不是一起孤案。权力机关不恰当,甚至是非法介入企业家之间的民事纠纷,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但在近年来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针对这些现象,公安部、最高检多次发文明令禁止,甚至在2010年,最高检曾详细列出哪些经济纠纷才能被立案追诉,但依然没能有效制止。
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现象是什么样的?为何会愈演愈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了有“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他曾亲自代理过多起民事纠纷被刑事化的案子,所在律师事务所也举办过关于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研讨会。
民营企业家成为主要受害者
中国周刊:三年前,由您所在律师事务所牵头举办了“民事纠纷刑事化与和谐社会之冲突”的研讨会。为什么会举办这个研讨会?
田文昌: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初衷,是律师办案过程中的有感而发。近来,民事纠纷刑事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日益普遍化。出现了很不正常的倾向,一些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出现纠纷和利益争端的时候,会利用司法机关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中国周刊:如何理解“民事纠纷刑事化”这个概念?
田文昌:民事纠纷并没有涉及到犯罪的问题,应该通过协商、诉讼、仲裁这三种方式来解决。有的是,这样走了,没走通,没走下去。还有的是干脆我就不走这条道,让公安抓人可能更快捷。直接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介入,利用公权力达到目的。
中国周刊: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案件有哪些特点?
田文昌:争议的数额很大,利益驱动力强。被追诉的当事人往往是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罪名也相对稳定。诉讼程序极其复杂且相当长,诉讼中罪名不断变化。
中国周刊:通常情况下,哪些民事纠纷容易被刑事化?以什么罪名?
田文昌:合同纠纷、欠款纠纷、股东纠纷、员工纠纷这些方面多一点。这些纠纷常常转化为合同诈骗、贷款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侵占、挪用、虚报注册资本、抽逃资金、伪造公务印章等等,因为这些罪比较贴边。
中国周刊: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受害者?
田文昌:民营企业家没有那么大的后台,他弱啊。国企毕竟还不敢轻易动,但也有动的。
强大利益驱动
中国周刊:民事纠纷刑事化的主要原因是立法等技术层面上的,还是执法层面的?
田文昌:有些是立法等技术层面上的,但从立法上来看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线是越来越清楚,制定得越来越明确。更大的原因还是在执法上,利用公权力。这两者是结合的,利用公权力也得找着理由啊。执法机关不恰当的将民事纠纷用刑事手段来处理,最根本的还是跟法制环境有关。
中国周刊:民事手段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反而愿意采用刑事手段呢?
田文昌: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跟整个法制环境有关。有的走民事不公平,有的走民事太慢,有的就没理,有的就不懂法,就想着抓人,抓人快。这样下来,有一种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看你这么干,他这么干,都这么快,都得逞了。
有的案子是这样的,我和公安的利益绑在一块了,到后来是骑虎难下了,我想撤公安都不让撤了。我办过好多夫妻、亲母子、亲父子、亲兄弟这样的案子,有些经过别人的劝说决定收,但收不回来了。为什么?你收回来了,别人怎么办?已经绑在一块了。把他抓了,得的利益,咱俩要分的。
中国周刊:民事纠纷为什么能够被刑事化?哪些环节容易导致它被刑事化?
田文昌:强大的利益驱动,他就这么做了。从公安进入侦查开始就被刑事化。有的就是利益链条,绑一块了。钱的作用非常大,也有权力。上级的干预,是不得不去做的。领导批案是很严重的。这次的刑法修改,我们那天开会还在提,律师能不能提案增加一个罪名,关于领导干预案件。这段时间,台湾那么火的“关说”。我们有多少“官说”啊。哪怕判一年也行啊,就老实了。但这个难啊。我办过一个台商的案子,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给弄进去了,看守所里人就对他说,别人花钱把你弄进来了,我们没办法,等你出去后,你给我钱,我再抓他。
这说到底就是一个法制环境的问题,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法制环境好的话,谁干啊。
中国周刊:民事纠纷被刑事化的案件翻案的多吗?
田文昌:少,得逞的多。这是最可怕的。权力机关被利用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成功的也有,但很难。西安有对合作了十多年的香港房地产商,产生了纠纷,一个把另一个给弄进去了,判了十多年。我给打了三年多,打出来了,无罪释放。后来他来找我,要把对方给弄进去。我说我救了你,尽心了,不愿意帮你弄他人。最后他真是找人把那人弄进去了。
我找出他们错误的证据多了,可别人就是不理你。我们国家有错案追究,这是双刃剑。有的一错到底,我不能认错啊。
“口号管不了”
中国周刊: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早在八十年代就有,公安部也在八九十年代多次就此现象发文。为什么屡禁不绝?
田文昌:法制环境不好。公安机关权力过大。权力干预,独立性没有了,制约性没有了,程序没有了。法律的公正最主要靠程序来保证,你没有程序怎么保证?个人说了算,法律算什么?证据链没用,有的是你说了也白说,有的是说都不让你说。
中国提出“依法治国”时,标志性的改变就是法检两家规格提高了,两高的院长高于部级半格,副国级。公安部不动。十年前,公安部长个人的级别高过检方。我们一看就知道坏事了。公安成了老大了,你的事谁敢不给你做啊。
中国周刊:2010年,最高检和公安部甚至联合发文,详细列出86种能立案追诉的经济纠纷。如此细的措施,为何还不能有效制约民事纠纷被刑事化?
田文昌:管不了。那是口号,没有机制的设计。发现的有处罚的,但能让你发现吗?真发现的话,真处罚吗?那也不一定,力度不够。没有很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而有很强大的利益诱惑。现在最可怕的是,公检法机关办案收缴的赃款他们是提成的,这是政策允许的。一部分交国库,就地留一部分。这怎么能行?所以很多公检法愿意奔钱去。你看公检法的大楼盖得那么漂亮,怎么盖的?收缴赃款的提成成了财政上的支持了,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这种动力多可怕啊。
还有一个是指标制,这都多少年了。公安局,检察院都有指标,一年必须得办几件这样的案件,否则就过不了关,交不了差。公检法办案的指标制是很害人的。办案定指标、打黑定指标,这是非常愚昧的做法。
中国周刊:对于违规、违法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做法,是否有针对当事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措施?
田文昌:除了公安部、最高检的发文外,没有切实的措施去制约。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
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
[1989年3月15日]
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决不能把经济纠纷当做诈骗等经济犯罪来处理。一时难以划清的,要慎重从事,经过请示报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当处理,切不可轻易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以致造成被动和难以挽回的后果。
对于经济纠纷,应由有关企事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公安机关不要去干预。
禁止用非法手段提成牟利。不得随意超越职权范围,以查处诈骗罪为名,干预经济纠纷,替当事人追索欠债,从中提成牟利。非法动用强制措施,侵害经济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借机中饱私囊的,要依法严肃处理。(摘录)
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
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
[1992年4月25日]
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
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对于不符合国务院和公安部规定的收审条件的人,不得使用收审手段。
坚决杜绝强行抓捕收审经济纠纷当事人作“人质”,逼债索要款物,彻底纠正“以收代侦”、“退款放人”的非法做法。(摘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检察机关
越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捕人的通知
[1992年7月20日]
检察机关一律不得介入属于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案件,更不允许超越案件管辖权限去直接受理诈骗、投机倒把等案件。
检察机关不得以任何借口,采用任何形式为经济纠纷当事人追款讨债。更不允许滥用职权,采用限制甚至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扣押一方当事人或其家属作人质,为另一方当事人逼索债务。(摘录)
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
[1995年2月25日]
对于继续把经济纠纷当成诈骗案件办理的,上级公安机关应予以警告纠正;对不予改正者,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对于因越权干预经济纠纷造成行政或刑事赔偿的,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民警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最追刑事责任。(摘录)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
关于对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案件
依法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通知
[2002年5月22日]
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要严格区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尤其要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违约、债务纠纷的界限,以及商业秘密与进入公知领域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的界限,做到慎重稳妥,不枉不纵,依法打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不能把履行合同中发生的经济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对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捕的经济犯罪案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能作出批捕决定,对于明显属于经济纠纷不构成犯罪的,或者罪与非罪性质不明的,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应作出批捕决定。要认真审查被控告方提供的材料和辩解,对只有控告方的控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批捕决定。(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