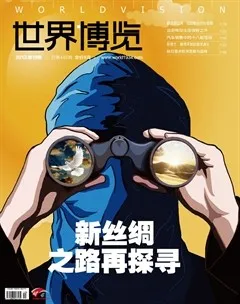拉伯世界的改革者和独裁者

身高接近1米90、长着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的巴沙尔·阿萨德一点也不像人们心目中的暴君。但正是这位看起来安静谦和,甚至有些羞怯笨拙的年轻的叙利亚总统,被指控为所有阿拉伯独裁者中最肆无忌惮地镇压民众民主诉求的魔鬼。有关他对自己同胞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是近来国际舆论的焦点,他的“垂死挣扎”无情地粉碎了那些曾天真地期待他成为一个开明改革者的幻想。
巴沙尔在英国求学时的老师、眼科医生埃德蒙·舒伦堡近日在接受《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采访时悲伤地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那个我认识的年轻人会下令使用化学武器……这可能是那个政府中其他人的决定。”
我愿意相信,舒伦堡医生心目中的那位年轻人与今天西方报纸上的叙利亚总统都是真实的,它们折射出这位阿拉伯世界年轻独裁者的复杂人生的不同侧面。
1994年,巴沙尔的父亲、有“中东雄狮”之称的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着意培养的接班人——长子巴西勒在前往机场的一次车祸中遇难。老阿萨德不得已,决定召回当时正在伦敦学医的巴沙尔,培养他成为新的接班人,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00年,当不满35岁的巴沙尔·阿萨德从突发心脏病去世的父亲那里承继大位,成为这个被称为“阿拉伯世界心脏”的国家的新领导人时,他曾经被叙利亚、中东乃至全世界寄予厚望。年轻、开明、温和、现代……这是上任伊始的巴沙尔留给叙利亚人民的第一眼好印象,而他的西方教育背景也使外部世界相信,他能够在这个族群复杂、教派繁多的社会里继续推行世俗化路线,处理好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关系。
巴沙尔似乎也愿意响应民意,他在就职之初就承诺,会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和自由选举,给老阿萨德30年铁腕统治下专制僵化的叙利亚注入更多政治和经济自由。在巴沙尔的领导下,叙利亚经历了短时间的一段宽松期:数以千计的政治犯被释放,新闻管制明显放宽,集会和结社自由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开……
在经济上,巴沙尔雇佣了一批曾在美国留学工作过的精英人士和IMF供职的经济学家出任内阁成员,明确宣布叙利亚将改革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推行私有化,走市场经济之路……
当时这一系列“改革新气象”被兴奋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称为“大马士革之春”,明智的巴沙尔也很乐意自己被视为这场席卷全社会的“大马士革之春”的催生者和赞助者。尤其受到阿拉伯世界青年欢迎的,是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来的积极反腐的形象、务实亲民的作风,以及对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重视。
这位年轻的总统在就任之初便雷厉风行地打击腐败,剔除了不少老派官员,在很短时间内令老阿萨德留下的陈腐低效的叙利亚官僚体系有所起色。为了表现出不同于父亲高高在上的威权军人领袖形象,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一直都是西装领带,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银行家或公司经理。他经常自己开车,甩开保镖带上家人到普通超市购物,或出现在寻常饭馆里和老百姓聊天。他和夫人阿斯玛还喜欢像西方人那样,在周末带着孩子,骑自行车去郊外野餐……这些都让长期生活于政治上高压专制的叙利亚乃至阿拉伯民众备感耳目一新。
巴沙尔有一位频繁出镜的美貌妻子,这在保守闭塞的中东阿拉伯社会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也给他的形象平添了不少柔性的光彩。她就是1992年巴沙尔在伦敦学医时遇到的阿斯玛·阿赫拉斯。
阿斯玛出生于英国,拥有英国国籍和一部分英国血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西方媒体眼里,这位喜欢时装设计的叙利亚第一夫人是西方现代化与阿拉伯传统完美结合的典范。对于那些热切地希望巴沙尔成为改革者的人来说,阿斯玛经常出现在镜头上的迷人形象强化了这一愿景。
但10多年后回头再来看,巴沙尔没有让叙利亚人民过上好日子。他的那些改革被证明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改革的步伐不仅缓慢,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在襁褓中即被扼杀,巴沙尔的统治面目也日益向旧式的“铁腕”回归。
在“大马士革之春”的初期,巴沙尔曾亲自组织了一个“改革论坛”,倡导执政党和反对派、知识分子间的建设性对话。但是,当“论坛”的话题渐趋激烈且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执政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内部——表达出他们对这场“公民运动”的同情和关注之后,巴沙尔立即宣称它破坏了“稳定”,并莫须有地指控运动背后有境内外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的“敌对势力”推手,随即镇压了此次运动。那些幻想借“大马士革之春”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民主改革运动的兴奋的知识分子不是入狱便是流亡,从此一蹶不振。
自那以后,巴沙尔本人的言辞也越来越谨慎,“民主”只是有气无力的口头愿景。此外,他还一再表示:叙利亚“优先考虑的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经济上,叙利亚政府虽然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放松了一部分管制,对某些领域实行了私有化,但它不愿意放开那些国有垄断行业,向民间和外来资本提供平等竞争机会。这使得叙利亚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大多数老百姓并没分享到它的成果,贫富分化愈演愈烈,中产阶级的财富迅速缩水,贫困人口的生活雪上加霜。到“阿拉伯之春”革命爆发前,叙利亚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
一些观察家相信,巴沙尔的改革之所以夭折,以至于叙利亚会沦落到今天这样不可救药的境地,是因为在这位年轻的西方流行文化爱好者背后,有着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其中包括他的家族势力——的羁绊和掣肘。执政至今,巴沙尔确实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出过不少“新政”,但每当有风吹草动,他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退缩。
但更多人认为,经过老阿萨德的精心栽培和10多年的执政,巴沙尔已经牢牢掌控了叙利亚政局的领导地位。他最初的那些“改革”只是他博取民心的策略,而在各领域掌握政治经济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支撑他时至今日统治地位依然稳固的根本力量,才真正与他坐在“一条船上”,也是他必须竭力拉拢的。
我深深地相信,上述两者都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而且它们其实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古往今来一切渴望有所作为的独裁者,无一不试图对每况愈下的现状作出重大改变以图振兴,然而没有一个改革者会想要通过改革来削弱自己的统治。而他们的改革能否真正取得作为,则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否在这两方面求得很好的平衡,将旧有体制所蕴含的正面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进而拓展体制的疆界。
“巴沙尔” (بشار,Baššār)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带来好消息的人”。但很遗憾,历史将证明,一度几乎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巴沙尔·阿萨德不仅是一个蹩脚的改革者,也是一个缺乏运气眷顾的独裁者。这位昔日的优秀学生和出色大夫没能为自己和叙利亚开出一张治国良方,就像所有专制体制下的失败统治者一样,他的人生注定是一场赢家通吃和没有退路的决斗。他通过一步一步的参与,主动或被迫地塑造并强化了这一罪恶体制,而他本人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千疮百孔的罪恶体制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