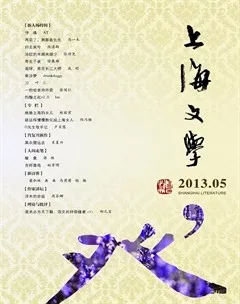浮木的命运
我是台湾学者中研究丁玲的第一人。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曾使我震动不已:那个挣扎在新旧夹缝间的女子莎菲,似乎在1970年代又还魂而寄附在我的身上,我似乎总听到她在狂笑怜惜着自己:“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所以,丁玲,她的作品与生平,便成了我的研究课题。为了收集资料,我曾在1977年考取台湾教育部公费留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到美国各大图书馆收集相关资料,独自漂泊异邦过了两年孤寂的“访问学者”生涯,终于写完这本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论文《丁玲与中共文学》,1979年再带回台湾发表。
结果我的这本《丁玲与中共文学》论文不但高分通过,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还立刻被聘任为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那里工作一年,完成了我的公费义务。我的论文也得到台北成文出版社的赏识,列入他们即将出版的《现代文学丛刊》中,编辑委员有夏志清、葛浩文等著名学者。这本书在1980年付梓后,不但荣获“台湾国科会”的研究奖助金,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台湾地区、大陆的各大图书馆也加以收藏。大陆的学术界也将它列入丁玲研究的学术专书之一。这一来,我才卸下了心头的重担,好像对自己、对莎菲都已有了交待。
然而,我曾经失望过、颓唐过。丁玲在1978年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曾于198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到美国来访问。她的演讲我虽失之交臂,但风闻大部分的听众对她“随波逐流”、“曲线革命”的态度表示异议,觉得她不复有莎菲女士之风。而当我看到程步奎为她写的诗:“有时在浪头上”,“有时在浪底下”,“你的命运只是一根浮木,随波逐流?”我也曾颓丧地认为莎菲女士是死了,死在一连串的文艺整风里,死在北大荒的劳改里。
而在1985年的6月6日,我终于来到北京,见到了丁玲。在等待了十年的岁月后,我飞越了万里的关山,就是为了印证这个答案吗?
那是一栋坐落在北京市的公寓大楼,附近是个小菜场,几个个体户热心地叫卖着茄子、黄瓜、花椰菜,菜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风沙,是北京特有的风情。
一架古旧的电梯吱吱嘎嘎地将我们带到了二十二楼,同行的小游告诉我,中国作协的一些成员,如茅盾、曹禺、王蒙、白桦、艾青等人,也是这里的居民。于是,这座平淡、斑驳的灰色建筑便平添了几许风采,似乎每一转头、回身,便能碰触到这些创造历史的人物。回想自己在台湾就读“政大东亚研究所”的日子,作为一个初窥学术堂奥的学子,20世纪30年代作家求新、求变的勇气,爱国与追求理想的精神,便如磁石般吸引着我,而丁玲,作为一个家庭的叛徒、新派女作家、社会的改革者,更有她不可抗拒的魅力。
当小游按着18号的门铃,我的手心微微出着汗:我想破门而入,又想不顾一切地落荒而逃。只因为想像总比事实来得美好,而理想的幻灭,或许终身将不再恢复。
矛盾挣扎中,门已嘎然而开,丁玲就那么猝不及防地落入我的眼帘中。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奇异的,但并不如姚蓬子所说的:“充满了生之忧郁……显出一个没落贵族的寂寞与尊严。”她有点矮,有点胖,红润的圆脸上漾着开朗的笑容,一头白发中依稀有几茎青丝,实在看不出她已有八十一岁的高龄。
丁玲站起来跟我握手,第一句话便是:“欢迎你到北京来。”语音洪亮、爽朗又诚恳。她的丈夫陈明在一旁热情地说:“我们五年前(1980年)就在美国看到你的书了,没想到你这样的年轻。”至此,我才松弛下来,心上有如落下一块大石。只因为,在书中我曾严酷地批评她文风的转变,作为一个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妇女,我曾赞美她自由主义的作品,而对她在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那本得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不以为然。
我从不苛责丁玲的私人生活(她一共结了三次婚),但详细地描述了她最忌讳人谈起的第二次婚姻:与冯达的结合,但看来对此她并没有放在心上。冯达是早期的俄国留学生,当过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秘书。丁玲在第一任丈夫胡也频死前就暗恋着冯达,并为他写下了缠绵悱恻、连毛泽东都击节赞赏的散文《不算情书》。她的文中曾有这样的句子:
我还是喜欢什么都告诉你,把你当一个我最靠得住的朋友……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来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末(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 好了。
在当时保守的中国社会里,可说是骇世惊俗,何况她跟胡也频的婚姻还算幸福,她却毫不在乎。
丁玲在胡也频死后,不顾世俗的非议,立即与冯达同居。1933年,他们双双被国民党逮捕,幽囚南京。但这段婚姻的下场是:1936年她私自从南京出走,经北京辗转到了延安,等于丢弃了身患肺痨的冯达和与冯达所生、还在襁褓中的女儿蒋祖慧。后来她在延安跟陈明结了婚,而冯达竟投靠了国民党,并在1949年后跟国民党到了台湾,曾在“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当顾问,等于是我的同事。一对昔日的恋人,那时各为其主,泾渭分明,再也无缘相见了。
这段婚姻当时在大陆还是不公开的,一般人以为丁玲只结了两次婚:胡也频和陈明。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究竟冯达是否如史沫特莱女士所说的,他本来就是潜伏在共产党内的国民党特务,而丁玲在1933年被捕,是由于冯达的出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为了怕丁玲、陈明难堪,我先声明如果有任何不便回答的问题,她可以不回答,但请她介绍我去读一些资料。但她坚决地摇摇头,爽利地说:“问吧!没什么不方便的。”然而,提起冯达,她的声音仍不自觉地低沉下来,她用一种感伤的语调回答我的问题:
“冯达不是国民党特务……从来就不是,他是后来才转变的。”她的眼光无比柔和,“冯达在抗战后又跟徐恩曾(当初逮捕丁玲、冯达的人)搭上关系,1947年跟国民党去了台湾。这些事,我也是在1950年代见到冯雪峰才听他提起的(冯达和冯雪峰是好朋友)。我跟冯达在一起生活过几年,他什么事会做,什么事不会做,我是知道的。对他这方面的人格,我还有一点基本的信任。”
但是,她的眼神突然凌厉起来:“他是条狗!他的毛病是既没用、没骨气,又不会投机!什么事不好做,要去投靠国民党!他现在在台北吃得开吗?”她咄咄逼人地看了我一眼,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她尖锐地接着说:“我早知道他吃不开的!没骨气的人谁瞧得起啊?”
陈明在一旁尴尬地保持沉默,我则在心里暗暗地喝了声彩:这才是丁玲!那个心里有了话,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血性女子!那个写《三八节有感》,触怒毛泽东,却倔强不肯认错的湖南骡子!
回想当年在台北,我曾两次求见冯达,第一次被拒绝;第二次托人去说,他勉强答应,却事先声明不谈丁玲,因为他在台湾又结了婚,有妻子儿女,不愿意破坏家庭的安宁。我心中不快,又因出国在即,这次的约谈就此不了了之。看来比起丁玲,冯达是少了那么一点面对现实、对历史负责的勇气,或许他是有难言之隐吧?
接着,我问丁玲是否如徐恩曾所说的,在南京写过《自白书》。她坚决否认:“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我问你啊,我逃走了以后,徐恩曾要不要继续做官啊?要不要想办法交差啊?他说我写过《自白书》,拿出来看看啊!他根本拿不出来!他还说送我一笔路费,去北京玩,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啊?我告诉你,我们被关在南京的时候,他是派三个人看守我们,一个月给我们一百大洋的生活费,日子过得不错,可是没有一点自由。”
她歇了一口气继续说:“前几年有两个日本学者(高田譲和野泽俊静)合写了一篇《丁玲转向考》,就是考证我当年在南京有没有办过自新手续,结论是没有!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所以我常常告诉陈明,这几年我老是出国访问,去得也烦了(她两天前刚从澳洲回来),以后谁请我,我都不去了,只有日本除外。冲着这两个人的面子,再累我也要去一趟的。”她看了一下陈明,陈明给了她一个充满谅解的笑容,可看出他们夫妻的感情弥笃。
那么,丁玲又如何从南京逃到延安的呢?她说:“是曹靖华、张天翼、胡风、鲁迅、冯雪峰、聂绀弩等人帮的忙。详细的情形我不愿意多讲,因为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即《魍魉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叙述我被捕的前因后果,以后你看了我的书就会知道的!”其实根据左派文人英山(I.Insum)的说法,丁玲当初一逃到陕北,就决意要写《南京三年》,但后来因顾虑到统一战线的利益(国共合作抗日),才暂时放弃了出版的计划。但我很讶异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没有完稿,是政治因素呢,还是丁玲忙于杂务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我提到了沈从文:“你跟沈从文还有来往吗?”她说:“有的,我们还是朋友,但见面机会不多。尤其是最近我批评他新发表的一篇文章写得不好,他有点不高兴,就很少来找我了。”
“听说他在1933年你被国民党逮捕后,表现得很冷淡,几次回湖南,都没有去探望你的母亲跟孩子,这件事对你们的友情有没有影响呢?”
她想了一想,回答道:“算了,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只是我对他写的那本《记丁玲》一直不以为然。你知道,那本书是他在我被捕后写的,那时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全书用的是小说的体裁,其实不太可信。可是,我自己在1979年才看到那本书,还是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为什么呢?”我问。
她说:“那本书在上海出了一版就停了,没有再版。我自己后来又逃到延安,对内地的出版界很隔阂。陈明常说,你觉得那本书写得不好就要反驳啊,否则因为沈从文是你的好朋友,每个研究你的人都拿那本书当原始资料,那不是糟糕了?可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沈从文年纪也大了,身体很差,我不愿意刺激他。但我目前正在写回忆录,等书出版了以后,你可以作个比较。”
她低下头喝了一口茶,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私人问题:“听说沈从文在你嫁给胡也频后追求过你,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呢?”
她反应极快地说:“没有!他那个人基本上跟我个性不合,在一起并不怎么投缘的。”
陈明在一旁补充说:“哈!沈从文这个人最恰当的描述就是‘胆小如鼠’,他不会,也不敢喜欢丁玲的。”在客厅的几个人都一致哈哈大笑起来,一时把这个问题岔开了去。
接着,我赞美她的《三八节有感》写得好。这篇文章指出延安妇女由于男性的歧视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并呼吁当局加以改善,文中曾有这样的句子:“延安女同志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都能作为有趣的话题被提起。而且各式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有的非议。”如果她们结了婚,“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当时得到许多读者的共鸣,丁玲却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中受到批斗。
她对我的赞美显然感到高兴,但不知是否因为政治上的顾虑,她还是自我批评了一番:“我那篇文章是偏激了点。我那时年轻嘛,难免火气大一些。现在想起来,批评别人应先说好,再说坏,不应该以偏概全,才能被别人接受。”
谈到中国当前的女权问题,我问她是否认为中国的妇女真的已“撑起半边天”?她先反问我:“你觉得在国外,男女已完全平等了吗?”我回答说没有。她接着说:“是嘛,男女很难完全平等的。目前的中国妇女在生产上已撑起半边天,甚至在许多家庭中都是由媳妇当家。”
小游在一旁补充道:“但是中国的法律还是照顾妇女的。妇女如果遭遇婚姻问题,如遭丈夫虐待、遗弃,可以向‘妇联’投诉,法官也倾向同情妇女的。”我点头不做评论。因为在中国住了几天,接触到一些办事人员,商店伙计,饭店、旅馆的服务生,似乎女的都相当勤快独立,甚至比男的还精明能干,比起西方的先进妇女毫不逊色,除了服务态度差一点。至少中国这些年来的妇女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丁玲说的“在生产上已撑起半边天”的说法也是对的。
最后,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她那二十年劳改的生活(1957-1978)。她先做了更正:“我这二十年并不完全是劳改,有一段时间是坐牢。我跟陈明1958年被送到北大荒,在那儿住到1970年,那时‘文革’进行得很激烈,北京、上海的‘红卫兵’都到北大荒串联,就把我押到北京的秦城监狱关了五年。”
我插嘴道:“那陈明呢?”她说:“不在一起,那五年我完全没有他的消息。”
我暗暗地叹了一口气:“那真惨。那这以后呢?”
“以后啊,就跟陈明团聚,并且搬到山西(长治附近)去了。”
1978年平反复出后,丁玲写了不少跟北大荒有关的文章,流露出深切的留恋之情,一般的读者都批评她矫情,觉得一个大牌作家,被贬到北大荒去种菜养鸡,居然还津津乐道、依依不舍,简直难以置信。我读她的《牛棚小品》(三章),里面就提到有一阵子她和陈明在北大荒被隔离审查,她被单独拘禁,陈明下“牛棚”,二人住的小茅屋被查抄,两人不但挨打、挨骂、挨审,还被禁止见面,并被没收所有的纸张,只能用香烟纸及玉米叶子,偷偷地互传情愫。她提到每天怎样躲在玻璃窗后,偷看陈明排在“牛鬼蛇神”的行列中走过,提到陈明如何利用机会丢纸团给她。里面有一封情书是这样写的: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曾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她就靠这些书简来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光。
我还记得我读《牛棚小品》时那种为她不值的心情,特意问她那些“情书”内容的真假。她回答道:“都是真的。”她说:“那时我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吃了不少苦头,但在这以前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北大荒的风景美,居民又纯朴,我们交了好多朋友,大家一起劳动,生活很愉快的。”
她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北大荒是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冲积成的三江平原,一共有一百多个农场,最大的是友谊农场,有十一万个员工,我们每个都去过,那儿啊,真好,每个人都诚恳相待,就像1950年代那样,简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我平反后,还跟陈明在1980年回北大荒探亲,还带了一个美籍华裔学者梅仪慈女士一起去的,一共玩了两个礼拜,很开心。”陈明在一旁笑着接腔道:“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下回带你一起去。”
我必是露出了半信半疑的神情,因为她的管家王增如女士,马上抱了两大本相簿出来,一一地指给我看丁玲、陈明二人在北大荒住的小茅屋、与农场朋友的合影及一些北大荒的风土文物。照片中的丁玲,穿得虽破旧,却是神采焕发、精神勃勃的,并没有悲愤、萎靡的样子。
我还是不死心,接着问道:“那坐牢的五年呢?在秦城监狱里你可吃了苦头吧?”因为我总记得她在《牛棚小品》里写被关押到北京前,与陈明分离时那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场面:
门呀然一声开了,C(陈明)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
她却潇洒z1+VHo/F70p3jfHAhqkU1ngtqOv+9AjFenvzAKLWvnM=地说:“哈!被抓去监狱时,我心里可高兴了,我想我这回休养去了!关在牢里头,‘红卫兵’斗不到我,比哪里都安全。”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审视着她跟陈明。那两张坦然自若的脸,早就看不到昔日的伤痕。她的话让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一股活泼的生命力,一种永远“向前看”、不后悔,也不对困难低头的精神。
我在心里惊叹着:老舍被逼死了,沈从文改行研究考古去了,巴金封笔了,但丁玲还活着,还在不停地创作,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和热情支撑着她?她还是莎菲女士,那个浪漫而理想主义的女子,只是时代和环境,迫使她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同的是,经过岁月的锻炼,她早扬弃了那个苍白、颓废的自我,而注入了刚毅与勤奋。
那时,以八十一岁的高龄,丁玲仍然一年出一部她自嘲为“红白喜事”的杂文选集,真正投注心血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还有《在严寒的日子里》及描述北大荒生活的《风雪人间》等四个长篇。她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写作,至于家事,则由管家王增如女士代劳。她这样坚持社会主义的信仰,五十年如一日,至于她以前在南京有没有写过《自白书》,在我看来,早就不重要了!
小游暗暗地丟了眼色给我,并指指她的腕表,表示时间快到了。我怏怏地站起来,跟丁玲、陈明握手告辞,互道珍重。临走前,我环视这间设备简朴、大方的客厅,不禁感慨万千。在美国,有的是一字万金的畅销作家。他们的居所豪华如皇宫,而他们的休闲生活,多的是美人醇酒,声色犬马。比起他们来,中国作家的生活实有天渊之别。
如丁玲,她的生活不过可以温饱而已,至于地位不如她的,那更不堪闻问了。然而,他们却严肃而有理想,不但热心创作,还想着报国。一波又一波的文艺整风,外加十年“文革”,不知道剥夺了多少作家的生命与理想。人生最可悲的,莫过于理想、目标之丧失,名利双收的海明威落到举枪自戕,川端康成切腹自杀,或许就是悲于茫茫人海中无所适从吧!丁玲却挺过来了,犹如开在悬崖峭壁的一朵野百合花,冷艳清芬。
丁玲谈话的率直,人如其文,使我印象深刻。比起1976年许芥昱会见沈从文的拘束与做作,我显然是幸运多了。沈从文是许芥昱大学时代的老师,他先是拒绝许芥昱到他家拜访,而宁愿自己搭公车去旅馆看他。而见面后,他滔滔不绝地谈他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一直回避有关写作的话题。当许芥昱提醒他过去写作的辉煌成就时,他只说了句:“那是过去的时代了。现在小说要求的内容不同,我写不出来。”凡此种种,不外是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生活的真相和他内心真正的感受。
那时在归途中,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夜已经深了,北京六月的晚风拂在身上,带来一丝凉意。司机先生正播放着邓丽君的录音带,有板有眼地跟着哼唱“何日君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