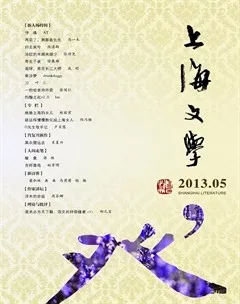吉祥隐地
这几年,每当我兴致勃勃地和人谈起米积山天龙寺,人们总是疑惑地询问它在哪里,勤奋点的上网去查,也会把杭州的天龙寺误以为是它。
宣统年间《临安县志》早就记载:米积山,治西南二十五里,梁昭明修禅岩下,石罅中日撒米升余,足以自给。
近代的《玲珑山志》讲得更详细些,说米积山顶古有寺庙,香火旺,山后岩洞会自动出米,米量不多不少,正够当日香客吃。某年当家和尚郝兴起了贪心,想多得些米,高价卖到山下,便用铁器将出米口凿大,结果适得其反,从此洞里一粒米也不流出了。
此庙就是天龙寺。山因米积洞而得名,寺又以什么而得名呢?没人提起。只知道山并不高,海拔仅四百零七米,行政上属临安玲珑街道管理。
米积山吉祥,不待我说,但喻它为隐地,是我说。首先没有多少驴友知道它。就是临安人也未必全知,我们自驾车去,都到玲珑街道了,还有不少被问者一脸的茫然。听说去年春天,一个老板请一位搞摄影的朋友考察一下米积山的自然资源,那人登山后失声叫道:天哪!我哪里还需要打飞的去丽江采风,摄影天堂就在家门口啊!从此米积山成为了浙山浙水摄影创作基地。当地人尚且如此,更别说外地人了,比如一位杭州居士,又是做记者的,年年云游,号称全国有名的寺院全部跑遍,江浙两省的寺院更不用说了,偏偏就不知道此山此寺,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如果有这样一座寺院,怎么临安的居士都不知道?!
我有几个上海朋友,自从去了一次米积山,从此便念念不忘,有的一年要跑数次。此山究竟有什么这样吸引人呢?我国山水美的地方多了去了,说穿了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妙和尚。写到这儿容易让人想起那个可笑的绕舌故事:“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老和尚说‘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老和尚说,山上有座庙……’”在听故事的年龄,这样的故事真让人抓狂。可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妙和尚,他也会讲故事,但他的故事找不到出处,又非原创,大至宇宙本元,小至鱼虾的命运,有时把听者的历史也说进去了,深奥而有趣,让听者欲罢不能……也许这只是我的偏执,所谓“法无优劣,契机者妙”,小庙之美好,非静心耐心以及机缘不得收获。这也许是我认为隐地的另一个原因。
别人得到什么快乐我不好说,单说我自己无意中得到的收获,就很有意思,在十几年时间的流逝中,从初见端倪,到发现一些轨迹,点点滴滴的事物,它们竟有着隐秘的联系。独自享受太浪费了,拿出部分欣悦与大家分享比较心安。
先说十五年前的那次天目山游,我们来到了昭明下院,看到供奉的韦驮菩萨塑像非常俊美,当地百姓说是十八岁的儿郎相。据说昭明太子是韦驮菩萨的化身,塑像就是按昭明太子的形象塑造的。这位太子归隐山林的情致,以一种文本样式存在于他编辑的《昭明文选》之中,而他向佛的情操,又遗存于山水之间,让我产生了寻觅的兴致。在这之前,我知道今人所见的《金刚经》与昭明太子有关,但不知道三十二品就是在天目山分的。听说由于心血耗尽,他的双眼生瞽失明了,是一位山僧用天目山的两泓泉水治好了他的眼疾。
这不成药水了吗?听说其中一眼水就在山上的昭明上院附近,它清明如镜,不见泉眼,但池中水永不干涸。我和几个亲友决定上山去找这眼泉水,没想到我们在深山中迷失了方向,竟然走到一条布满蜘蛛网的狭隘山道上了,周围竹林遮径,光影斑驳,鸟声婉啭,仿佛入了王维的鹿柴之境,可我们无法欣赏,有的只是一片恐慌,气喘吁吁中,我们大喊:有人吗?
奇迹出现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僧人仿佛应声而现。他相貌堂堂,肤色清纯,人略清瘦,却有着一双粗大的手,他的右手攒着肩上的米袋,左手腾空持着一本书,书是打开的。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他则一边看书一边登高,绑着灰色绑腿的下肢显得轻快利落。这条高低不平的小道不足六十公分宽,有些地方崎岖得简直不能称路,一看就没几个人走,可他每一步落地都非常准确,好像脚底长了眼睛。我们全看呆了,一时疑为天人。当时《西游记》正在全国红红火火地上演,演员的俊逸和淡定可以乱真,却无法模仿这位僧人的气质,他不仅潇洒自在,还有一股自然的庄严相。同行的一个男孩说:他比唐僧还要好看。
这个僧人的法名很奇特,叫“香影”,出生在中医世家。他的声音很轻柔,讲话充满诗意。经他指点我们才知道,我们寻找的方向完全背离了那眼泉水,但是,歪打正着,原先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分经台”就在他的闭关处,正好随他行。
他说和一位老僧已在山上闭关了两年,除了下山买些生活必需品,就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我认识中,垒石为室结茅为庐是古人的修行方式,而当代苦志修行的又多是藏人,没想到汉僧也会猫进深山。
在山林的清幽处突然见到这三间平房有些恍惚,平房周围竟有回廊,木窗结构也具古色,但它显然很旧了,带着沧桑的感觉。它们仿佛突然冒出来似的,这又一次让我想到了正上演的《西游记》。
当中那间平房一分为二,前面客堂间,后面灶火间,左右两间则是寮房。客堂只有一张粗糙的木桌,桌子靠墙处供着一本《金刚经》。他微笑着让我上香,于是我第一次不是向佛像而是向经书奉上了一支清香。
一位老僧正在门前浇地,他手持长柄木勺从露天大缸里舀水,白花花的水,亮晶晶的抛物线,瞬间菜田润绿一片。缸边有块破损的石碑,内容我忘了,只记得是块古碑,时间久远。老僧脸有苍色,袈裟打着好几块补丁,像一个贫寒的老农。我们向他双手合十,他微笑着点头致意,非常质朴。
昭明太子的伏案处“分经台”就在菜田的小径旁,很普通的样子。山石长约一米多,宽半米见方,厚大概十厘米,石面较平坦,上面晒着一捧树枝,这是两位僧人的柴火。
香影禅师眼光平常淡然,见我们恭敬地摸这块石头,也禁不住轻叹一声:嗳,不容易啊。
我的一位同行朋友身有疾患,向他请教如何调身,他说:世人光知道滋补,不知道泄露,若不先行排毒,反而补了邪气。他当场赐予朋友一方子。当我谈起体质虚弱浑身是病的母亲,他轻轻念了几声佛,虽然没赐什么秘方,仍是让我得到慰藉。
香影法师虽然令人亲近,但又透着一种类似于清高孤傲的气息,也许说他有自己的原则更恰当些,比如严守教内相关的戒律不与女子合影,不接受居士同住的请求,不欠人情债等。
多年后我才知道,香影法师是位有修证的高僧,经常被全国其他寺院请去开示《金刚经》。当时虽然不知道这些,却能在他营造的轻松氛围中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
临走时,我蹲下来摸灶间地上的一截老松树疙瘩,真没想到松明子还能长得这么大。香影法师说,这是我们当榔头用的,你喜欢就送给你。油润发亮的大圆疙瘩酷似金刚力士手持的神锤,我如获珍宝,并深感幸运。
没想到神奇的缘分还在后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回娘家看母亲,见她精神少有的好,我还没说行程呢,她先惊悸地告诉我:前几天做了个梦,梦见一座深山,山里石头上出来两个男人,好像没穿衣服,给我一碗绿莹莹的菜汤,好像是药草,吃了很舒服,不好意思将脏碗还人家,就四下找水,结果发现附近有两摊浅水,我这里舀一点,那里舀一点,才把碗洗干净了,这时他们又贴到山壁上了,才看清他们穿衣服的,衣服上一条条纹路,像佛教人士穿的衣服。他们大概是和尚吧?
香影法师为我母亲念佛的情景浮现上来,惊喜之余便是感恩,修行人的神通是建立在慈悲众生的情怀上的啊!
隔年,我和女儿去杭州游玩,返沪时买的车票没有座位,因为不是始发站。过道中站了不少人,偏偏一位年轻僧人边上空着两个位置。我们问询后便坐了下去。
僧人是个小个子,眼睛清亮,肤色干干净净,长相、气质都像小姑娘,但观点却直截了当,没有丝毫的冗余部分,然为了我能理解,不时地运用一些义理比喻,有很深的穿透力,鬼不知神不觉的,让人忘记辈份的差距。一路上,我们交谈甚欢。有些我过去不得解的思索,他竟能三言两语地破解。通过交谈我得知,他是个云游僧,居无定所,这次是去上海参拜圆明讲堂的。我们彼此留了电话,用他的话来说,互相交流心得。
大概半年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声调很熟悉,我突口而出:香影法师,你好啊。
谁知对方说,我不是香影法师,你怎么认识他的?香影法师是我的师父。天下真小啊。他常年闭关,并不见人,你能见到他也是缘分。
这一说我分辨出细微的不同来,香影法师声调柔和悠长,然所说却简明扼要,而他正相反,语调轻快敏捷,所说却像回文体,正看竖看全得意趣。原来他就是火车上邂逅的年轻僧人啊。
通过几次电话后,他告诉我,经过各地的参访,他对大乘意趣了然于心,决心选一佳地实修。后来他得一梦谕,寻觅后确准是米积山天龙寺旧址。我不知道他在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如何走到了今天,只知道作为主持,天龙寺依然条件艰苦。但电话中他的声音却透着无限的幸甚:这真是一处吉祥之地啊,你能时时感受到观自在。
他的话并不为过,最近我看到有人撰文,说佛陀曾授记,米积山是十轮金刚王出世的地方,那里有过去金寂佛与饮光佛之舍利秘密伏藏。凡俗如我者除了要靠信心相信外,真不知以什么去印证这些传说,但可以亲自前往领略那里的风光,去过了,想忘记都难。
自火车上认识米积山天龙寺僧,一别就是整整十年,终于一行五人开着越野车去了米积山。这是第一次去,正是初春时节,那些粗大的竹子像巨烛一样遍布山岭,竹梢在微风中如同燃烧着绿色的火焰,满山坡的毛笋、竹笋悄无声息地萌动,各种各样的山花先后绽放,紫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色彩艳丽,香气缭绕。然而天龙寺却很简陋,一座圆通殿,供着千手观音,侧面一大间平房,厨房兼饭堂还兼客房,同时供着一尊笑口弥勒,对面是主持住的平房,矮小潦草,等同于棚子。没有电灯,几个杭州来的义工凑在蜡烛前读经。上山的路也没修好,山石砂砾硌脚,下雨天又泥泞得没法走。然而这位年轻的主持毫不在意,依然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作各种交谈。这样的年纪,却有一颗少见的婆婆心,为了让你明白某一道理,会反复举证,批评起人来却毫不客气。记得说起《六祖坛经》,他说道:你读出精髓了吗?你能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收获吗?我来教你如何保守六根门,这就是一切与你不相干,包括你自己。当时我喜悦非常,那感觉尤如醍醐灌顶。朋友们也个个眼眸清亮神情轻快,在上海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情状。山风清凉爽朗,如同慧言散发出的怡人气息。当我们身边窜过去一条四脚蛇时,这位僧人还像孩子一样笑起来:多好看啊,像药师佛,宝蓝色的。
说起他的师父香影法师,这位年轻山僧充满了敬意和爱戴,他说师父是个真正的修行人,不追逐名利,随缘自在。他的赞叹让我相信传承的力量,我想所谓的衣钵实质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接力棒。
他明显变了,个子超过了我,标标准准的小伙子了,不再是我印象中的女孩子相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眸里有神光转动,身上透着隐隐的金刚力。我突然意识到十年前的印象,那时他才十八岁呀,难怪我会误以为他长得像女孩子呢。在火车上,我怎么会想到他的智慧已经超越了这个年龄段呢?看来,智慧不但与文字无关,也与岁数无关。
听说最初山上无饮用水,要下山去挑,那时山路没修好,为了节省时间,他们走的是古山道,那是一条直上直下的小径,三十多公分宽,现在几乎被灌木杂草遮蔽了。我和朋友走过一次,没行几步,朋友的脚已抖得迈不开了。想想在这样的小路上担水是多么的困难。后来一场观音法会,出现许多瑞兆,当晚空中有光,山壁上冒出水来。当地人都说是观音菩萨解难,赐予不竭的甘露水。那水清澈微甜,口感纯正,现在天龙寺饮用全靠它。我们每次去都要掬一捧喝,走时还要装上几瓶回家。有一个朋友用甘露水养金鱼,说鱼的颜色也变好看了,并且不像过去,需要频繁换水。
在我心里,米积山和天龙寺是一回事,它们是浑然一体的。而米积山又是西天目余脉,仿佛时光空间的延伸,在即将截断消失的时候,我猛然醒悟,赶紧赶紧,不要错过。后来各种机缘,我又去过几次,那里一次比一次好,虽然进展缓慢,通上电了,寺院便也有了稳定的光照;山路也修好了,方便私家车开上去,爱走山路的人脚底也是爽快。我就走过一次,路两旁的风景真是美丽,空气新鲜得没法说,真正的幽香四起。新造的总持王殿也非常精美,精美得好像脱离了天龙寺整体的简陋风格,但反差之大并不突兀,反而提人精神,因为在总持王殿的后门,一铺石阶直上山顶的圆通殿,看上去幽深而又神秘。台阶连接了两殿,一头是华美精致,一头是简朴端庄,混然一体不分你我,如同佛门的应机说法。作为当今的现代化速度,天龙寺的发展还是缓慢,但是,山脉的气势天然而成,不需要人工变动,站在古画般的山崖旁,眼前就是一片活着的水墨画,你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世上竟有如此静美的山谷。晨曦雾波缥缈,细微的水分子轻拂脸容,感到皮肤润泽得如同花草,云海汹涌时,好像涌到脚下,人就仿佛随着山岭抬起来,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实地拍出来的米积山照片,外人看起来,就像作过艺术处理一样。
看到这位年轻的主持就会想起只有一面之交的香影法师,也会想起他说过的话:我有个不好的习气,喜欢闭关,过清闲的日子才自在。这位不愿跑闹市却爱荒山野岭的法师最终还是被浙江“佛协”请出山了。我在网上查找过他主持的寺院,同类的论坛热热闹闹,他的寺院却一片静寂,三言两语的地理介绍,肃默的习禅课堂,如同他闭关修定的身影。看到这样的画面,我耳边响起的却是他柔和而真切的语声,“佛法是活泼泼的,般若智慧如大海般深广啊”。他的这位主持弟子和他不同,虽然每晚于星空下打坐,但从不闭关,各种琐事苦事都应付不完,忙起来经常忘了吃饭。对待来请教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也只是从心性上说法,从不纠缠在事相的是非上,比如他对想做好事又有烦恼心的人说:“有能力了,去帮助别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当能力不足,勉力去做,总是有些不自在。”他又提醒那些救护流浪猫的好心人:“不要仅爱一个种类,要将爱猫的心扩大到所有的生命身上。要清净平等觉。任何偏执的爱都是可怕的。”他还对自负的念佛人说:“邻居有苦恼,你劝他念佛解脱吗?小孩子摔倒了,你去扶持吗?妈妈来电话,你好好说话了吗?光口头念佛算不了什么,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你修行的对境。”如果说,香影法师像一位导师令人敬爱,那么这位年轻主持就像一位智慧的朋友,可以无所顾忌地交心。他们虽然性格不同,接引人的方式不同,但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槛外人都会变得身形端庄,总不能歪脖子斜肩地合十问询吧?我们的衣服也很飘逸,那是恰到好处的山风吹的,而我们的心境更是雅安,个个具有君子淑女相,人都有向往美好的本能。
说到这位香影法师的高徒,我就会想到传承的力量。但没想到的是,天龙寺的法源竟然能追溯到志公禅师身上。作为佛家人,志公禅师非一个“神”字就可以说清,南北朝时梁武帝的国师、十二面观音化身、身上禅、密的双重性,使他成为史上名人。疯疯癫癫的济公故事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还得说到十几年前的那次天目山游,在昭明下院,一位穿百纳衣的老僧送我一本自编的《宝志和尚》油印本,讲的就是志公禅师。油印本纸质粗糙,但画像传神,那是志公的半身像,相貌算得上丑陋,然古面长眉,胡子拉碴,神气间弥散着道气。
我着迷于那本小册子,也由此明白《西游记》中不少玄思妙想的来处,比如居住在树上的乌巢禅师向唐三藏传授《心经》那一章。史料上记载,婴儿时的宝志就是被人从树上的鹰巢里拣来的,这位手足如鹰爪的奇人后来出家到道林寺。他曾经给齐太尉司马殷齐之画了一棵栖有乌鸦的大树,告诉他紧急情况下可以登树。后叛军追击,齐之在林中果见一树,树上有鸟,便躲进鸟巢,鸟竟然不飞,追兵看见树上伸出的鸟头,认为不可能有人,便撤走了。而白居易曾参访过的住在树上的乌巢禅师,竟然法名也是道林,不知是凑巧还是后者要模仿宝志?但神话小说里的乌巢禅师借鉴了历史传说几乎是无疑的了。
记得没多久互联网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我也学会了上网,在网上搜索关于志公禅师的文字,结果找到一篇配有照片的简介,看了不由一怔,那照片竟是清定上人年轻时的照片。我曾拜清定上人为师,看见过这张旧照片。
如果说,清定上人被人误当作志公禅师使我莫名的开心外,听到天龙寺的首任主持本源长老就是志公禅师时我真的惊喜了,过去我一直以为治昭明太子眼疾的是个无名的山僧,原来他就是志公禅师,再一想也合情合理,既然昭明太子在米积山坐禅,有分身本事的志公禅师到这里来帮助弟子也是顺理成章。现在,米积山的出米洞依然在,传说中的米不复见,只留一片高高低低的插香。出米洞不远处是一高崖,崖上有一山石,石面赫然一个“米”字,天然显现。据说当年昭明太子就在上面打坐。现在的主持也经常在上面打坐。因此,我们去到那里,也会一本正经地盘腿拍照留念。
在高崖西侧,有一小殿,里面供着三尊塑像,除了昭明太子、地藏菩萨,还有一位名“五通和尚”, 这三位并列受供的设置极其罕见,我心下总是生疑。据天龙寺的人说,他是本寺的和尚,神通了得,比如开法会米饭不够时,他能把山下他人锅中的米饭从空中移来。听到这个传说,我不由发笑,难怪是五通而不是六通,佛门中人怎么能犯偷盗戒呢?但一想便释然,如果这位和尚修到漏尽通了,就是得道圣者了。一个肉身和尚,难道能像佛陀一样要求他吗?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有了个新的猜想,没准这位五通和尚就是志公和尚吧?他的异迹确实表明已证得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可惜没有《天龙寺志》一类的文字记载,否则寻觅史迹会方便得多。
比起国内一些大寺名寺来,天龙寺的规模实在不值得一提,但与最初的赤贫比,还是值得一说,尤其是总持王殿,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漂亮的拱穹,艳阳的色彩,高大的空间,而是里面的珍贵塑像和不一般的法物。两侧高座上的十二药叉散发着好闻的香樟木气味,香气如药。正中的雕塑更是令人咂舌,它是一尊乌木观音,整棵树雕成,高四点八米,底座更为珍贵,是金丝楠木。香案也是一整块金丝楠木,长有五米,非常厚实。据说,此珍贵木材长了两千年,之后又在金沙江里埋了一千四百年。被有缘人打捞后又被有缘人收藏,最终到了观音足下。乌木与金丝楠木的珍贵世人皆知,而它们竟然进入这样一座小寺,不称奇也不行。更奇异的是人们无意中发现,从卫星上拍摄的米积山形竟然与观音足下的底座造型一模一样。卫星拍摄非常客观,而制作者并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从卫星上看下来的米积山是什么形状呢?酷似龙形。而天龙寺在米积山的位置正在“龙尾”部分。这么说来,寺院名字确有几分道理。可是问题又来了,古人怎么知道米积山是龙形呢?而金丝楠木座的造形又怎么会与米积山形凑巧一致呢?
还有不能解释的是五彩舍利,它们盛放在金丝楠木香案上的水晶舍利塔里,据说它们是寺院诵经时天上降下或直接在供台上生成的。一位住在山上的居士给我看他供的白色舍利,说是天舍利击穿殿堂屋顶降下来的,当时有几十颗,他伸手接到了一颗。也许冥冥之中真有我们所不知的逻辑存在吧?
若不亲见不能妄说,我只能说说自己的一次经历,那是2007年农历二月初九那个清晨,年轻的主持带我们到山上看日出。他说:今天的太阳很吉祥,你们好好看看,它就像你们原本的身心,纯净无染。
于是我也像他一样,安静地看去。这一看惊讶不已,仅仅两秒钟,我们熟悉的太阳就不认识了,它开始变色,先是湖蓝,继而玫红,然后淡黄,纯美的色彩不停地变化,有时几种色块同时出现。太阳四周还出现火焰状,更奇特的是太阳中间的色彩是旋转的,由右向左转,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在虚空界给太阳上色,有时没涂好,边沿突然露出一块空白来,但瞬间又被色彩涂满了。
那些色彩完全是活的啊!难道我们进入了童话世界?我反复证明自己,没做梦呀!
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我们恋恋不舍地下山,回头看,彩色的太阳依然如动画片一样。有几个人吃完了早饭正站在山坡下闲聊,当得知了我们所见时,他们半是惊讶半是埋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
这位年轻的主持说:你们看啊,太阳一直在天上,就像你们一颗清净的心,它一直在,自在自在,就是你自己一直在啊,你到什么地方去找?!
于是又多了一群目瞪口呆的人,他们看得如痴如醉,看得如入梦里。《金刚经》云: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确实如梦如幻啊,这是释迦牟尼指出的物性真相,这真相又是如此的清晰。无中生有,奇幻的太阳,奇幻的心性。
在米积山,在天龙寺,我们领略了人生洒脱自在的本地风光。而那位年轻主持的法名,让我想起来就会微笑,它的读音有穿越时空的幽默感。而我所接触到的这一切,都仿佛在戏说。
一切吉祥本在吾心,只是隐藏太深,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么,烦劳忧愁之际,去米积山轻快地走一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