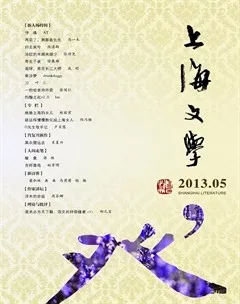暖意
我在不远处
那年回乡,是为了叔叔家的琴琴。
母亲告诉我,你就在不远处悄悄看看,她是不是让人放心?
故乡的天,总是亮得很早。
十七岁的琴琴,给小亮的瓶里灌满热水,装进书包,小亮六岁不到,上学紧紧拉着哥哥衣角。大亮不开心就故意放快脚步,害小亮在后面东倒 西歪。
琴琴站在院边桃树下,望着两个弟弟渐渐走出她的视线。阳光很好,她似乎有些开心。或许是因为,又一个暗夜过去了。
转身回屋,洗过碗,把一些剩饭渣兑了刷锅水,倒进鸡盆。打开鸡窝,六只鸡争先恐后叫着挤出来,顾不得在新鲜空气里打一声鸣,便冲向它们的食物。尘土扬了琴琴一腿,她像大娘一样骂:没出息的东西们!
柜子桌子擦得光亮,琴琴洗把脸,梳头照镜子时,忍不住笑了一下。那酒窝,像极了妈妈。
大娘还在家里忙碌,大爷还未从地里回来,琴琴快走两步,顺小路爬上屋后的山坡。
草都青了,露水也差不多落完了。琴琴坐下来,太阳暖烘烘晒过来,小院尽收眼底,自家的鸡已经和大娘家的混在一起。那只没出息的黑公鸡又在满院追大娘家的红母鸡。大部分鸡都坡上坡下开始觅食,只有那只最瘦的花鸡还在盆里一粒粒捡拾着最后的残食。
昨晚,大娘拿过琴琴正织的毛衣说,手有些紧。琴琴觉得也是,因为针都有些拨不动了。她沿着昨天的痕迹一点点继续。新买的线,蓝得在阳光下闪眼。琴琴没听大娘的话,拆掉爸爸的旧毛衣,而是给大亮买了新毛线。爸爸妈妈的所有衣物,琴琴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妈妈当初陪嫁来的红漆木箱里。
爸爸妈妈又一次钻进琴琴脆弱的心底,两行泪顺势滚落在青青的草叶上,露水一般晶亮。六个月,仅仅六个月前,爸爸还在;一年前,妈妈也在。然而今天,爸爸妈妈却相聚到了另一个世界,把他们姐弟三人像飘飞的柳絮般丢在这个看不清未来的生活里。
“妈,爸爸?”琴琴无数次在心底喊,忍不住说出来。两个弟弟在,她不敢,在心里使劲,震到嗓子疼。妈走的时候,她哭了一天又一天,爸走的时候,她眼里就没了太多泪。有时她说想妈,有时又说恨妈。她天天祈祷,保佑爸爸把他们三个带大。然而,妈还是把爸爸叫走了。爸爸,顶天立地的男人,真的兑现了当初的诺言,跟他的女人走了。
“把我也带走……”
琴琴说,妈走后第二天,爸就是这么喊,跪在雪地里,歇斯底里,声泪俱下。当时大娘大爷都骂他,乡邻也骂他:“你走了,三个孩子咋办?”
爸爸扑过来,把三个孩子搂在怀里,嘤嘤哭了,把满院人的心都哭碎。琴琴知道,爸爸实在舍不得妈妈,但爸爸更舍不下他们三个。
事实不这样。那个凌晨,爸爸毫无征兆地走了。天亮时分,爸爸已僵硬了,小亮却裹在爸爸臂弯里酣睡。
琴琴拿起毛衣,擦擦眼角。她努力不去想这一切。现在她是姐姐,这个家的老大,必须承担重任。她一直纠结,大亮继续上学,还是去打工?她不想让大亮退学,虽然大亮学习成绩比她差很多,可她已经回家了,大亮怎么可以再退学?妈妈活着的时候,没事就跟大娘叨叨:我们琴琴呀,可不像别人家的女孩早早退学回家;我们琴琴,手一定是白白的、嫩嫩的,像城里女孩;可不能早早结婚,得学个样子出来。
妈妈的姑姑在城里,她每去一次回来,便发一通感慨:“不上学真不行。”
如今,妈妈疼爱的琴琴坐在山坡上,一双嫩嫩的手已显出粗糙。琴琴的成绩单,至今都整洁地压在书包里。那只书包,她会时不时拿出来翻翻。自从退学回家后,她便把墙上的奖状一张张揭下来,擦去尘土仔细叠好放起来。她知道,今后不可能再有新的了,这些旧的,必须存下来留个念想。
如今,墙上空空。大亮从未得过奖状,小亮还小。大娘劝琴琴,让大亮退学打工去,念书不会有什么名堂。要不,地里指望亲戚们东一下西一下,收成不会好。没有来钱的路子,三个人怎么活?
箱子里,爸爸收下的礼钱已经越来越薄。爸爸在信用社还有贷款,数目不算大,可是大爷告诉她,如果不能尽快还上,利滚利怕得惊人。
怎么办?让大亮退学?琴琴喜欢学校,愿意看两个弟弟背着书包离开家,就像妈妈当初看着她背书包离开家一样。她愿意晚上收拾好一切,辅导两个弟弟写作业。听窗外偶过的风吹草动,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笔一画写字做题。翻大亮的书,那些习题和课文,总能让琴琴重回课堂。
“琴琴,该准备买谷籽了。犁完这两遍地,过两天我就出门。”正在沉思的琴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原来是大爷牵着牛从地里回来吃早饭了。大爷说今天犁完自家地,明天给琴琴她们犁。
“大爷明天不用回来了,我给你送饭。”琴琴乖巧地说。
买谷籽要钱。钱,就这样一张张出去了。大娘告诉她,过几天有个亲戚结婚。大娘说,这些事得自己操心,红事白事,哪样都不能落下。看着琴琴为难的样子,大娘说,迎来送往就是人情,爸妈不在了,你们还是一个家,没人会因为你们是孩子,减免这份礼,也不能因为你们是孩子,就不参与这些事。
“以后家里有事,都需要用人。”大娘这话,让琴琴懂了,人情就是这样积攒的。爸妈走后,琴琴和两个弟弟见了谁都觉得像亲人,哪个亲人送来的哪怕一句安慰,都让他们觉得家还没散。
“大娘,以后不管谁家有事,一定记得提醒我。”琴琴郑重叮嘱大娘。
花母鸡用最响亮的嗓门告诉山坡上的琴琴,它下蛋了。四只母鸡很争气,天热的时候,每天至少两颗蛋。
听到鸡叫,琴琴的脸就有些红。她忘不了那个中午,一口气打了十颗鸡蛋炒了,黄灿灿端上桌。小亮惊了,大亮叫了。看到两个弟弟欢呼,琴琴的成就感十足。以往,妈妈总在节日才舍得炒鸡蛋,每次顶多四颗。两兄弟为此争抢挨打,总是常事。
琴琴觉得,鸡蛋是自家的,不用花钱买,怎么总不让他们吃个够?
大娘端着一碗面进来说,“谁家这么吃的?鸡一年下几颗蛋?这一盘,能卖多少钱!”
琴琴对我说,那一刻她才明白,鸡蛋是用来卖钱的。她不是不知道,只是一瞬间脑袋突然就糊涂了,没把鸡蛋和钱联系起来。那一餐或许成了永久纪念。此后,除了过生日、“六一”,琴琴再不轻易给大亮小亮吃鸡蛋。此后的每一颗蛋,琴琴像妈妈在世时一样,埋进米缸,攒够了卖钱。
花母鸡围着小屋扑棱棱飞,墙皮被鸡扑得一片片往下掉。
“修房子,也得用钱。”那晚,琴琴想外出打工,可两个弟弟咋办?家里的鸡、屋子、地,咋办?懂事的大亮看出姐姐的心事。
大亮只有十三岁,可大亮拍着胸脯给琴琴保证,他会挣钱回来。可大亮能干什么?做童工,悄悄跟着工头,搬砖和泥,学着干呗。
这件事,就差琴琴点头了。
许多时候,琴琴在暗夜里问过爸爸,希望爸爸托一个梦,告诉她不犯难的办法。
大娘说,大亮到二十几岁,就要娶妻生子,小亮到镇上读初中高中。上学花钱多,娶妻生子更需要钱,需要房子。可盖房子要多少钱?琴琴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只知道攒这笔钱会很遥远。遥远的事,却不能不想。
她常常问大爷大娘,爸妈在世时,怎样挣钱?卖鸡蛋、卖粮食、挖药材、倒卖袜子,这些琴琴有记忆。那时琴琴在爸爸背回的一麻袋袜子里,挑挑拣拣。她以为一麻袋袜子是爸爸的,如今才知道,爸爸只是背回了袜子,那是别人的。
山坡上,琴琴有一下没一下织着毛衣。她笑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是想到曾经的教室,还是撑起家事重担的自豪?
此刻,小伙子木子来了,抓着一把黄的紫的白的花。
琴琴看了一眼木子,不说话。
木子家的两只羊就在身后吃草。
木子的花是专门给琴琴采的,是有用意的。村里不上学的女孩子们,大多数都在谈恋爱。像琴琴这样大的,好多都有了主。何况,大她五岁的木子对她早有意思。
大娘说,琴琴还没退学的时候,木子在路边等她,给一把酸枣几颗核桃。琴琴不要,木子一直伸着手等她接。琴琴从不接这些东西。
爸爸包括大爷大娘曾经表扬琴琴,不要木子的东西。木子有什么好呢?不读书是大毛病,而琴琴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大人们眼里,琴琴的未来一定在城里。
但是爸走后,大娘常常故意说起木子,木子其实不错,长得也好,没其他坏毛病。木子依然像以前一样对琴琴,有一天大娘挑明说,与木子定下来也好,现这样的情形,指望找什么样的男人?让木子帮助挑起这个家,有什么不好呢?
琴琴心里难受,现实又让她把这事认真放在心上,从心里讲,她并不讨厌木子。以前不理他,是因为他不上学,现在,他们都一样了,很多年甚至一辈子,她可能都留在这个小村里。木子难道不是最好的人?她有时想,如果与木子恋爱,如果与木子结婚,是不是也很好?他忙时种地,闲时外出打工,她照顾家照顾两个弟弟,日子是不是过得和别人家一样好?
可面对木子,琴琴高兴不起来。
大娘在院子边上看到了,望一阵,叹一阵气。大娘说,琴琴心里是阴天。当时,一干女人在麦场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在厕所里的琴琴听到一句话:“她是好姑娘,那两个‘累赘’咋办?一下娶三个,换你们干不干?”
琴琴听得真真的,说这话是木子妈。
木子妈强硬,“木子想娶,就跟她去,回这个家,不能够!”
外面的女人们都知道琴琴在厕所里,知道琴琴能听到。琴琴明白了,女人们一定看到琴琴,才向木子妈提这事,而木子妈声音那么响亮,也是故意的。
琴琴走出厕所,女人们尴尬地打招呼。木子妈,头也不抬。
琴琴回家和大娘哭,“以前她很喜欢跟我说话呀。”
山坡上,羊在远处吃饱了草,慢慢靠近他们。木子拣石块,赶走了羊。琴琴愤愤站起来,离开。
山坡上,木子看着琴琴的背影,蹲下,又起来。
大娘在院子里喊,春天来了,该把衣服拿出来晒晒了。
可琴琴还是没打开家里那只红漆木箱,她知道一翻就会翻出爸和妈。大娘进屋说,以后,箱子里的,包括家里的事都是琴琴的,要亲手把旧的翻过去,新的翻出来。
琴琴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晾在暖哄哄的太阳下。
“中午吃啥?”大娘过来摸摸琴琴妈的衣服,问。
“面条。”琴琴答。
不久,有力的擀面声音,嗵嗵响起。外面,天还是蓝天,太阳还那么暖。鸡群也卡着时间回来觅午饭,琴琴腾出手,抓一把玉米撒出院子。
琴琴的更多心思,必须跌在柴米油盐里。
她没有看见,我一直都在不远处看她。
我不知道,把这些告诉母亲,会不会觉得难过?
故乡的秋夜
车子停在一片玉米地旁。
放眼望去,我认识的树,都老了;老了的房子,依旧在老地方。
下午的人抬起头来。我看了,想寻出一两个熟识,名字似乎已到嘴边,却又失了主语,才知道,二十年流蚀了我的全部记忆。这些陌生人,一定是从前的小孩,现在的成年人,是外面嫁过来的媳妇,是从前的孩子生育的孩子,是从前的熟人,现在衰老了面孔的“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或许更不熟悉我。时间让我们变了模样,让我们极力回忆却还是回不到从前。
有调皮的小孩喊:“去谁家?”
我答应着。就有人问:“可是小小?”
听到名字,挑谷子的女人在我身边盯了一阵,说:“比小时瘦了。”她的头巾上挂了一层薄薄的黄土,让我找回丢失的亲切,想摸一摸。她可是谁的妈,可忘了辈分,不敢妄称,就笑答:“小时候胖。”
她说:“城里人就是不一样,还能嫁一次。”她的话很清澈,是流出来的,我信了,笑了。
婶婶从玉米堆里抬起头来,愣了半天才跳过来夺下我手上的东西:“一个人?”
“孩子跟爸爸出门了。”
“你爸咳嗽轻些?”
“一直吃药。”
“你妈的腰呢?”
“保养着罢。”
婶婶丢下玉米,攥紧我的手,急切地开始了积攒多年的询问,直到远在城里的亲人在她脑中一一清晰,才满足地拍拍手,“晚上吃蒸饺!新磨的红面!”看我惊喜的表情,笑笑说,“没忘吧,小时候一闻到味儿,就骑在门槛上不走。”
往事,暖暖的。
我洗了手,被婶婶推开,“转转去。”
阳光洒满院,晒出阵阵泥土香,空气中弥漫着久违的粮食气息。谁家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清晰入耳。偶然,传来一声狗叫,婴儿啼,温情弥漫在整个村庄。
出门,那个爱打闹爱逗小孩的旧邻叔叔迎面走来,满头白发,身后一个小孩追着他喊爷爷。我小心叫声“叔”,他眼神疑惑,浅浅作答。我没说我是谁,他未敢问我是谁。走出一大截后,才返身盯着婶婶家的院门恍然求证:“可是小小?”
表姐坐在我面前,说自小得病卧床、博览群书的儿子,在一个夜里毫无征兆地离去了。时间过去大半年了,她泪水依旧肆意,顺势裹进她的皱纹里。我惊叹她的苍老。高中时代,她拖着两条美丽的大辫子一路闪耀,她与校长儿子的恋情轰动小镇,她出嫁当天嫩白的肌肤清亮动人。今天,她用粗糙的双手轮番擦着泪,与每一个农家怨妇一般凄凉讲述。尽管还有一子一女,她依然执著地惦记着她的“二小”,那个无声逝去的她情愿付出一生再服侍二十年三十年的“二小”。
去表姑家。她不在。她去城里帮儿子看孩子了。两年不见,照片上的她清晰地衰老着。眼神,神情,稀少的头发,都让我失落。记忆里,是她在小河边将一头秀发浸在水里;上气不接下气跑进院门骄傲地告诉闺蜜,有个男生在后面拚命追;她露着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咬着一只梨在树下爽朗大笑。
时间!一切的一切,全是时间。曾经的好东西,都让时间夺去了。它像个妖魔,悄然从每个人身边走过,粗暴地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内到外掠去人身上的一切,包括记忆。我们可以战胜任何坎坷,唯独无法战胜时间。它要无情流走,一秒钟都不肯停留。你试着哭,试着拉扯,试着哀求,都无用。
好在,故乡的夕阳也如此美好,黄昏极其富有诗意。打谷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嘴里的开心或烦恼。家长里短,就在茶余饭后被一桩桩晒在太阳下,有人疼,有人喜,有人冷眼无语。
东西南北上天入地扯累了,空气在瞬间有些沉闷。对面梁上恰当地传过颤巍巍一声:“吃——饭——”被喊的人,起身嘟囔:“破嗓子”,顺手拍拍前面的背,“回,一会儿又该喊了。”于是,担心被喊的,相继收起烟锅家什起身。那些已经没人喊的,心便沉沉的失落,咀嚼着曾经荡气回肠的那一嗓子,嘴里倔强地嘲笑,“一辈子被管!”
我深信,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我养我的乡村。我与故乡,依旧可以碰撞出那种一擦即燃的火花。味道,如此销魂。
“小小——”脆生生的呼喊响彻多半个村。
“叫你吃饭呢。”许多与我熟识起来的乡人热心提醒着。
回身,望到房檐上翘盼的婶婶,我知道,她的红面蒸饺,熟了。
三大盘原生态蒸饺,冒着热气点燃着我升腾的食欲。城市的饭店,不管怎么吃,都不是眼下这般味道。我知道,除了婶婶的手艺,更多的缘于脚下这片黄土。
天,不觉间在我与婶婶边吃边唠中黑下来。这顿晚饭里,我与婶婶同样收获了大量信息。只是婶婶只能靠躺在被窝里慢慢融化,我却可以立即品味。毫无睡意,起身下炕,换上婶婶的布鞋,出门。
一院的月光,隐约听到邻家电视机里的打斗声。
布鞋,松软的乡村黄土小道,星星月光……我悄然绕过一个又一个屋檐,不会有人知道我心中的惬意。邻家门缝里,清楚地看到鸡入窝后院中的安宁。即便那个白天不听话的孩子在挨打,哭声也是暖的。你看,泪还在,他就端起母亲盛的粥,笑着喝了。
恨,我没有一双可以绘画的手,否则,这幅恬适的安宁,该有多么值得珍藏;恨,这样的画面,是文字所远远不能及的。
谁的一声轻咳?像极了儿时的爷爷。我移开脚步,看他挑着一担谷物经过,听负重的呼吸随沉重却快乐的脚步一同归家。秋天,是乡村男人证明自己的季节。当他肩挑沉甸甸的一担推开院门,他的妻子,早已迎在门边递上热毛巾,捧出晾到正好的茶水;他的儿女,也早已安静地等在桌边,给他敬上筷子,外带一壶烈白。
他的一声许可,孩子们会飞快地挑起一块炒得焦黄的鸡蛋塞进嘴里,哪个,一定会被噎着;哪个,一定会被呛着;还有哪个,一定会被母亲硬生生拍一巴掌。只有他,会在这吵闹嘻笑里乐呵呵醉去,专享他的夜。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实在无法拒绝这样的暖情。我的乡村,我的故土,多少年,多少次,我总会莫名被击中,莫名在这样的想像中澎湃万分。我深信这就是最丰富的人生,最纯真的幸福。
我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思绪,也在这越来越熟悉的情境中回到从前。文字、画面,在我脑中交相辉映,撤掉一幅,又换上一行。
那个夜啊!故乡的秋夜,如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