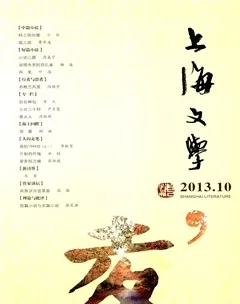挚友程乃珊
认识程乃珊已经三十多年了。
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瞬间,但对有所追求的人来说,常常是取得成功的契机。乃珊在这几十年里,以自己的坦诚、真挚、热情、坚韧,显示出文学创作个性,抓住契机取得了成功。
三十年前和乃珊认识,是从她的处女作开始的。
那是1979年春天,《上海文学》复刊刚两年,被打乱了的编辑工作秩序正在恢复;散失了的作者队伍亟待重新组织;来稿逐日增多,只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所表述内容的犹疑不定。
这时,我们收到了用当时市面上出售的格子很小、天地头狭窄的稿纸抄写的三篇小说,由我们几位老编辑分看。
字写得不规范,稿面也不整洁,题目却很活泼:《在公共汽车上》、《妈妈教唱的歌》、《愉快的聚会》。文字清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但不是英雄人物,只是普通知识分子的优雅生活,相当长时期少有作品反映的,作者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
终审选定了《妈妈教唱的歌》,请作者修改后在1979年7月号上发表了。从此她成了《上海文学》业余作者队伍中的一员,经常参加我们举办的文学活动。
那时,她只是刚刚开始学习文学创作的中学英语教师。在众多的有着深厚文学修养、不满足传统表现方法、追求探索新路的有才华的作者中,乃珊显得有些寂寞。
她一开始写作,就是为了倾吐对她生活其间的那一阶层人的感情。这里有钢琴家、科学家、银行家、企业家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成员。
她的那一社会、知识阶层的人们,在一段时间里,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他们的命运很少被关注。乃珊却理解他们,爱着他们,抑制不住要“写写他们”的激情。
她写了一篇又一篇,默默地写着。有修改意见,改。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
这个编辑部不采用,她寄到另外一个编辑部。
乃珊甘于寂寞,不受外界影响。她想,既然发表了第一篇,为什么不能发表第二篇、第三篇呢?
未想到,她第一篇被文学选刊转载、第一次获奖的小说,竟是发表在《儿童时代》(1980年12月号)上的《欢乐女神的故事》(获1981年儿童文学奖),这对宋庆龄主席创办的儿童刊物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喜欢乃珊作品的读者在增多,关注乃珊作品的编辑在增多,向她约稿的刊物也日益增多。当然,也有不喜欢这类作品的读者,赵钱孙李各有所喜嘛,这很正常。
乃珊写完二十多个短篇小说,手中的笔进入中篇。《蓝屋》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不同凡响,也有争论,她面前不再是静悄悄的了。
《上海文学》编辑部也组织了一次对乃珊等三位上海的青年女作家的作品讨论会。
那次会上,文友们对乃珊作品的长处和不足做出了中肯的分析,也有好心的朋友对她将来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大致意思是,要她走出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的那个圈子,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关心政治关心改革,写得深些,要关注文学新潮流……
乃珊的脸上泛出红晕,她低着头,在自己早准备好的记事本上快捷地记录着。她还来不及领会其中深意,没有点头摇头作出反应,她只是不停地在记。
有人戏谑地称我是乃珊的老师,要我给“学生”提点意见。
我当时从内心讲,很怕她会舍弃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而去跟着大家往金光闪闪色彩斑斓的小门里挤,这无疑是自寻淘汰。我讲不出长篇大论的道理,也不能引经据典做些论证。我只能凭着自己的直感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以为,乃珊作品里反映出了她的二重性。一方面,她深爱着她圈子里的人物,为他们的命运激动,她能准确传神地写出这些人物的心理感情兴趣爱好痛苦欢乐,内涵隽永深刻而耐人回味。另一方面,她又强迫自己去否定、批判她内心并不以为错的一些旧的生活习惯和别的什么,显得相当苍白生硬勉强,甚至不可信。这些是非文学因素造成的,我真诚希望作者以后能忠实于自己的本体意识、艺术感觉,不要掩盖自己的本意……
我曾经在编发乃珊的作品时,私下里也和她讨论过:文明礼貌有什么不好?良好的文明比粗俗无礼要好吧,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什么呢?……
那次的作品讨论会对乃珊有一定的震动。
我再去看她,发现她有些苦恼。她强迫自己去考虑重大题材、社会意义等等方面的问题。
“我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所见所感来写……”她说。
我把自己未在会上说出来的那一段话对她说了。
她点点头。“我也这么想。”
她又开始娓娓地讲述她朋友、熟人的故事,恢复了温柔娴雅从容的神情。
她的朋友熟人很多,常常互相走动。她说,如果不和朋友来往,就写不出东西。
这次她讲的是一位过去开过服装工厂老板的发家史,对照了今天称之为企业家的情况,她说得很具体很生动,仿佛研究过企业管理知识又做过社会调查的行家。
我听得津津有味,也由此联想到我们不大理解的一些现状……
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收获》(1985年第6期)上的中篇小说《风流人物》的人物原型。
每次见面,她都滔滔地给我讲她熟人的故事。她说话又快又响,富有节奏和乐感,让我听得入神。
“我只能写我熟悉的人物。”她两眼溢动真挚热情的光,“每次我的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写得很像他们。听了这些话我也很高兴,我愿意把他们都写进作品里。”
乃珊继续走自己寂寞的路,没有往另一扇门里去挤。她的《签证》、《银行家》相继发表了。
不管她主观愿望如何,她的这些作品都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我作为乃珊的责任编辑,为她创作上的这一大步而高兴。可是也免不了有些遗憾。
我苦笑了一下,“乃珊,我退休了,不能在我离开终身所从事的编辑岗位之前,最后发你一篇小说,真有些不甘心。”想到过去要推出她作品的不易,如今她知名度高了,作品分量也在加重,而我却不能再作一次她的责任编辑,心中也有些戚然。
她突然走到我面前,一脸真诚,镜片后面流动的目光变得晶莹灼人,“彭老师,我给你赶写一篇。”
我牵动了嘴角。
“真的,”她急切地说,“我写一篇小说作为送给你的礼物。”
我的眼眶湿润了,说不出一句话来。
无论她的许诺能否兑现,都足以使我感到安慰了。
她又给我讲出了一位熟人,她中学数学老师的故事。“我很想写写他,真的。你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和几十年前完全不能比了……”她无限感慨、惋惜。
乃珊问我,最后的交稿期是什么时候。
我向她交了底,末了又补充一句,“乃珊你不要赶时间,什么时候写完交给我都可以。”
乃珊还是为我赶写出来了一个小中篇。一口气写完,很多地方剪剪贴贴还来不及誊清。数学老师在文中出现了,但主要不是写这位数学老师。这就是发表在《上海文学》1989年7月号上的《祝你生日快乐》。
几十年过去了,我实在无法把白血病和乃珊联系在一起。她在我面前一直是那么开朗、快乐、充满活力。白皙细嫩的娃娃脸,浓黑的童花头,亲切的笑容,讲不完的过去现在亲朋好友的故事,悦耳的语音,快捷的叙述,和她在一起总是那么快活。
我退休前,和乃珊一起参加了浙江江山文联举办的文学活动。我俩住在一室。晚饭后,我们走到街上买了两节红皮甘蔗,一人手握一根,在初春的晚风中边走边吃,回到住处,手中的塑料袋里已装满甘蔗渣,两人大大享受了一次无拘无束的疯吃。那一夜我们讲了大半夜话,主要是她讲,我听:讲她的婚姻、她的朋友、她的困惑,那么坦诚。虽然我们属于两个年龄段的人,但我能理解她说的一切。我也向她讲述了我朋友的故事,她有写不完的素材啊。
不久,她去了香港。她和我通信中讲到生活的变化:忙、累。她说,发现自己离开了老严(她的丈夫)还是挺能干的。我知道,在上海时全靠老严对她生活上的照顾,衣食住行样样安排得很周到。稿件发出、稿费收入也全由老严打理,不用她费心。
正好我到香港探亲,乃珊利用周末假日,邀请我和她一起喝早茶。其实是十点开始的自助餐,我们呆了两三个小时,把一天的卡路里一并吃了。这就是她在香港的生活,平日里工作很忙,她独自一人挑起刊物采编的担子,还要负责摄影配图,还在好几份报纸上开了专栏,在上下班的轮渡上写稿子,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只有在每个周末去大饭店休息休息,大饱一次口福,自己不必做饭了。
她让我看到了她的能干。
乃珊喜欢香港,也适应了香港的生活。但她告诉我,香港好比是婚外恋,是没有结果的。
老严也说,乃珊还是会回来的。
果然,乃珊回来了。我又有了和她欢聚的机会。虽然我早已离开编辑岗位,成为了社会贤达(闲人),她却一直和我很热络。
乃珊带回了更多活力,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不再排斥“小资情调”,而要求更加深入认识上海。乃珊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老上海的生活,她从小就发现上海是一个传奇层出的城市,她对上海的了解太深了,写起上海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等相继出版,这些生动精致地反映了上海世态人情和弄堂生活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排在畅销的行列。
乃珊写作之余,仍不忘和朋友聚谈,旧朋新友、文化金融、白领蓝领,她的生活圈子更大了,她曾邀我参加过不同行业对象的聚会,由于她的关系,让我和已经恢复公民身份的老友徐景贤有了来往。
最后一次聚会,是乃珊为老严庆祝七十岁生日。那天,著名作家、音乐家白桦、陈钢夫妇也都参加了。平日聚会,都是老严忙进忙出。这天,乃珊穿了一身红色旗袍连衣裙,略施脂粉,喜气洋洋地招待朋友,这是乃珊真挚地表达对爱人的感激之情。老严被深深感动了,他说这一辈子只做过两次生日,一次是二十岁时母亲为他做的,现在七十岁由乃珊为他做……我联系二十多年前在江山乃珊对我说过的故事,更加感受到了乃珊的善良真诚。
和谐温馨的家庭需要夫妻俩共同筑建,乃珊不是只会索取享受而不知付出的人。
就是这么一位充满活力、文思泉涌的人,怎么会突然患病呢?!不愿相信!我不断去电话,无人接听,只有留言。
总算有了回音。悦耳欢快的声音,乃珊病情稳定了,她正在写家史。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真高兴。
在晚报上,在我们刊物上都看得到她的文章,行云流水般,一点没有病痛的痕迹。
谁知又突然断了电话联系。我正在纠结,4月23日的早新闻中传出了乃珊辞世的噩耗。我的泪水溢出眼眶……
怎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有病,我衰老,腿不能行,手无力拎,不能到龙华为她送行。
总不能不告而别!
我由人推着轮椅到乃珊家中,在遗像前送上一篮洁白的鲜花。乃珊走好!
看到老严消瘦的面容、失神的眼,我说,老严,你尽力了,太累了,别太难过。
老严哽咽着告诉我,她在病中,还写了十几万字……他知道我一直关注乃珊的创作。
乃珊从1979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处女作开始,一直不断和刊物的联系。直到去世前最后一篇文章、她的绝笔也是刊发在《上海文学》上,她真是《上海文学》的挚友。而她的这些文稿都是由老严亲自送到编辑部的。
我不禁想起乃珊说过,她这一生做对了两件事:选对了事业,嫁对了郎。
确实如此,老严给了她无私的爱,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亲自护理,寸步不离。
乃珊手中的笔直到停止呼吸才完全放下,给社会,给读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乃珊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