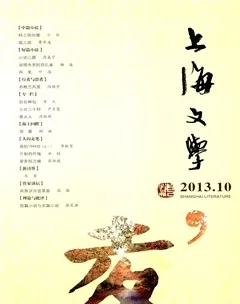邻居
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的房子是我住过最久的房子。我出生以后就住在那里,中间去过别处,回来又住在那里,直到二十七岁。那是被称作“新式里弄”的房子,“新村”、“新式”是在解放前叫的,相对的“旧式”是石库门,三层楼,一楼二楼是我们家的,一楼前门有个小院子,但我们还是管它叫天井,鲁迅写“门外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种了一株桃花”的,就是那样的房子。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房子,因为他住9号,我们家是19号,他的后门正对我家前门。参观鲁迅故居的人走到一楼半拐弯处的时候,必定会从那里的窗口朝我们家看一眼:那块泥地上种着一棵枇杷树,长到三层楼高,因为三楼邻居说妨碍了他们晒被子锯掉了不少。还有一棵桂花也是一直在的,是我奶奶种的。除了枇杷和桂花,别的就不一定了,看你是什么时候参观鲁迅故居的。上世纪80年代时有几棵月季,我和我的表姐穿着织锦缎小袄、头上装着假的鬏鬏和辫子、手里拿着团扇,在花丛中像戏曲里的小姐那样拍照。直到继母住进来以前东南角都有竹子,后来她说虫多,“连蛇都有也说不定!”把竹子连同爬满红砖房子的爬山虎一并清除了。1991年泥地边缘有一排韭菜莲,是我从中学里采的籽种出来的,很好长,夜开花也很好长,长在里圈,两个一起拚命长了很多。有挺长一段时间,废弃的原来浴室里的老铸铁兽爪脚浴缸靠东墙放着,里面还一度养过许多金鱼。在夜里,一缸水变得幽黑深邃,金鱼高高低低停着不动,鳞片在倒映水中的星星之间闪着清冷的光,西边的天空下高耸着千爱里{1}的水杉的黑影。有过葡萄,埋过一只死兔,葡萄因而又大又甜。那年枇杷也结得很多,我爸爸站在天井里赶吃枇杷的鸟。今年他则在抓芋艿叶子上的蟊虫。还有参观者一眼不会看到的东西,比如紫角叶、虎耳草,还有玻璃鱼缸里胀满像美杜沙之首一样盘曲缠绕的仙人指,以及一只盘踞在桂花下面的长寿的大蟾蜍。每年春雷隐隐滚过,我们冒出“那只癞蛤蟆大概不在了吧?”的念头时,就会听到它“咯呱咯呱”地鸣叫起来,许多年都是这样。它的声音听上去总让我觉得有种怡然自得而又遗世独立的感觉。它是怎么来到这个天井的呢?它应该也不会出去了吧。外面都是水泥地,没有地方可去,不再会有别的蛤蟆会来这里,它也不可能留下后代。像是这世界上只有它一个蛤蟆,真是孤独。比我年长的桂花从来也没有开过,今年居然开了——想来是枇杷树修剪了很多,使它得到光照的缘故,只有稀小的几星白花,香满了一院子,我发现了这件事就想:那只癞蛤蟆大概不在了吧?又想:不知道去年夏天火灾的时候它在不在,在的话有没有逃跑,会不会火灾正是它所期盼的——它修炼了那么多年,得到机缘火解登仙了?又想出四句:桂花老又犟,闷闷数十年,忽而发奇想,噗嗤开出来。再想,它说不定是因为蛤蟆死了才开心一笑的。
总之,四尺见方的泥地加上屋门到院门之间一块水泥地以及另一边一尺宽四尺长的一条窄泥地,还是可以容纳比一株桃花多很多的东西的。除了院子里的景象,二楼房间里的事物也是能看得很清楚的。我家二楼乏善可陈,陈旧的西式老家具围满一圈,中间还堆满东西,尽是大塑料储物箱和挂满深色衣物的简易落地衣架,不是一个会令任何人产生一点向往的画面。黑色的铁院门年久锈烂,豁开一大角,野猫出入方便,我爸爸也懒得管,后来公家出钱换了新的,不知是不是因为就在参观者眼皮底下,被认为有碍观瞻的缘故。从一楼到二楼只有那么一个窗口,又是一个楼梯的停顿,是免不了要朝那外面看一眼的。
我在上下楼经过我家的那个窗口时,总要往外看一眼,最自然地就会看到29号人家天井、院门和二楼屋里的样子。以前不知道茅盾曾住在那里,最近挂了牌子才知道,里面一直住着普通的居民。有两年时间,茅盾要去找鲁迅,或者反过来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要是能从19号直接穿过去不必绕路就好了”吗?那时19号还不是我们家的。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带着在重庆出生的我爸爸回到上海,才住到山阴路上的。
晚上看那一眼时我总是怀着紧张的心情,因为听我爸爸说过他从前在那窗口见到过29号门边有一个没有人的人形黑影。
29号住的人,我完全没有印象,印象深刻的是那里养过的一只长毛白猫,它常常待在窗台上,有一副尊贵的仪态。别的邻居说:“那是只波斯猫。”“波斯猫”是他们唯一知道的有别于寻常家猫的猫,在他们看来,“波斯猫”是一种高级的猫,显然比寻常家猫要来得稀罕,适宜被当作宠物,而普通猫则不过是能灭鼠的家畜,老房子里老鼠多,弄堂里许多人家都养猫,像过去我奶奶养猫一样,都是随它出门玩耍游逛,不加约束,因此邻居又说:“那只白猫他们不让它出门的,连天井也不曾踏足,每个星期都要洗澡,所以雪雪白的。”
我养的是普通的猫,从北京带回上海,住在山阴路,我有工夫看着它的时候就会让它出去玩,因为天井一带有树有鸟,有高有低,是与它相配的乐园。它胆子不大,心也不野,不会跑远。20号在天井里砌了水泥小屋,顶铺的是青瓦,我的猫很喜欢去那上面睡觉,盖着枇杷树荫,我很喜欢看它在那上面睡觉,金灿灿的一团,有鸟飞舞在枇杷树间,吱吱喳喳,它就醒过来瞪大眼睛看,眼睛比宝石还亮。它也会端端正正地坐在屋顶边,认真地看20号人家养在笼子里的鸟,一动也不动,结果看得太久,把小鸟看死了。我觉得它非常美丽,尽管我从不给它洗澡,它的皮毛也蓬松柔软,光滑得沾不上灰尘,爪子、胸脯、肚子、鼻子也雪雪白的。
我继母非常怕猫,我猜与其说怕可能还怀着厌恶吧,我带着我的猫住在山阴路时她就离家出走了。
后来我搬到外面自己住,有天回来看望我爸爸,见到29号门口摩托车上有一只白猫,很脏,长毛一绺一绺缠结在一起,看见我们就叫。我爸爸说:“这就是原来29号里养的那只猫呀。他们搬走了,它就一直在这里。”拿了猫粮给它吃,它就狼吞虎咽。他说他们搬走第二天还有人回来过,大约是拿别的遗漏了的东西,撞见他,就问他怎么不把猫带走,他颇尴尬,说想要带走的可是带不走、抱走自己又跳下车云云,不想多说,仓皇离去。我问:“当时那只猫呢?”我爸爸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说:“没碰到他吗?”我爸爸说:“没看见呀。那人很快走掉了。”之后那只白猫就待在29号门口,我爸爸和20号的邻居可怜它,看到它就给它东西吃。尽管如此它的样子还是每况愈下,越来越凄惨,又瘦又脏,与此同时天气也在变冷。我继母已经住回来了,我爸爸也不能让它到家里来。到了冬天,它就不见了。
后来我想,它一直在那里,为什么那人回来时它不在呢?那个人为了非拿不可的东西硬着头皮回来,心里觉得很麻烦,也庆幸它不在吧,拿好急着走,生怕碰到。其实不必那么慌张的。它躲避起来不见,是不愿逼你难堪之下又当着面说出更厉害的谎来遗弃自己吧,那样就不堪得跟直接死去没什么两样了。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但也许那人走得匆忙只是因为事务繁忙,也不想和无关紧要的人闲聊,并没有把猫放在心上,既不顾忌,也不羞愧。
我的猫后来也不准出去玩了。它的脚在天井里受了伤,我怕它腿脚不那么好,走墙上房时再有闪失。它去外面哪里钻一钻,就染上一身虱子。一只得了瘟病的小野猫还来我家天井草丛里拉肚子。这些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我发现邻居当中可能有用汽枪射猫的人:在给猫翻找虱子时,我见过一块黄豆大小、很平整、边缘清晰的圆形皮肤上面没有毛,随后20号的邻居说他们家的猫被汽枪打了,我问怎么知道是汽枪呢?他们说身上有个小圆洞流血,一看就是汽枪打的,我就想到了我的猫身上那一处——是汽枪打的吗?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每天跟它睡在一起,愈合以前怎么没发现呢?会有子弹在里面吗?越想越恼恨心疼,不禁到天井里骂了一句:“下流胚!”也不知该冲着什么方向骂。
总而言之,几年里,因为长大、伤病、人的恶意,还有我的缘故,猫的世界逐渐内缩,我因此对它怀着歉疚,可是我的世界也一样,被猫推动的人生拐入了另一条轨迹,我上了班,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欠了银行一大笔债,不敢辞职,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工作上,很多事无法打算,可以扯平了吧?我们的活动由世界退缩、撤下,犹如河水退下石滩,带着卷来的碎屑和记忆的残影淤积在一个很小的水洼里,周围一片干涸。我们寄居在这狭小的容身之地终日相伴,并不感到不耐烦、想要突破逃走,可以持久稳定地处在这个状态里,我跟人就做不到这样。
至于用枪射猫的人,可能是18号一楼的青年,听说他有一把汽枪。从上大学开始算,我有八九年没在山阴路生活了,跟我年龄相仿的邻居小孩都已长成了陌生的成年人。我们不像我们的长辈那样来往,互相全无了解。只有偶尔在弄堂里看到一两眼的印象,是个一脸怨怼、谁也不看、平视前方的人。
唐卫德的儿子也是个奇怪的青年,他和他数十年吵闹不休的父母一同住在20号三楼,他甚至不如18号的青年在街坊心里有一个名字。他们用“唐卫德的儿子”称呼他。实际上他们几乎不会提到他。他长得像他母亲,矮短敦圆,被唐卫德揍时,哀号声也和他母亲一样尖厉而气长,几乎分不出谁是谁。他在弄堂里出现时并没有委屈忧戚的神色,反而常带着一种看起来好像是得意、轻蔑、若有所思的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看到的唐卫德也总是有着很谦和的笑容,头发花白,很短,戴个眼镜,显得斯文客气。“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复旦大学的呢。”我爸爸说。他比我爸爸小几岁,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进的大学,他们小时候还一起在虹口公园挖过硫磺片玩。“做啥要这样啦?”我爸爸也跟他说过。他说:“我没打伊,碰也没碰,伊就在那里叫呀!”如今的邻居之间,大概不会开口问这样的问题。
大陆新村的地板都是木头的,楼上的人走动,如果脚步不是像我奶奶那样轻,在楼下就会听见。去年夏天我家一楼由于雨天墙内有水引起老化的电线短路而在半夜失火,我爸爸和继母在二楼睡觉,幸亏被烟呛醒逃了出来,我爸爸逃出来以前还干了一件非常危险又有用的事情,就是冲进一楼用力推倒了烧着的顶到天花板的书橱,使得尽管一楼烧成一个焦窟,但火没有烧到二楼,天花板如果烧穿了,大概就完蛋了。不过我还是宁可他直接跑出去。我回家帮忙,消防员浇的水和东西的灰烬和在一起,踩上去肥腻厚软,我爸爸的麦草种子撒落在地,在焦泥上面发出芽来,一簇簇绿苗生意盎然,我感觉就像是踩在我尸体化作的沃土上,看到人全都不在了,万物哼着歌复兴,覆盖我们的痕迹。天花板烧得露出了一片焦了的木头的泥墁条,大约宽五厘米,密密排齐钉在横梁下,仿佛房子像只受重伤的兽,露出它的骨头,而它仍站着不倒,我在它五脏俱焚的腔膛里仰视它,以目光轻轻触碰了一下它的骨头。梁没有烧到,梁上面是二楼的地板,泥墁条用纸筋水泥墁上,外面再搪一层石灰,就是一楼的天花板了。过去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隔在我和楼上的人之间的是怎样的构造和质地。
不过我知道墙。上初中时有一阵子,继母的女儿到周末会来与我同睡一张床,她睡里边,我睡外边,她总会在半夜做噩梦,又哭又叫,拳打脚踢,蹬烂了墙。我把手指放进坏掉的墙里摸一摸,就像摸一个伤口,墙也不哼,石灰掺稻草,土黄色,再里面是空的,敲一敲听得出来,也许因为是隔出亭子间的墙,不是承重墙,夜里有时墙里有一个很细小的滴水声,滴得很快,老鼠在墙里奔跑、磨牙、变老、眼睛变瞎、胡须变白,敲墙也无法使它们停下。“房子会被啃坍的吧,”少年时的我躺在床上想,“真是个酥脆的房子。”
在这样的房子里,邻居看不到唐卫德有没有揍他老婆,但十天半个月就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唐卫德的话毫无实际内容,只是不厌其烦地一味重复同一句最脏的脏话,他老婆则一直放声尖嚎,仿佛在说:“即使你这么恨我,我的气也是不会断的。”东西摔在地板上很响。可是唐卫德的儿子是在场的,他在那儿,没发出声音,他在干什么呢?在我的想像里,我看见他默默地将脚尖插入一个他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物色到的地板缝隙,接着另一只脚,然后就挤了进去,又红又黑、粗糙柔软的胖脸最后没入地板,像仰泳的人将脸埋进水里,找到一个舒服的躺着的姿势,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唐卫德夫妇每天出门四五次在别人家门口翻拣垃圾时很难不被人看到。被看到时,唐卫德也抬起脸来和人笑笑,很客气。他的老婆则会有一点闪躲鬼祟,她看上去脑子不太灵,面孔惊惶又迟钝。唐卫德过去是高桥炼油厂(现在属于中石化)的,他老婆在房管所上班,两个人的退休工资不少,所以我想寒悭大概不是对他们爱捡东西回家最好的解释。也许他们每天捡很多东西回去是为了填塞他们之间的空隙,就像那儿有一道这里那里随时要被水冲开的坝,必须不停地修补加固它。也许他们一个要保持身体干燥,另一个要住在水里,保持一定的水位,一道坝开裂渗水,一个人就飞快地用他们捡来的废弃物另筑起一道。当坝又彻底溃塌时,他们就陷入水、干涸、沮丧和愤怒里,发作一通,之后又鼓起劲来,出门去捡更多东西,如此凄楚而顽固地度日。也许他们也从中收集一些纪念品,像喜欢将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带回巢穴的鸟。有一回我继母洗了一个老石臼和捣杵一起放在后门口晾着,捣杵是一根木棒插在一颗网球大的石球里,没多久就发现那颗石球没了,木棒和石臼都还在,我爸爸和她就在门口说:“咦怎么石球没了呢?好奇怪,是被谁拔下来拿走的吧,但是要那东西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唐卫德就带着那颗石球来了,说不好意思,是他老婆拿的,以为没人要了。她要那颗球干什么呢?路过中药铺,她也会把手伸进石狮子嘴里,把它含着的球拿走吗?在他们家里,藏品们被标上记号、按照某个秩序排列归纳了吗?
抬头仰望,唐卫德家的屋顶露台上杂花野树未经打理,恣意丛生,挤得满满的,盛也盛不下,堆出露台来,蓬勃葳蕤,像半空中塞着一个小树林,是一幅奇景。可是楼下的珍珍阿姨就不喜欢。一天有个花盆掉下来,砸在一楼天井里,珍珍阿姨就不肯还,要留作证据,找居委会投诉希望他们能管一管三楼影响他人的囤积行为,结果唐卫德的老婆从弄堂翻墙进去偷那个花盆,又被珍珍阿姨看到。珍珍阿姨说,堆积如山的垃圾使得蟑螂横生,多得往楼下爬,有一回她和二楼租户在楼道里喷洒药水,尔后清理了五十只蟑螂尸体。她的丈夫毛毛叔叔是唐卫德的堂弟,但他们是两家人。就像我爸爸和他的亲弟弟妹妹们一样,尽管他们有时会一起吃一顿饭。
他们很可能有囤积症。两个人都有囤积症,不知道算幸或不幸,是因此能彼此理解、相互怜恤、志同道合,心也在被杂物侵占后留下的寸尺之隅紧紧挤在一起,还是抢夺空间的战争会因为杂物增长速度翻了一倍而比伴侣中只有一方囤积的情况更加激烈。他们的轻手轻脚及惊惶紧张或是常年在堆积如山垒到屋顶的废物间穿行的结果,废物犹如立在狭道两旁的海水,如果他们谁言行失当,狂涛巨浪就会从上方盖下来将他们淹埋。
除了厨余,我们真的能每天丢出来这么多东西吗?是些什么呢?我每天能丢些什么呢?丢着这样的东西的人是怎样生活着的呢?人活着的消耗可真大啊。怎样才能减少一点消耗呢?“‘你为何抱着不放?’‘你为何任意乱抛?’”{2}人真是值得哀怜。
我从不会和人争吵,也没有和家人以外的人长时间一起生活过,在一段关系里我与人的交往往往是缺乏沟通的,我无法顺利地表达,于是对方浑然无所知。对于人为何要争吵,人为何整天争吵却不分开,我也略知一二,大约人在一起生活都要争吵,想和别人一起生活的人都会争吵,他们为了要在一起生活,积极主动,就算争吵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才能跟另一个人生活得下去。
但“整天吵架的人会一直吵下去也分不开”也不见得,我爸爸就和我妈妈分开了。我爸爸和我继母也争吵,但是就没分开。这取决于时机,人当时有多少行动力(经济和年纪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这几年我爸爸和我继母不吵了,感情变得挺好的,大概年纪大了,到最后人和人都会变好的。
我现住的住处窗户对面,住着可供我观察的一对爱吵架的男女,我坐在对着窗的写字桌前,正前方不到二十来米远是他们饭厅的窗子,窗帘就像戏台两侧的幕布,晚上从不合上,他们在白灯光下的活动全都展现在我眼前,我不想打照面,拉着帘子,但他们的对话没遮没拦的听得很清楚,女人的嗓音尤其清脆嘹亮,吐字清晰,男人话音沉闷,二人都是东北口音,说是吵架,其实基本上都是女人在叨闹不休,男人没那么多话说,就像我爸爸的情形一样。女人没吵架的时候,兴之所致会放声歌唱,唱那种高亢的晚会歌曲,像《我的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什么的,唱得不赖,一句唱不满意还会反复起头唱这一句,让我觉得她可能在文工团之类的地方待过。她平常说话声调措词也都有种戏剧性,譬如在十一点过后很安静的夜里,她突然夸张而“幽幽”地(能大声传到我耳朵里的“幽幽”)叹了一口气:“唉——”提醒了我的注意,继而字正腔圆、诗朗诵那样慢地朗声道:“爱情真可怕!”我听了就在我这里笑了。
他们是好客的夫妻,晚上常有人在家里一起吃饭喝酒,女人叫他们“二哥”、“三哥”什么的,不像亲戚,像义气之交。喝得大家嗓门都大了,女人对客人说:“来,我们来唱歌。”我心里说:“不要啊。”女人随即就连唱带说:“烽烟滚滚——唱——烽烟滚滚唱英雄——”对方并没跟着一起唱,她锲而不舍:“烽烟滚滚——预备——起——烽烟滚滚——来,唱——烽烟滚滚唱英雄——”努力带动了好多遍,没成功最后就自己唱了下去:“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着实是个热情积极的人。
到人走了,夜阑人静时,忽然女人的脆亮嗓子响起来,像打碎一个瓷盘,又白又尖:“有你什么事啊?你打算送到哪儿啊?不回来不是更好吗?你跟她回去呗。”先前的客人里大概有个女的。男的只会说:“你有完没完?”或者:“别过分!”好像她再没完他真会揍她或者离家出走,其实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关灯到后面去睡觉了,仿佛今天的戏顺利演完了,大家都很满意似的。
她是他再娶的老婆(“你女儿”是她常常吵闹的题目),他当初是个移情别恋的男子(“我是小三,我又是小三又是老大,怎么着?”),看如今她如此泼辣、他沉默被动,猜想他离婚跟她在一起大概也是她激烈争取的结果,否则可能只是偷情了事、风波一场。他们之间没有孩子(“不是因为你没钱养才不生吗?现在我没儿子可稀罕,你倒稀罕你女儿,你是不是想跟她们团聚呀?”)。她的不满总是与“钱”和“她”有关,约摸八二的比例。有一天她又在为钱吵闹,你借给哥嫂多少钱,给前妻女儿多少钱,一一算计,在我听来觉得是撕破了脸的吵法,面目太难看,实在也好不起来了,这个男的也忍无可忍,动了真怒火说:“别过了呀,我这就走。”接下来女的立刻说:“可我这么爱你!你走了我活不下去!”直听得我心里起一大哄。心想,我果然没有这样和人生活下去的本领啊。这个男人,大概也无法离开这样以撕掉脸皮的赤裸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女人吧。
又有一天,我走在小区里,突然听见这个女人的熟悉的声音,一看是她在路上打电话。我第一次看清她的样子,发现我因为她清脆的嗓音、苗条的身材、充沛的激情而低估了她的年纪,她的脸已经老了,修着细弯眉,涂大红口红,腿细细长长,就像那种文工团里待过、既有组织气、又有风流浪漫劲儿的女子。我目送她走进自家楼门,正是最靠里一栋。
我听见人们在我周围活动,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一对老人总是把他们的老家具搬到走廊上、我的门口——因为那儿地方稍微大一点——敲那些松脱的榫头或者钉子,他们自己的关节也在吱呀作响,摇摇欲散。我能听出那不是许瑞珠和她的男朋友在欢爱。她刚搬来时,总在午夜发出非常奔放、无拘无束的呻吟和叫喊,从晚夏大敞的窗口跃入密集地住在一起的居民之间的寂静,他们一会儿上床,一会儿赤脚踩在床边,动作之多之大,配得上所有“颠鸾倒凤”之类的词语,当她男朋友一边叫喊一边撞我床头挨着的墙时,我忍不住用力敲墙。我猜想是我有天坐在我床上大声地给我妈妈打的一个长电话让他们最终发现了隔音是如此之差,他们忽然不再大声喊叫,似乎改变了床的位置,并把行事的时间从午夜改到了清晨。许瑞珠家里的灯的开关大概是三个并在一起的,她住到现在也不知道哪个开关对应哪个灯,她开灯时常是连着啪五声,按到第三个她要开的灯才亮再把前两个关掉。开关不总是响五声,有时只有一声,我就在心里祝贺她一下。她总是穿着带跟的皮鞋在家里走来走去,要不然就是光着脚咚咚咚地走。她很怕冷,秋天很早就开始开空调,有毛病的空调外机的响声像一只铁鸡在瓦楞铝皮雨篷上打摆子。我曾经想难道她听不见自己空调的噪音吗?不过,也许那对她来说就像枕头上的猫在耳畔大声咕噜之于我一样是她不以为扰、而能带来安心欢喜的声音,也未可知。
我屋子西侧的墙那边,是从另一号门洞上楼的住户,从来也不会见面。我入住前装修工人曾经不小心把墙砸穿了,只有一块砖头的厚度,一块砖头从那边顶出去,对面的学生正在吃饭,因为是租客,很好说话,把墙补好就没事了。学生之后的租客在阳台外面的竹竿上晾晒像足球队员穿的那种鲜艳荧光色训练马甲。他们的动静,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后来有两三个月,到了晚上七点左右,就会响起有节奏的敲墙声。这个声音从来也没有在别的时间响起过。于是我就想,大概二人或其中之一是下班后赶来此地偷情,之后还要回自己家去的。他们的关系没能维持很久。
我听见有人在窗口拍被子和棉拖鞋,楼下的狗被关在阳台上用力地撞铁门。狗是白色的土狗,主人是一对母女,那个女儿年纪不大,总是穿着睡衣和她的母亲、一群阿姨、几个爷叔一起坐在楼底下,白天傍晚,长年如此。他们散去后,空地上的椅子保留着他们这一天的姿势,但没有闲聊的内容留下来。有时天晴,有时还在下雨,鞭炮突然炸响,我的猫吓得逃进床底,此外一个人的声音也没有,没有嫁娶乔迁,没人看,一个男人在放,有一串红,也有高升,他默默地放完就走了。他大概很喜欢放鞭炮。如此寂寥。
即使独自一人寡静地生活,也能被人听见。许瑞珠搬来之前住着的那个青年,每天早出晚归地上班,每晚十点多洗澡——热水器轰地响起,淋浴的水声听上去有种老实的感觉,他十一点关掉大灯准备睡觉——墙上的开关啪的一声,衣服洗得很勤快,他总在晚上洗衣服,洗衣机隆隆作响,比起空调外机的噪音并不算讨厌,但还是会干扰我,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它结束。
我替他收过一本货到付款的书,他不在家,那个送货员常给我送书,就找我帮他收,隔着塑料袋能看到那是本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教材,但我没注意他的名字。相隔没几天,他来敲门,他忘了带钥匙,想从我家阳台爬过去。我因为房间太乱不想被人看见,就说太危险了,劝他还是去找个开锁的人来。过了一会儿我出门上班,看见开锁的人在对付门锁,他坐在旁边地上,穿着黑色长西裤、短袖白衬衫,戴黑框眼镜,黑皮鞋,抱着一个黑公文包,瘦削端正,满头是汗,就像想要努力应付生活但是还是焦头烂额、快要溃败下来的样子。这时他的房东已经告诉我他要把房子卖掉的消息了,于是这位邻居不得不搬走,再去找别的房子租,我不肯为他行方便,又害他花钱找人开锁,过意不去,就跟他说了几句话才走。他不喜欢夏天,夏天使他狼狈不堪,他说到冬天就好了,他在冬天会神清气爽。他一开始并没有很想跟我多说话,后来却像在孤独的湖底梦游忽醒,呛到了水几乎要溺死,伸手抓住一根稻草似的想要向我寻求帮助。
我们一直往西走,这里的货车在码头混迹久了,连喇叭声也变得和汽笛一样。途中犹如幻影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飞机的尾翼像一面巨帆从楼群之后滑过。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他说没有。我们继续朝前走,看到的飞机越来越多,可是先前所见的飞机太低太大,还是令我百思不解,最后我们发现了飞机的栖息地。
傍晚,许多大飞机的庞大身躯擦着树梢掠过头顶,犹如白鲸游过,腹部饱满皎白,虽然速度很快,有些灰色的斑点仍历历可见。第一次在它的正下方那么近看见它时,它挟卷着令人情不自禁一阵恐惧的气势俯冲而来,又漠然离开远去,宛若谜一样的远古巨兽。河边有一蓬一蓬的小飞虫。让我想起很多年以前的一天,在莫斯科城北的一条河边也有这样一蓬蓬的小飞虫。你不得不突破它们的包围,而遇到它们的时候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月亮又小又亮。朝它走了一会儿,它竟真的大了一点。我的前邻居很久没和人打交道了,表现出康复者的生疏感,我并不这样,是因为我本一直在孤独里怡然自得,想借由我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并不是个好的选择。
后来我一个人去看飞机,飞机一只接着一只从北方飞来,飞过河,停在南岸觅食、休憩、整理羽翼,有时交配。如果是下午去到河边,则看到的起飞离去的飞机更多,还能看到它们有的身体下方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生殖器。离开的飞机比降落的显得要小很多,这与它们的飞行轨迹有关,飞走时离得比较远,看起来也就飞得比较慢,有时像只是悬浮在空中,没犹豫好要不要掉下来。另外有一种小飞机,之前我以为它也只是远所以看起来小,又或者揣测它是幼年的飞机,但其实它的确是另一亚种。
有人推摩托车从河边小路迎面过来,在前大灯的光束里惊诧地看到,小飞虫不止是一蓬一蓬的,那是连绵烂漫不可计数的一整条毛茸茸的银河,泱泱兮,芸芸兮,你就在这条银河中走着,当摩托车过去以后,这条河就隐匿不见了,只有旁边那条河泛着粼粼波光。
① 一条旧式里弄的名字。
② 《神曲·地狱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