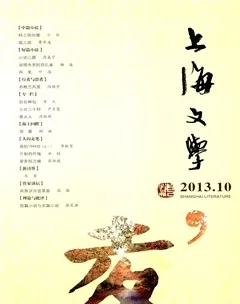看火人
大学毕业后,我在美国联邦储蓄所波士顿分行工作,我的顶头老板乔万尼是分行主管宏观经济政策的副主席。当别人得知我的工作,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中国人也能去美国央行工作?”接下来的反应就是:“美联储到底是干什么的?”两年工作下来,我多次想要回答我所理解的美联储和美国货币政策,却惶恐驾驭不了这样宏大的问题。在巨大的政策机器之中,我不过是看到其中一隅的井底之蛙。而这小小的一隅,我也并不是毫无偏见地去看到的,我的老板乔万尼,他的为人处事,他的思考方式,深深影响了我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理解。
我第一次见到乔万尼是在大四的秋天。那时我刚刚经历了一阵郁郁寡欢的投行实习,拿着几张全职华尔街工作的录取信,却幡然醒悟我永远不会喜欢这一行,而大学前三年我所有的职业准备都在金融上,从没考虑过其他出路。我醒悟得太晚了,开始疯狂出席那些我从未考虑过的职业介绍会:科技、教育、非盈利机构。这时有一个好心的朋友问我对宏观经济有没有兴趣,我说当然有兴趣,那个秋天我对一切非金融业都充满了外行的好奇。这位朋友因为自己对宏观经济的兴趣,曾经找过波士顿美联储的工作,于是推荐我给乔万尼写信。我向这位陌生的经济学家去信,那封啰唆的信与其表明了我对美联储工作的兴趣,不如说是表明了我对华尔街的恐惧。乔万尼回信了,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见面谈谈。几周之后,我在波士顿美联储的研究部见到了乔万尼。我穿着西服套装高跟鞋,走进了一个像极了图书馆的楼层,乔万尼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他穿着T恤牛仔裤,赤脚,一个微笑的意大利男人。
那个面试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乔万尼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而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和我解释他的工作,面试的最后他便告诉我我被录取了。我晕晕乎乎地和他出了办公室,他提议不如去周围随便吃一顿午饭。另一个经济学家曾问我们去吃了什么,他说意大利面,于是她很快地报出一个名字,“一定是去那家!”我讶异她料事如神,她却笑道,那是当然,整个波士顿,乔万尼只对那家意大利店还看得上眼。于是,我们去了这家“全市唯一可吃”的意大利饭馆,各自点了碗面。乔万尼一言不发,默默吃着,安宁而松弛。吃罢午饭我们在一座跨海的小桥上走了走,九月的初秋,阳光灿烂,海鸥在桥上飞。搬到波士顿后,我才恍悟这样美好的天气只是晚春和初秋的短短几周,而代价却是漫长寒冷的冬季。可是在那座漂亮的小桥上,我抬头看看临海的办公室,心想我会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份工作。
于是,毕业后我每天到这栋临海的办公室工作。面对美国国徽,经过金属探测器和持枪警卫的安检,上到九楼,气氛突然一变:没有西装革履,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这里更像个大学,有图书馆,有资料室,午餐时间常有大学教授来介绍自己的研究,而他们的听众一边嚼三明治一边提问题。这样的反差恰好说明了美联储研究部工作的性质:一个自由的学术机构,却位于森严的保密和官僚制度的核心。
我是在非常时期加入美联储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在五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到: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使美联储一改往日保守稳定的姿态,被迫主动出击。不过,我还是先讲讲我的老板乔万尼,一个绝非典型的宏观经济学家。
乔万尼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小镇伊夫雷亚(Ivrea),这座古老的小镇如今以每年二月的“扔橙子大战”闻名。成千上万的小镇居民和游客组成九支队伍,在狂欢气氛的三天中,向敌队大扔橙子。相比那些刻意强调禁欲的民族文化,大概只有这种提供了某个宣泄渠道的文化才能养育出真正平衡和谐的子民——正如永远好脾气的乔万尼。他在故乡呆到高中毕业,然后进入了米兰的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读经济学本科。乔万尼告诉我,经济系在学校里不是个大系,他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他只是更加不喜欢大学的其他专业——其他专业,当然指的是博科尼闻名世界的商学院。
他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然后来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他之前从未到过美国,心怀忐忑地去咨询当时在普林斯顿做教授的一位老乡,教授老乡说:你一定会适应普林斯顿的,这里和咱们老家一个样!一个样,指的是安详的小镇气氛,还有同样对橙子的热爱。我笑称他不过是从“一个橙子镇搬到了另一个橙子镇”:普林斯顿(Princeton)的字面意思是“王子城”,而此中的“王子”指的便是荷兰执政奥兰治(Prince of Orange),也即光荣革命后继承英国王位的威廉三世。于是,这座向奥兰治致敬的小镇的代表色,理所当然就是鲜艳的橙色,正如乔万尼的故乡伊夫雷亚。在普林斯顿的五年,博士生乔万尼的日子不丰足但十分幸福。他和青梅竹马的故乡女友结了婚,住在一间校园小公寓里。学业之外,他们花很多时间骑车、看电影、听音乐会。
巧合的是,当时普林斯顿的经济系主任,正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也是乔万尼的宏观经济课老师。乔万尼毕业后即加入波士顿美联储,不久后伯南克教授就被任命为美联储的常任委员,继而成为主席。学生时代的乔万尼记得的是一个安静温柔的伯南克教授,一个沉思寡言的学者——这些词也可以用来精确地描述乔万尼,也许老师的性格作风真的影响了博士生乔万尼。和许多一天跑几十个回归分析、热衷制造图表的经济学家不同,乔万尼从不病急乱投医。他会坐在办公室凝思苦想大半天,然后让我做一两个尝试,他看着屏幕上的结果,一言不发,再踱回办公室沉思半天。正是这样沉静的性情,他所负责的分析报告常常比那些急于求成的经济学家更有说服力,而所有的同事都会留心他用平淡甚至有些谦卑的语气提出的批评意见。
在波士顿美联储的研究部共有几十个拥有博士学历的经济学家,乔万尼是其中主管宏观经济政策的副主席,直接参与每次FOMC会议的分行准备会议(FOMC会议,即“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是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决策机制),也经常作为分行行长的副手赴华盛顿出席FOMC会议,可谓身担重任。可是,因为我经历的那一次过于随和古怪的面试,我对乔万尼的第一印象是挑剔的品味和自由的作风,更像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正式开始工作,我经常看见他一个可颂面包一杯咖啡就打发了午饭,因为“食堂没什么可吃的”,他也常常跟我交流他对波士顿“还算可以”的餐馆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市内一家昂贵的日式餐厅,人均消费两百美元,他只淡淡评论了一句,“那家店的番茄不错。”我心念,“你们意大利人就知道吃番茄”,之后攒够了钱去体验了一把,果真那家日料店里最惊心动魄的亮点便是番茄,那浑然天成又出乎意料的口感,简直让人觉得前半辈子所吃的一定都不是番茄。他会专程赶到纽约去看莫迪里阿尼的专题画展,看维斯孔蒂的电影回顾展,并把这些称作是“平凡的趣味”。在办公室里,他能随便到穿T恤牛仔裤赤脚,可是要是一时兴起或者逢到正式场合,那几身挺刮的米兰西装肯定绝尘于其他同事。
去年,乔万尼偶然得知我对世界银行的工作感兴趣,就主动说要给他在世行工作的一个本科老同学写信推荐我去做暑假实习。我问他,老同学现在在世行职位很高吗?他顿了顿,因为回忆而微笑起来,他说,嗯,她这样的性格应该在哪里都会很成功的吧。
我们等待着这位事业有成的老同学的回复。一个月,两个月……那两个月他经常一脸歉意地走到我面前说,“太对不起了,她还没回复。”两个月之后,他又再写了一封信给老同学。几天之后终于收到了一封短札,潦草地说,如果你的手下想申请世行的实习,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申请。
乔万尼把这句短短的回复从意大利文翻成英文告诉我。我们很失望,可是更加失望的恐怕是他,我从未见过他那么无奈的表情。他反复说,她从前不是这样的,我很抱歉。那样的劝说与其是在安慰我,不如说是安慰他自己。我点点头,明白人心随着岁月是多么容易发生这类变化:一个曾经好胜但亲切的姑娘,那种“在哪里都会很成功的”好胜的人,却又是让人回忆起来会禁不住微笑的亲切的人,沿着官僚的阶梯越爬越高,渐渐失去了亲切,只剩下好胜和势利。
乔万尼恰恰是他老同学的反面。他是那样亲切,简直让人担心这么和善的人如何去做一个领导。工作不久,我便意识到我所经历的招聘过程远非正常。正式招聘在两月份,比我自作主张联系乔万尼的时候晚了大半年。其他经济学家也偶有收到大学生的应聘问讯,一般都直接转发给人事,慢慢走程序,不像乔万尼那样亲力亲为。一位女同事生了孩子,他便提议整层办公室都装上幼儿防护装置,方便她边带孩子边上班。我申请工作签证时因为一条繁琐的法律程序而受阻,乔万尼居然毫无城府地说,“别着急,顶多我加薪重新聘你。”有一回我顺口提到自己对写作有兴趣,乔万尼便说,“你要不要更加宽松的工作日程,方便你写作?”他正是那么希望把人情味传递到这个制度森严的政府机构,即使做了领导还在任何人面前都毫无架子,以至于某段时间他愁眉苦脸地被逼去一对一的“领导补习班”,教他如何“管人”,就算那样他还是装不出一点领导派头。其实,别说领导派头,他说话的语气实在谦卑得过分,敬语谦词不断。即使对我这个小兵,他也这样说话:“对不起,你现在在忙吗?如果你不忙,我能请你做一件事吗?”
于是,他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一定会再道歉一次:“太对不起了,又是这么麻烦的事情要你帮忙。”然后开始解释我的任务:找出最近几十年的个人收入和失业数据,看看某一次意外裁员是否对未来收入有持续影响;读这几篇论文,整理最近几十年美联储发布声明的具体时间,然后观察当天的市场走向;模拟某个正在讨论中的国会议案对经济的影响;分析几十年内每个季度通胀率从第一次公布一直到第八次公布的全部数据;根据某个指定模型,计算核心CPI的一次小波动对GDP增长的冲击响应……
数据、模型、分析……这就是我工作的主体,也几乎是乔万尼工作的主体。当然,最终一切会变成报告和演讲,会显得概括而感性,可是,即使资历如乔万尼,也必须对各类数据和数学模型有详细而透彻的了解。在美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其实应该被理解为“宏观经济学的工程师”。对于工程师来说,材料(数据)是重要的,图纸(模型)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是,当材料和图纸结合在一起,它能不能真的造出一幢结实的建筑,也就是当数据填入模型中时,得出的结果能不能解释现在的经济情况,能不能有效预测未来。
如果沿用“工程师”这个比喻,过去两年我的工作让我深深体验到,美联储的宏观经济学家,毋宁是工程师中运气最差的一种。我们面对的是糟糕的材料和(也许更加)糟糕的图纸,两者的糟糕程度在短期内不可能改进,在施工期间不管是材料还是图纸都会因各类不可控因素而增改删减,而人们却指望我们用这些东西造出坚固的房子。我们的材料,说到底,就是各式各样的“时间序列”:譬如,几十年的GDP,几十年的失业率。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大部分序列都是季度甚至是年度的,所以总长度很短;许多数据的定义在历史上经历了重大改变;各类误差导致了宏观数据几乎总不会是微观数据的总和。除掉这些缺陷,雪上加霜的是,越是新的数据越是不牢靠,一个新发布的数据只是大约估值,要经过好几个季度的修改才真正稳定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材料:几十个可怜的数据点,最近的几个都不牢靠,以至于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数据所确切描绘的经济图景还停留在两年前,而我们却得使用某种奇妙的魔法来预测一两年后的经济走势。
而我们所使用的“奇妙的魔法”,也就是宏观经济学模型。在七八十年代,人们会用更加乐观积极的语气来谈论这些“奇妙的魔法”。那时候,一些简单而优雅的模型的确曾点燃过解释经济金融现实的希望,比如:解释失业率和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的贝弗里奇曲线、解释定价和风险之间的关系的CAPM模型……在他们刚刚提出的几年中,这些经典模型的确得到了数据上的验证。然而,时过境迁,经典模型大多不再能解释现在的美国经济。然而,正如所有其他学科,这些经典模型及它们背后的思想带动了之后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在巨人的肩膀上”,大部分后世的经济学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评估。那么,如果巨人的肩膀塌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便是央行工作的宏观经济学家面临的难题。多年来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公理”的东西,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都受到了严峻考验:经济增长了,当然就会有新工作——可是,美国GDP早在2009年中期就走出了负增长,而失业率却至今仍居高不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几个月前,乔万尼曾让我利用最新数据去检验一篇2009年的论文,我们得出了与论文相反的结果,于是我们查看了这篇论文所基于的2005年的另一篇论文,最新的数据仍然得出了相反结论……寻头溯源,我们回到了那篇著名的1970年论文,然后发现最新的数据也已经不支持这一篇元老级论文中的重要观点。那么,我们不得不问,难道是1970年论文所基于的假设错了吗?两条看似最基本最合理的假设:人对未来有理性的预期;人厌恶不必要的风险。——难道为了解释今天的经济情况,我们连这些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假设都必须放弃吗?放弃了这些奠基石,宏观经济学何去何从呢?
乔万尼会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美联储的工作需要的是工程师的智慧:如果图纸画错了,工程师还得硬着头皮继续把房子造下去。于是,乔万尼的工作,说到底,是将就和妥协。无论是已经被奉为经典的模型,还是这几年炙手可热的新秀,都需要进行改造才能利用到宏观预测的实战之中。把几种模型混合在一起,看看能否捣鼓出一个最适合描述现在情况的临时模板,即使这意味着每个月每个季度,我们都要不厌其烦地把旧账翻出来,仔细审查之前的所有改动再进一步修改,“缝缝补补又一年”。也许这样的捣鼓修改会被批评为“操纵”模型“操纵”数据,可是其实稍了解计量学的人都知道,在灵敏的回归方程里,想要“操纵”一个结果是多么容易呀;多少看起来坚挺的结果只要稍稍改个形式就能千差万别。在乔万尼看来,真正重要的是模型背后的思想。只要我们没有背离这种思想,那么对模型的修改再造也不会让我们失去经济学的立场。如何做一个经济学的工程师而不背离经济学立场,这便是乔万尼的热情所在,在这一点上,过于亲切过于艺术感的乔万尼是个百分百的经济学家。
我曾有一个难忘的同事叫理查,在他身上能加上一连串形容词,古怪滑稽愤世嫉俗天才书呆子。他常常会在午餐中,从诙谐的笑话大王突然变成大放厥词的愤青,批评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我们这些“小孩”中,他是经济学的绝对专家,任何经济学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讲上很久。我工作的第二年,理查申请到了经济学博士项目,我问他什么时候走,他用那种惯有的玩世不恭说,“走哪去?”
“去学校呀。”
“我不去学校。”
“那你去哪里?”
“去山上呆着。”
“在山上干嘛?”
“演戏。”
“一个人演戏?”
“嗯,独角戏。”
“剧本呢?”
“喏,这就是剧本。”他指指我手中正在读的一篇经济学论文。
我乐了,“这种论文都可以成剧本?”
“当然啦。随便哪篇,张嘴就来。”
于是理查拿过我正在看的论文,随便翻了一页,开始大声朗读。
那一小段来自于著名经济学家詹姆士·斯托克(James Stock)和马克·华生(Mark Watson)在2012年撰写的一篇论文。我无法不注意到,与之前我所读过的这篇论文的一个早期版本相比,这个段落已经删掉了重要的最后一句总结,“换言之,经济恢复而就业率不增长将成为常态。”(In other words, jobless recoveries will be the norm.)
为什么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作者把这个有力的结尾删去了呢?因为它过于悲观,过于坦率,它越过了经济学家的工作范畴,而指出了他们无法改变的根本问题。也许理查是对的,经济学论文真的可以当作剧本来念,它的戏剧性在于既念出文本的意义,也念出那些经过深思而隐藏起来的“弦外之音”。在一篇优秀的宏观经济论文中所蕴含的忧虑是如此丰富而深重,他们跟随着许多公式、模型、数据……显得言之凿凿。
我沉默下来,我们每天煞费苦心的工作,试图预言几个季度之后的世界,试图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前就未雨绸缪。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在“美国人口本身的变化”——人们活得更长了,男女更平等了,也就是说,在这些巨大的历史车轮面前,我们只是螳臂挡车。
在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偶然在一节社会学课程的课堂访谈上见到了一位女看火人。这位姑娘深爱着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为了实现小说中所呈现的澄澈心境,她大学毕业后去蒙大拿州的山区成了看火人。她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每天透过窗户观察森林有无突发野火。她的职责是不断给总部报告野火的进展,而大部分时候,消防队不会出动,因为最好的做法很可能是任凭野火自生自灭。
那之后有好几天,我想像着一个人在孤绝的山顶看着一场场大火,记录它的点滴进展。在那间隔热良好的小屋,她感受不到火的炙热,也闻不到树叶烧焦的气味。她的职责是观察这遥远的大火,而无权去影响它。在那个情绪动荡的毕业季,对这场无能为力的大火的想像曾经让我冲动过是否应该去蒙大拿州成为一个看火人。
最后,因为我对孤独的胆怯,我没有鼓起勇气去做看火人。我来到了美联储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工作两年后,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也是一种“看火”的职业。大众把央行想像成无所不知的预言家,我们的确是预言家,可是除了极少数幸运的时刻,我们的预言为时已晚,它预测了灾难,却已无法根治导致灾难的祸首——何况那些祸首也许本身是无害的,甚至那么乐观:人们活得更长了;男女更加平等了。绝大多数时候,“灭火”太晚了,我们只是在“看火”,隔着很厚的玻璃窗看火。几千人的工厂倒闭了,几十年的老员工突然失业,一座辉煌一时的小镇变得潦倒破败——可是这些凄楚的故事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成了无声无息的数据,取对数、去平均值、取差值、跑回归,然后把经济火灾的报告传送出去……仅此而已。几周几个月后,这些报告会导致重大政策出台,第一轮量化宽松、第二轮量化宽松、第三轮量化宽松——也就是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印钱。它们是有效的政策,可是公众将永远批评政策效果太缓慢、太被动,因为他们难以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看这场安静的大火。
正这么云游着,乔万尼从办公室探出头来,一副为难的模样:“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了。你现在有空吗?能不能烦扰你帮一个大忙?”
我知道我会跟他进去,他会坐下来,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告诉我首先应该做什么,然后应该做什么……他读过刚刚我和理查朗读的那篇论文(因为正是乔万尼让我读的),他知道论文里面悲观的观点,也知道该如何对付它。在美联储,我们做的是宏观经济的工程学,任何石破天惊的论点都得接受现实数据的检验,实证结果总是和理论不太一样:悲观的被迫带上一点乐观;乐观的也被迫不能把话说满。现实是一摊浑水,非清非浊。乔万尼不是传统模样的经济学家,他的表情不会为了T数据和R平方而变好变坏,他也不醉心用几十个图表和公式来弄花人的眼睛。可是我越了解他,我越相信,只有这样沉静如海的人,才能位处于美联储的玻璃后面,盯着那从没太平过的宏观经济之林,做一个稳健尽责的看火人。
“当然啦,老板。当然愿意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