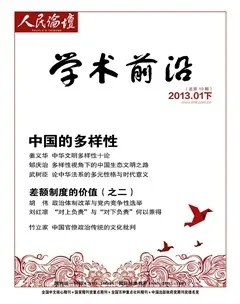多样性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之路
摘要 如果从多样性的视角来观察与思考,即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重大主题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充满着“一”与“多”之辩的议题。因而不仅需要坚持一种科学而辩证的认知态度,而且必须正视更具体的理论与实践层面挑战。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向度的生态恢复或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更全面、协调与绿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追求的内在组成部分,这要求中华民族展现一种更高的政治、社会与生活智慧。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多样性 绿色发展 环境政治
【作者简介】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欧洲/欧盟政治等。
主要著作:《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当代欧洲政党政治》、《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环境自然价值的发现》等。
中共十八大之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媒体宣传与学术研讨的热门话题①。十八大之后,“五位一体”和“建设美丽中国”等新表述引发着国人对于中国绿色未来的诸多美好愿景与想象。但严肃地说,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层理论关系,还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大量具体性理论与实践挑战,都要求我们作出既坚持科学而辩证的认知态度、又富于创新勇气的时代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向度的生态恢复或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全面协调的、绿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追求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要求中华民族展现与彰显一种更高水准的政治、社会与生活智慧。基于此,结合对十八大报告有关论述的学习,笔者从“多样性”的视角谈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维度。
“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多样性”(diversity)最初是一个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概念,即生物(态)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物种之间及其与周围生态环境所构成的复杂丰富的样态和关系结构以及不断延续下去的潜能。如今,地球上生长着超过200万种生物。这是经过30多亿年生物进化而渐趋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的结果,这些物种十分复杂地相互关联着,并组成各个区域/层级上的生物社会(链)。换言之,正是这些分化为不同物种的生物种类,以及由它们与周围环境组成的生物生态和社会结构,构成了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最基本前提的生物(态)稳定性与多样性。依此而言,多样性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既是大自然漫长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客观性事实,也是人类理应认可、肯定和尊重的一种正向价值。简单地说,(生物)多样性、多样化本身就是积极的,因为它意味着更为复杂与丰富的种类构成及其关系结构,而复杂与丰富的种类构成及其关系结构意味着更多的生物(态)信息传承和延续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过于单一性和简单化的生物种属及其生态关系结构,即使能够获得短期内的数量性膨胀或空间性扩张,也往往难以逃脱突然灭绝的厄运。
相应地,我们也在近似或类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或社会多样性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无论是人类社会整体还是某一国家(族群)社会,一种多样性、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更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与文化价值传承,而且也更容易承受外来文化与社会的冲击、入侵甚或殖民而得以薪火相传。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谜案也许就是,为什么四大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成功地延续下来(至少是在更为完整保存的意义上)?一个最有说服力阐释是②,中华先祖们幸运地享有宽阔的地理空间(从西北到中原,从北国到江南),使之在面对来自文明水平较低的“荒蛮”族群时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而当华夏文明最终成长为一个庞大而强势的农业文明时,就变成了足以抗拒任何外来冲击的同化性力量(而很难被同化)。也就是说,尽管中华文化与社会时常被冠以“大一统”的称谓,但其更根本性的特征也许是它的多样化(及其多样性)。近代以来的历史曾一度被知识(政治)精英解读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而言)所遭遇的“灭顶之灾”,我们除了融入一个工业/城市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世界外别无选择。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整体实力的逐渐恢复和上升,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社会主体(同时作为历史性主体和现实性主体)意识正在觉醒,其中包含的文化与社会多样性信息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和现代化实现后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依然可以成为另一种“样态”。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文明”呢?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一种能够充分考虑并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及其客观要求的人类社会化生存及其组织形态,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平、和谐与共生。一方面,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形态都是一种相对广泛分布的社会化生存及其组织形态,因而,地球上过于局部性的、数量有限的族群或社群生产生活方式难以构成独立意义上的文明,更不用说同一社会内少数个体的特立独行意义上的异质举动;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文明革新必须同时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个层面上。因而,文明性的变革肯定是人类社会整体与深层意义上的巨变,尽管它的发生与完成都不太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与实践尤其如此。因为当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基于如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价值的自觉认识与反思;二是人类对社会文明发展及其延续条件的自觉认识与反思,尽管远古时代的人类文明(比如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也许是更“合生态”(在自然而然的意义上)。就前者来说,数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扩张,使我们在充分利用地球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同时,初步认识了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的生存前提性价值,并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代表的人类“先进”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展开反思;而就后者而言,正是从局部性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污染到全球性气候异常的自然生态系统崩溃危机使我们初步反思与认识到生物(态)整体性与可持续性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及其延续的前提性意义(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尤为重要的是,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大规模工业现代化建设之后,当代中国已经具备了生态文明建设主客观条件,并站在了这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深刻、最为艰难的文明形态革新浪潮的“潮头”。
可以看出,“多样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意蕴解读的方法论相关性在于:生态文明建设在本质上趋向于并最终实现对自然界生物(态)多样性、整体性与可持续性价值的人类文明性理解、善待和尊重。换句话说,对生物(态)多样性与多样化的认可、崇尚与促进应该成为当代社会的文明追求与文明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或者说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崭新的生态化文明的内源性基质(在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歧视本性的意义上)。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与“多”
在中国特定性背景与语境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化中后期主动解决传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模式与理念下造成的生态环境难题(代价)——集中体现为生物(态)多样性与稳定性的降低或破坏——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努力。③相应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性要求与检验尺度就是恢复自然界本身以及人类社会曾拥(享)有的生物(态)多样性与稳定性。笔者认为,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全国人民尤其是各界精英必须达成的绿色“政治共识”或者说“一”。具体地说,这种绿色政治共识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的内涵④:
一是着力于对传统工业文明(尤其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生态化超越。从最直接或直观的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主动克服依然主宰着当代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副面影响。事实表明,近代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全球性扩展的确带来了世界物质财富总量的倍增式扩大,但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全球性紧张的根本原因——当地球上所有的民众都希望以美国人的物质消费标准来生活时,地球的命运就已注定。需要指出的是,更为根本的是摒弃工业化及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无条件的至上性和优越性,而不是简单地抛弃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成就及人类解放性遗产(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这方面最值得珍视的也许是我们作为后现代社会主体所具有的自我反思(批判)性视野与能力——比如,大概只有后工业化社会及其民众才会真正理解物质财富对于人性自由与解放的有限性意义(物质富裕与幸福感并不是一回事)。
二是坚持一种弱人本主义的哲学与价值立场。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引入了西方学者关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将前者作为我国环境(生态)伦理学/哲学构建的基础。⑤事实证明,这种极端化的二分法思维并不适合中国学术传统与语境。而就其作为一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新解而言,“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更不(可能)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力求在人类(社会)的视野与潜能之内实现对自然生态的充分尊重与内在契合,或者说一种“弱人本主义”。更具体地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是,逐渐学会和习惯于将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自然系统整体(包括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片面强调和夸大人类(社会)超越自然系统整体的智慧与工具性(尤其是借助科技的)能力。可以说,十八大报告概括与贯穿其中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态文明观”,或者说是一种更文明的生态认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控制开发强度,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这些显然是弱人本主义的表述,却具有强烈的“环境主义”甚或“生态主义”色彩。
三是构建一种合生态的生存生活伦理与发展观。近代社会以来的工业文明成长及其扩展是以个体、社群和国家的物质享受、财富占有与资本积聚为价值旨趣和进步导向的,结果是,这种个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进步观,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主宰下的世界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相应地,我们只能看到与面对一个社会日益不公正、生态日益衰败的星球。作为反拨,生态文明建设倡导与追求的是一种尽量维持生物(态)多样性、可持续性的适度生产、有限消费和绿色发展,而这些新理念将同时是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和大众性的日常生活伦理。无论是“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还是“三个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它们的切实推进与真正实现都基于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本身的一种全新理解,同时依托、内化于全社会主体的生存生活伦理(正义)观念的实质性革新,也就是一种“生态新人”或“生态文明主体”的出现与孕育。
四是实施一种生态的国家现代化战略。生态文明无疑只能是一个社会、甚至一定地理空间内的数个社会经过长时间缓慢演进的历史性结果,任何指望凭借大跃进式的跳跃或空洞口号实现工业文明生态转型的想法,都至多是一种善意的幻想。但生态文明建设及其推进,却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积极进取性的国家战略选择,而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五位一体”提法应理解为这样一种国家的绿色发展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现代化”在欧美国家尤其是欧盟核心国家有着特定的理论与政策意涵⑥,但对于像中国这样依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生态的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内容一致性⑦。比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其政治正确性更是不容置疑。
毫无疑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头等大事是尽快在全社会和全党树立起对上述四个层面意涵的“政治共识”,也就是真正理解、认同和遵循这种大写的“一”。但在笔者看来,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一”的对立面,即“多”。十八大报告着力阐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基础、战略部署和任务总要求,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一”的概括与展开,其目的是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的政治共识,这当然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就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本身,还是就这些战略部署和任务总要求的贯彻落实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面是“多样性”的思维与视野。在笔者看来,生态文明建设中对“多”的考量主要基于如下四点。
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中国自然地理禀赋的多样性、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共同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最大现实,即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广义的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还包括不同样态的自然生态系统、人文历史文化遗存和经济社会组织,而绝非只是人为划定的各级行政管理单位和经济GDP产出统计单位。这方面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在充分尊重不同主体的适当的普遍性物质利益需求的同时,将这种多样性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宝贵财富,而非亟待消除或资本化开发利用的对象。这其中一个很容易引起的争论是如何对待所谓“落后地区”的物质利益需求和经济发展权利(作为历史性权利),由于这些区域往往处在地理边缘和少数民族积聚地区,这一争论会变得更为复杂与纠结(比如会添加上少数种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公平权利和文化保持自主权利等)。但理应坚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首要任务是自主性的多样性主体认可与彰显,尤其是消除多样性主体中的等级化划分与歧视(尤其是基于对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及其利益的屈从),并最终使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成为一种正向性的价值与能量。
目标追求的多样性。如果不同区域、层级和社区主体的自主性得到充分尊重,或者说,如果这些不同区域、层级和社区中的主体真正呈现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利益表达,那么,这些社会主体理应有一种多样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追求,当然也包括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目标追求。比如,对于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居民来说,他们是绝不会仅仅把山体下的稀土矿产视为等待开采的自然资源的,因为,他们往往与大山、森林、河流有着更为复杂的精神与情感联结;同样,农村与农民首先体现的是一种农业文明诞生以来的悠久性社会生存与文化传承方式,而不只是工业文明视野下的土地与劳动力储蓄地和污染物排放场(劳动力来源和环境空间),因而,成为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无产)劳动力与(市场)消费者并非就是广大农村与农民的唯一出路和自主选择。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多样性主体与多样性(化)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而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基本要求是生态觉醒与自觉的多样化主体能够自主做出多样性的目标追求。简单地说,对于广东省和西藏自治区来说,生态现代化的战略和对工业文明的生态化超越都应有着十分不同的目标性意涵和思路,而对于一种大众性的合生态生存(活)伦理和发展观培育来说,前者很可能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而不是优势。
制度架构的多样性。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不同的社会制度架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如此。可以想见,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的沪宁杭城市带与青藏高原地区的荒野城镇有着十分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任务,因而也理应拥有大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框架——如果说前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以更经济高效和生态友好的方式提供物质生活必需品,那么对后者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充分保护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原生生态系统;同样,雨水丰沛的南方城市和常年干旱的西北城市对于城市水林生态景观的目标追求与管理制度也应有着诸多方面的差异,比如对于延安和兰州来说要维持一个大型人工湖泊或水上游乐场就必须首先考虑自然与生态成本问题(而不简单是园林部门的经济成本核算)。也就是说,对于不同区域的主体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根据自主确定的适当目标,构建合适的经济、社会与法律制度框架——哪怕都是环保厅(局),其在不同地理区域和行政层级的机构与职能设计也应有所不同。
政策体系的多样性。多样性的参与主体、多样性的目标体系与多样性的制度架构当然意味着各有特色的政策体系,也就是政策体系的多样性。毫不夸张地说,就像我们很难树立一个全国性模板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一样,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几乎不存在全国、全省(区)范围内的普适性“好”政策或“坏”政策。比如,一般来说,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是一项与国家长期发展需要相一致、同时也有着较为广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绿色政策,但盲目和低标准的无序膨胀却很容易使之成为一个地区的新型污染源,给当地带来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再比如,推进城乡一体化从现阶段来说的确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助于抑制和解决日趋恶化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但简单地用消灭乡村的办法来扩大城市规模,或者用大中城市污染行业的转移来支持中小城市的扩展,都很难说是一条“生态文明之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辩证理解与处理好“一”与“多”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需要借十八大的东风在全党和全社会营造一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共识和舆论氛围,但同时也要充分强调和尊重生态文明建设中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多样性,二者不可偏废。
如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样性
那么,我们应如何来保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样性维度呢?在笔者看来,鉴于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现代化发展阶段,尤其需要强调如下四点。
首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包容互鉴。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这组概念绝非仅是“生态文明”概念的逻辑延展,而是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现状时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性抉择。⑧一方面,就其实践进展而言,“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或“生态的资本主义”是我们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从事生态文明建设时必须要考虑的整体性环境,而且,“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等方面的积极进展也的确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尽管这些措施未必能够真正导向一种“生态文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生态的社会主义”似乎也不应仅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实践与理论的现实性对立面,而应有更为具体与深刻的新意涵: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般性阐释,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或者说,人类文明的未来只能是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依此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真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当然,如此意义上的生态文明需要更严格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像“生态新人”的培养。从人类社会的现有智慧来看,一种更生态化的文明既不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之上(将其完全破除),也不会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的新基之上(这还更多是一种逻辑推演)诞生,因而,更为理性与现实的选择是在二者的包容互鉴中尽量扩展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比重,而这也就意味着肯定与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及其举措的多样性。
其次,对前工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遗产的总结反思。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时代以来的三种主要文明形态。总体而言,越是古老的文明形态,人类社会越会遵从或受制于生态自然的客观性规律及其约束,只是到了工业/城市社会,人类才可以做到相对摆脱自然界及其生态条件的地域性限制,实现了持续而文明的生存延续(除非重大自然灾害和战争)。也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应充分肯定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意义。但无可否认,正是在工业/城市文明中,人类社会逐渐忘记了自然生态的客观规律性及其约束,追逐一种超越自然资源制约和生态规律约束的普遍性(无论地域)、即时性(不分时节)和无限性(不加节制)满足,而地域性、时节性和自觉节欲曾是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的生存条件与重要表征。结果,“工业化/城市化”终于走到了其生态的极限或“文明的极限”。因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前工业文明时代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遗产”,目标则是现行的工业/城市文明的生态化。依此而言,无论是就未来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连结形式还是就最新一轮的城镇一体化推进来说,我们都需要慎重对待“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过分简单化思路。⑨相比之下,至少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恐怕是一种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型城乡关系结构以及新型的经济社会联系方式。
再次,对生态化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创新性探索。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方面已经有所进展。比如,创建“生态省(市)”、“生态市镇”、“生态社区”和“生态经济(工业)园区”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福建省厦门市、贵州省贵阳市和新疆喀什市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验,山东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战略,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的生态镇建设实践等,都已取得了某些实效。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生态省(市)”、“生态市镇”、“生态社区”和“生态经济园区”(也有一些叫“生态工业园区”)建设,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更大范围内(层面上)经济增长压力的挑战,而在一个经济主义甚至GDP思维主导的语境和环境中是很难生长出真正的绿色文明的;二是本地范围内或层面上多元价值目标之间冲突的挑战,如果缺乏制度化的“硬约束”,生态文明的考量或尝试很容易成为一种绿色的修饰、伪装或替代。再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方面,国内较为成熟的是由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创制的“生态文明建设省区评估体系”,目前已发表了3个年度报告(2010年~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评估的量化及其指标体系设计是一项科学性极强的工作。应该说,北林大评估系统仍存在着方法论设计(比如生态文明程度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指标选择和不同指标赋权等方面的不足,尚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而且,我们也许需要更权威的、更多元化的评估体系系统。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是依据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原则,依据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rT9aQqUjA6lqKtXhnOddURJO4tgyZ+9J22LMzLVkKjI=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功能区战略的基本思路是不同省区或生态区域依据其自然生态条件,分别担当国家或区域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中的不同职责。其生态科学性是不必置疑的,但现实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前提是解决“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以保证不同发展功能定位下的区域及其民众享有大致均等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迄今为止,“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都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京津冀地区水源地、陕甘渭河流域和浙皖新安江流域的政策试点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而更具挑战性的制度创新是,一方面,在一个依然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应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生产生活环境和人文历史遗产的充分严格保护,而这些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区域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水准的基本尺度。因为从历史经验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人文历史遗产衰败消失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客观必然性”代价,因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尽量减少、延缓和降低这些方面的不利影响,其“红线”是不能使这些方面的损害/破坏成为不可逆的。这就需要一个拥有充分权威与职权的“环境国家”,而2008年行政级别升格后的环保部显然难以承担这样一种重大责任。
另一方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动力机制。除了技术的和经济的创新与推动,还需要有法律与政治的创新与推动。比如,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政策议题的界定与民主讨论、政府的民主科学决策到相关政策的落实与评估,都需要来自社会和政治各层面主体的“信息输入”和“主动介入”。就此而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经济与技术创新机制革新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公众民主政治参与问题、社会管理及其政治制度创新问题。概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实现都离不开人民主体,因而,人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生态文明社会”(“生态公民社会”)建设是这种综合性动力机制的枢纽和关键,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化动员”和“自上而下动员”有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
总之,我们必须十分清楚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或根本要求的真正实现在相当程度上是很难在现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框架下做到的。无论是经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还是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观念的牢固确立,归根结底都需要创建一种真正生态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构架。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将是基于一种全新制度框架的结果。毫无疑问,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层面上的生态化变革,必将是一个长期性、渐进性和累积性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既不能指望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来实现,也不能无视这样一种长期性趋势,而应大胆地探索与创新——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制度(经济、技术和法治管理)和更基础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
最后,对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更多关注。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阐述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重要基础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文化、价值理念的不断生态化革新,从而最终确立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发展观和文明观。而研究与传播这样一种价值观、发展观和文明观正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生态文化理论)的任务与使命。必须看到,我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环境自然科学、环境工程科学相比还处于严重滞后的不协调局面。除了相对成熟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外,其他分支学科仍处于交叉边缘学科的地位。⑩
广义而言,中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对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回应与互动,所形成的众多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的总称,具体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文学(艺术)、环境史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公共管理)、环境教育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等,同时还应包括近年来在属于理工门类的以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为主体框架内成长起来的一些明显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分支学科,比如环境伦理(哲学)、环境与社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源保护)、环境与公共管理、环境与国际合作(法),等等。但无论是总体上与理工类环境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科相比,还是就大学科内部与其他传统或主干学科相比较而言,我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不平衡。而从生态价值观取向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把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生态文化理论)作出“深绿”、“红绿”与“蓝绿”三维向度下的整体性概括。“深绿”强调公众个体价值观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变与提升,自觉地把个体生活与生存理解为自然生态整体的一部分,因为单纯的制度层面变革并不能真正消除生态环境问题;“红绿”强调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指导,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与重建来克服生态环境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在性矛盾注定了它不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做到这一点;“蓝绿”强调通过经济技术手段与公共政策管理的渐进革新切实抑制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根本性变革都很难设想会经常发生。正是这些具有明确价值承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分支流派,给我们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样性思维与思路,并始终保持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批判精神。
最后,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多样性的上述阐述绝非是要忽视或贬低凝聚与宣传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民共识的重要性,而是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就其本义和根本性要求而言,理应是一种多样化的文明性、制度性与社会性回应,以便更好地恢复、维持和符合生物(态)的多样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依此,我们才能切实避免以传统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和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克服现代文明的生态弊端,更有可能找到真正属于未来的后现代社会组织与文明生存道路和形式,并避免代际、地域、阶层、组群局限性的全局性不利影响。
注释
①近几年来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著作有:姬振海:《生态文明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薛晓源、李惠斌:《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学明:《生态文明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张慕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吴风章:《生态文明构建: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傅治平:《生态文明建设导论》,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版,2008年;余谋昌:《生态文明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周鸿:《走进生态文明》,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明初、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文台:《生态文明十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参见2012年11月16日杨庆中教授在清华—卡内基中心举行的“中国传统和谐文化论坛”上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与和谐观念”。
③郇庆治:“强化顶层设计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教育》,2012年第12期。
④人民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http://cpc.people.com.cn/18/GB/350825/index.html,2012年12月24日。
⑤杨通进:“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载徐崇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⑥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⑦李克强:“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3/c_124086899.htm,2012年12月25日。
⑧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9月26日。
⑨刘茂松:“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工业化”,《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26日。
⑩郇庆治:“亟待发展的中国环境人文社科学科”,《环境教育》,2011年第1期。
⑾郇庆治:“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责 编/樊保玲
Examin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ity
Huan Qingzhi
Abstract: Observing and pondering from the diversity perspectiv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will become a major issue in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is a topic involving a debate over "singularity" or "diversity". Therefore, we need not only take a scientific and critical attitude in understanding this topic, but also squarely face a series of specific challenges in respect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 result,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never simply been ecological recovery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ut a mor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green inherent component of futur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ursuit. So it requires the Chinese nation to show a higher level of wisdom in politics, society and life.
Keyword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diversity,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