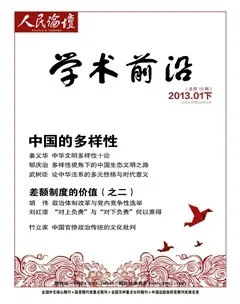中国语境下的差额选举及其问题
摘要 选举式民主是对古典民主的修正。“差额”本身是选举的应有之义,差额选举不仅提升了民主的真实度,体现了人民主权的观念,而且有利于一种高质量的民主前景,符合现代的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不过,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差额选举”却反映了民主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理性对待并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提升执政科学化水平,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差额选举 候选人 民主政治
【作者简介】
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等。
主要著作:《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隋炀帝传》、《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等。
余艳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价值目标之一。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与代议政治则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党制度的完善,选举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大制度的发展等紧密联系。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不仅需要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同样,以开放性的姿态、包容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复兴,也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的重大使命。故而,加强对当代中国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与人大制度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
选举与民主
从原生态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发轫于古希腊的“民主”,其原意是指人民的统治;①虽然这里的“人民”主要是指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但是这里的统治却是指公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管理”。②因此,这种古典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其实并不包含选举这一内涵,也就是说,选举并非古典民主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虽然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宣称他们的民主追求,但是,从古希腊到近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视为“坏东西”。民主之所以变成“好东西”,既与思想家们对民主观念的革命有关,也与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态的变化紧密相连。
思想家们民主观念的变革,主要是将古典民主所内含的普通公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管理”,替换为公民通过选举他们的代表,再由他们的代表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管理,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代议制民主。这样一来,古典民主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暴政问题,零和博弈问题以及高成本、高风险问题,就被成功地化解;④更重要的是,从近代以来的人类政治生态来看,近代人类最基本的政治共同体,不再是古代的城邦,也不是绝对主义的国家与帝国,而是拥有广袤领土的民族国家,故而,古典民主所要求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与管理,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代议制民主则成功地克服了这一规模困境。
在代议制民主制下,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因此,选举自然就成了代议制民主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之下的公民,他们的“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⑤因此,从公民参与的强度与效度即民主的精神实质方面来讲,代议制之下的选举式民主,实际上是对经典民主观的第一次修正,这种选举式民主已经偏离了民主最原始的内涵。
现代视野下的差额选举
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诠释,所谓选举是指挑选,“它是一种具有公认规则的程序形式,人们据此而从所有人或一些人中选择几个人或一个人担任一定职务”。⑥也就是说,选举本身意味着要么从所有人中挑选几个人,要么从一些人中挑选一个人。而所谓的差额选举,是与等额选举相对的,指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人名额的选举模式。故而,原初意义上的选举,其内涵本身就意味着差额选举。换句话说,选举本身就意味着差额选举,他们之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从民主的质量追求上看,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等额选举相比,差额选举无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也更符合民主的本意。
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差额选举提升了公民参与的可能性,而公民的参与机会与强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主的程度。公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介入政治的报酬、备选方案的差异、参与者的参与对改变结果的影响等,都会对公民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产生深刻的影响。⑦与差额选举相比,等额选举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因为不存在备选方案,而且公民的这种参与也对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冷漠,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极为低下。因此,一个理性的选民,除非受到社会责任感与民主运作的义务感的驱使,否则,在等额选举制度之下进行投票实际上是不理性的。相反,差额选举意味着任何公民的一票都可能改变选举的结果,它既提升了公民参与的效度,也提升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故而,这种选举模式之下的公民,其参与政治的机会与可能性,确实大大提高了。
从人民主权的角度来看,差额选举体现了更为真实的民主。如前所述,民主的本意是指人民的统治,由此引申出人民主权的逻辑。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现代政治中的公民很难直接作出政治决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就被剥夺。相反,公民放弃直接的决策权,换取的是自由的选举权,也就是说,公民可以直接选择由谁替他们作出决策。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那么,所谓的人民主权,其内涵就被完全架空了,没有任何意义。而等额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否认了公民的自由选举权。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公民只能在自己无法决定的名单中选择自己相对满意的候选人。故而,公民的民主权利与选择自由,都被大幅度地压缩。
从民主的质量与远景上看,差额选举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与可持续。无论是民主的成长还是民主的巩固,都离不开高质量的公民,这种公民既有理性精神与宽容气质,又富有公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是,公民的民主性格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正如米歇尔斯所说的,“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我们在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⑧差额选举中存在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因此,它需要公民作出选择,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学会自己去寻找并分析关键信息,在不同的候选人之间进行富有想象力与分辨力的洞察,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政治智慧、实践能力、理性精神,都会得到升华。而所有这些,都会为今后的民主巩固,提供知识学与实践学方面的基础。
从科学化的角度来看,差额选举也体现了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差额选举意味着淘汰与竞争,因此,无论是政党、组织还是个人,为了赢得选举,都会千方百计地将最优秀的人员推荐出来;更重要的是,从预期上讲,候选人一旦当选,必须兑现政治承诺,否则,下次选举极有可能被选民选下台,这样一来,为了赢得下次选举,当选者的进取心、责任感与对群众的利益关注度等,都有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此外,差额选举至少部分地杜绝了操纵选举的可能性,从源头上制约了以法治名义进行人治的空间。⑨
差额选举:历史与现实中的困境
早在1928年,差额选举就被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实践之中。⑩但是,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在其选举制度中基本上都采用等额选举模式。之所以采用这种制度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建国后我国的选举制度依旧受到苏联的影响,而苏联的选举制度长期采用的恰恰就是等额选举模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于稳定与秩序的追求。因为这种等额选举既从法理上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也有利于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性控制。
不过,从1957年开始,差额选举就成了部分领导人的价值追求。1957年6月19 日,刘少奇在谈到来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问题时说:“候选人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例如选10个代表可以提20个或25 个候选人,但在提出名单时,还是要经过协商。”此后,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革的影响,直到1979年,差额选举才由正式的制度予以确定。根据1979年通过的《选举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同年通过的《组织法》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地方国家各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差额选举制度。
1979年前后,党和国家都将差额选举条文写入了正式制度。相对于此前的30年,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自此以后的差额选举,却一波三折,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历史变迁。透过这种历史变迁,我们可以窥视差额选举在共和国的困境,同时也可以见证民主政治之路在中国的艰难。
范围:难以逾越?差额选举的困境,首先体现在差额范围确定的举步不前上,甚至可以说今天差额选举的范围,还没有突破1979年的法律条文与精神。从此意义上讲,30多年以来的选举政治依旧原地踏步,乏善可陈。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所有地方各级政府的正职领导人,都应该进行差额选举。这相对于实行了30多年的等额选举制度,毫无疑问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进步。而且在此后的地方政府正职领导人的选举中,也确实存在着差额选举的事例,例如1988年广州进行的市长差额选举。但是,反观2004年新修订的《组织法》相关条款,可以发现:不仅没有在此基础上进步,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倒退。该法对于地方各级政府的正职领导人的选举态度是,“差额选举是通则,等额选举是例外”。但正是这一例外性的规定,为正职领导人的等额选举留下了法律上的操作空间,而在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都将等额选举这一例外当成了通则,以至于在最近几次的地方领导人换届选举中,几乎鲜见正职领导人采用差额选举的事例。可以说,地方各级政府正职领导人,是采用实质的差额选举还是采用可操纵的等额选举,乃是真民主与假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大众的参与起到的仅仅是一种程序合法化的作用,而他们的参与对于选举结果毫无影响,那么,这种选举民主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提名:谁的政治?差额选举的困境,还体现在对候选人的提名以及这种提名的有效性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差额选举制度发展的困境。
以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的选举为例,从候选人的提名上看,1979年的《选举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2010年新修订的选举法第二十九条则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也就是说,单个选民成为候选人的要求明显提高,从而使得难度也大幅加大。从对候选人的宣传与介绍上看,1979年的《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实际上意味着,选民与候选人可以通过各种正当与合法的形式进行竞选,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获取民意支持。但与1979年的《选举法》相比,2010年的《选举法》在这方面同样没进步可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倒退。根据2010年《选举法》三十三条的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这就是说,候选人不得自己随意与选民见面,而必须进过选举委员会的批准与组织。实际上反映了对候选人的不信任以及对于公开的选举政治的不适应。
从选举的实际效果来看,由于1979年《选举法》相关条文的规定,在1980年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不仅选民确实可以自由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而且确实有了比较激烈的竞选。在这一年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大代表选举中,北京大学有两个代表名额,而正式候选人则有18个,且公开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竞选的大字报、辩论会、演讲、座谈会、辩论、回答提问等)。而此后的人大代表选举,出现了鲜见的激烈竞争,人大代表甚至成了一种荣誉与身份的象征,这种象征并非个人与选民之间互动的结果,而是一种分配。因此,这些人大代表,自然也很难代表选民的利益,甚至在人大开会时“只懂得跟着别人,人家干啥我就干啥,举手就举手,鼓掌就鼓掌”。以致于严重影响了权力机关的实际运作效果,也使得国家的权力配置出现严重的失衡。
类似情况还有对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提名。从法律条文上看,按照1979年《组织法》第十六条以及1986年《组织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地方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提名权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手中,也就是说,除了人大主席团以外,人大代表可以提出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包括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等。这一规定同样见于2004年《组织法》的第二十一条中。只不过后者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例如,对于“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的提名,省一级需要30名人大代表的联名,市一级则要20名,县一级要10名。因此,仅仅从条文上看,前后20多年似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后者由于对于提名的人数有了具体的要求,因此,毫无疑问是加大了操作中的难度。毕竟,对于省一级来说,由于涉及政治因素,且人大代表本身不是专职的,彼此之间平时几乎很难有见面的机会,因此,要争取30名以上的人大代表,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所以,从实践效果上看,最终前后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从前者来看,仅仅以1988年广州的市长换届选举为例,在这一年,由增城、花县代表团10位代表,东山区代表团13位代表,芳村区、黄埔区的12位代表,分别联名提出了由雷宇同志做市长候选人的意见,这一意见最终被采纳,使得雷宇同志最终成为正式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之一。可见,此时人大代表提名候选人不仅是真实的,可操作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效果。而2004年的《组织法》,这一条文对于人大代表来说几乎是形同虚设。因为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各级政府正职领导人采用的都是等额选举模式,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党提名的候选人成了正式的候选人。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官方对民间介入政府选举也讳莫如深,甚至发生过仅仅因为个人逞一时口快而表达竞选市长的意愿,最终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的悲剧事件。
观念:解放思想有多难?差额选举的困境,还体现在官方尤其是执政党对于差额选举的认知方面。如前所述,从1979年迄今已有30多年,在此期间,作为民主政治基础之一的差额选举制,在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几乎是举步维艰,止步不前。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国内一系列大事的冲击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官方对差额选举本身的认知困境有关。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三峡”的转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面临着各种问题,诸如腐败、失业、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一旦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差额选举,那么,人们很有可能将这些不满发泄在执政党身上,以至于在实践中存在着执政党所提名的候选人被差额选举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官方对于稳定与秩序的追求几乎压倒一切,这种追求实际上一直是历届政府的核心价值诉求之一。而从差额选举的历史看,1980年代初也确实出现过少数人利用选举宣传进行破坏的先例。故而,如果真的对差额选举进行大规模的放开,可能会使得部分人借此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甚至进行串联,从而威胁到政治稳定。因此,这种观念也制约了政府对于差额选举的态度。最后,对民众政治能力的怀疑同样限制了对于差额选举的认知。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普通大众政治能力的不信任几乎是近代很多政治人物的共同看法,从严复的“开民智”到孙中山的“训政”,都可以看到这种怀疑主义的倾向。即使是今天,依旧有很多人认为,除非公民已经受到过良好的政治训练,否则他们的政治能力是严重值得怀疑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将选举纳入可操作化的轨道,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
制度:何时不再稀缺?最后,差额选举的困境,还体现在与差额选举有效性相关的各种配套制度建设方面。有差额的选举未必是真实的民主选举。民主政治本身是一套系统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对公民权利的系统保障,司法独立,政府信息公开,政府行为法治化等。所有这些制度,都关系到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差额选举制的有效性。但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制度的建设,依旧是任重而道远。
差额选举:希望在何方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差额选举制度,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以真实、广泛且有效的民主为价值尺度,认真分析,仔细对待,给予应有的探索,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言,意义极为明显。
首先,政府与执政党需要转变观念,将差额选举作为民主应有的价值理念与追求。一方面,就执政党而言,执政党的先进性本身应该体现在党员的能力与业务素质方面,这些人应该具有竞争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因此,差额选举既是对他们的挑战,也为执政党展示其执政能力提供了记忆,它反映了执政党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自信。实际上,通过让群众进行比较与鉴别,最终巩固而不是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认识到,政治稳定并非单纯的畏惧变化,追求片面的稳定,政治稳定与放开差额选举之间并不是冲突的。相反,差额选举制度通过更替上届领导人的方式使得选民发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同时也通过选举的方式进行了统治的合法性置换,促进了政治稳定;更重要的是,差额选举制度通过引入真实的竞争,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也化解了社会的不满。最后,政府与执政党还应该认识到,民众的政治能力与民主性格,并非天生的,相反,这些能力只有在锻炼中才能提高,在实践中才能成长。因此,让公民尽快、尽早地介入到各种政治参与之中,会强化公民的政治能力、政治责任感与民主性格。
其次,在观念转变之后,要进行制度上的大胆改革、建构与创新,为真实的差额选举创造外在的制度化条件。良好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熟且系统的制度所创设的。这些制度至少包括但不限于选举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司法制度,舆论自由制度等。选举制度为差额选举本身提供法律依据与可操作的法律基础,因此,要对现有的选举法相关条文进行大胆突破。比如,对于各级正职领导人,不能规定“可以等额选举”这种例外,而要一律进行差额选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向中央推行;对于候选人的提名,要降低门槛;对于团体与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要有数量限制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公民获取与选举相关的各种信息提供便利,因此,要通过媒体、报纸、政府网站等各种媒介,及时进行政务公开,确保公民获取对称的信息;司法制度则对选举中各种非法行为,比如打击报复、弄虚作假、山头主义等进行规范;而舆论自由制度则有利于创造一种公平合理且富有活力的选举环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一种健康的、公平的、真实的差额选举的存在。
最后,在转变理念、突破制度之后,要敢于付诸行动,进行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去操作,制度再好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因此,可以先通过局部试点的方式,进行部分试验,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这方面,我们要防止过分的乐观主义,毕竟,民主政治本身也是一种实践中的智慧,一种技术性的政治,故而,一开始可能有各种小问题与缺陷,这完全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正常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过分的悲观主义,不要因为实践中的一点困难与问题就退避三舍,灰心失望。我们要相信,在这方面的探索本身就是改革的“红利”,就是一种投资,这种收益未必是及时性的,但绝对是可以预期的。其最终补偿的,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
注释
①[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页。
③[法]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9页。
④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2~43页。
⑤[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⑥[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
⑦[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31~137页。
⑧[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
⑨虞崇胜:“差额选举:中国式民主的应然之路”,《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
⑩高新民:“差额选举与党内民主”,《学习时报》,2012年5月21日。
⑾徐百尧:“略论彭真对新时期人大选举制度建设的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⑿“刘少奇:最早主张实行差额选举的委员长”,《人民论坛》,2009年第1期。
⒀“1988:中国民主选举风波”,《深圳商报》,1989年3月31日。
⒁⒆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7193,最后检索日期:2012年12月23日。
⒂⒄“共和国辞典:差额选举”,http://news.qq.com/zt2012/ghgcd/63.htm,最后检索日期:2012年12月29日。
⒃方三文:“姚秀荣:要说,不说不中”,《南方周末》,2001年3月8日。
⒅“曹天:我要竞选郑州市长”,《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1期。
责 编/赵斯昕
The Competitive Election in China and Its Problems
Yuan Gang Yu Yanhong
Abstract: Election-based democracy is a modification of the classical democracy. "Competitive" in itself should be the proper meaning of election. It not only enhances the practicalness of democracy and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popular sovereignty, but also helps create a prospect of high-quality democracy and conforms to modern scientific spirit and rationalism.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a, "competitive election" has been able to reflect various problems facing democratic politics. Rationally treating and carefully analyzing these problem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making ruling of the country more scientific and in promoting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Keywords: Competitive election, candidates, democratic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