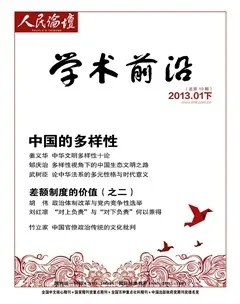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
摘要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来说,简单化地套用别国现成的模式是不行的。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文明的成功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
关键词 中华文明 多样性 伟大复兴 现代转型
【作者简介】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常委、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等。
主要著作:《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觉醒》等。
一个历久弥新的原生巨型文明
中华文明至少已经延续了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原生性的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
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0世纪左右,是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公元前2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是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日渐频繁,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立统一国家。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初,是中央集权的AHE0IJhLRig0adPdJHJYe6zlWLct+hXgUVHkmMbAGag=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秦汉王朝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文化的汉族已经形成,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
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及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
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是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固确立。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国家形态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自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农耕地区就一直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小农家庭中的人力、畜力、物力,能够较为合理而充分地予以利用,而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又特别能够节省与节约。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资金、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固然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它们又可使小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并能够在受到严重摧残后,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不断地存在与繁荣的主要基础。
同时,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北方及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农耕文明区域虽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口经常占全体人口的80%以上,因此,它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地区人口相对较少,但地域特别广阔,极其广泛地影响着农耕文明和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三种文明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当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草原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不仅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成为一个整体。
至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和巨大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传统的经济根基,但这只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提升,而不是中华文明的断裂与否定。
政治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柢
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国家;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大一统。这也许可以对应汤因比所说的“统一国家”与“统一和平”,但在中华文明中,它绝非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而是整个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诉求和主要支柱。
政治大一统国家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而统一的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兴修水利、防灾防荒、利益冲突等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是因为要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
近百年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不少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都碰了壁,因为当这些方案付诸实施时,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明以“不语怪力乱神”而著称。中华文明一直注重以人为本,将“人文化成”视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中华文明因此常被称为泛道德主义文明。中华文明恰恰没有汤因比所说的“统一教会”和“统一宗教”对全社会的统治。
中国乱世亦常用重典,但平时对德治、礼治的重视要远远高过于对法治及刑治效果的期待。它体现了小农经济对于家庭及社会长久保持和睦与稳定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有序与稳定运行的原则需要。泛道德主义将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贯通与统一起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成为夫妇、父子、家庭、亲友、同学、同宗、同事、同乡、同胞等关系中的一个无法割断的一环,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往往得以坚守和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内在动力。
以家国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占支配地位的家国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家庭、家族、宗族一直是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但人们相互之间,还有广狭不等的地域性联系、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联系和族类联系,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系。至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更渗透到人们生存的全过程,以大一统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联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形成不可分割的家国共同体。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社会道德、社会礼制、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以家庭伦理、家族伦理为起始,由家庭、家族而地区,而国家,而天下,逐步向外扩展。任何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到衰老再到去世,都是由家庭而逐步递升至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存在都只能依附于这一家国共同体。家国共同体的价值远远高于并永远优先于个人价值,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家国共同体方才能够得到真正实现。
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是一种为等级差序所主宰的社会共同体。在等级差序结构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层级,都有其确定的角色地位,这就使共同体得以保持稳定。但在中国家国共同体中,权威与服从其实都只是相对的,职责和义务则是相互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被视为天下之达道。在家国共同体中,人们的身份与地位经常转换、流动、升降、变迁,“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连皇帝的位置都可觊觎,何况这一等级差序结构中的其他位置?父原本就是子,子终将成为父;大宗原先可能本是小宗,小宗很可能会独立为大宗;经由举荐或科举考试,平民可以成为官宰,官宰也很容易成为一介平民。总的结构是一种保持着等级差序的共同体,但每个人的地位又非永久固定不变,这就使这一共同体始终充满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形成了以私人所有制和高度契约化的市场交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本位主义、人权理论,以及人权天赋、人生而自由平等、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契约自由、罪刑法定及主权在民等法制原则陆续传入中国。人们在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传统家国共同体这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上、政治制度上、社会结构上、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传统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乡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同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但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中国非常薄弱,这就使个人本位主义的呼吁经常只局限在少数知识人圈子之内,游离于广大民众实际需求之外。尤其当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时,各个新兴的政党、军队、企业、学校、社团,要使自己具有真正强大的力量,都离不开对传统家国共同体的依仗和利用。
传统家国共同体近代以来受到的最大冲击,是20世纪50年代以摧毁农民小所有制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摧毁“官僚主义国家机器”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发展,是试图取消家庭共同体;从反对官僚主义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是根本改变原有国家共同体,而代之以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可是,社会大同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带来社会大同主义的实际,它所带来的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再受挫,政治、文化发展严重畸形,直至演变为“全国全面内战”。最富有“反潮流”精神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一步步退到现实所许可的范围。
事实一再证明,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合理的内核,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民营企业的兴起,为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提供了广泛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农民有权独立作出经营决策,支配其经营成果。这是中国传统复合型土地所有制的现代承续和新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制度就此瓦解。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在经营中的作用主要在土地发包,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农民一家一户重新成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承认城乡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构将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转到承认、支持和保护民众自主从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毫不含糊地确定中国现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修复与勃兴家国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为有效地防止个人本位主义和社会大同主义两种倾向过度膨胀,修复与勃兴家国共同体提供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
中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它要求“以百姓心为心”,知民之性,习民之情,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汉文帝时,贾谊在《大政》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提出,民为国之命,“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他又强调:民为国之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他提出的第四个命题则是:民为国之力,“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以此,他做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上位,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 在这里,民为国家、君主、官吏之本;为国家、君主、官吏之命;为国家、君主、官吏之功;为国家、君主、官吏之力。因之,民为国家安危、君主威侮与官吏贵贱之本,为国家存亡之本、君主盲明与官吏贤不肖之本,为国之兴坏、君主强弱与官吏能庸之本,为国家、君主、官吏能否克敌制胜之本。
“民惟邦本”所谋求的,不仅是人人丰衣足食,更重要的是通过“选贤任能”对整个国家进行动员、控制和管理,通过德教、礼教的教化和法治、刑治的约束,激励和引导人们成为君子、贤人、圣人、至人。能否真正做到“选贤使能”,被视为国家治理是否真正成功的关键之所在。为解决知贤与能和用贤与能问题,中国很早就已在探索并不断改进对贤者与能者尽可能公平而有效地进行选举、考核、升迁、罢黜、奖惩的制度,以及对于权力运行有效的制约、制衡、监察制度。
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明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进行直接选举的选举制传入中国,为人们所向往。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无论是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社会,都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将人与人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一概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亲情、友情、审美、知识交流全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清末新政以来,个人本位、代议制、多党制所引发的严重政治混乱以及各种政治闹剧,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在现代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人们在这一方面正努力寻找着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径。
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
中华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以义制利,以道制欲。
“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两千多年来,人们或主张重义轻利,或主张义利兼备,或主张先义后利,或主张先利后义,占居主流地位的价值取向,都是既承认利己,又承认利人,既承认私利,又承认公利。而且,总认定利人当高于利己,公利当高于私利;无论牟取何种利益,都必须选择正确的即不损害他人并兼顾他人的道路与方法。“以道制欲”的“道”是指比之耽于欲望更高的人生境界。它是和西方文明所力主的人为“经济人”或“实利人”、“唯利人”、“自利人”的个人主义,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有着巨大差异的经济伦理。
亚当·斯密追逐自利的“经济人”,边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观,这些观念从输入中国起,质疑声就一直不断。争论根源于它同中华传统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的冲突,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人首先应当是个经济人,还是道德人,应当是个人至上,还是社会至上,实质上,还是义与利、道与欲二者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的老问题。
由于缺乏经验,中国人一度以为苏联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实行统一分配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成熟的、成功的社会主义。这一模式,形式上只讲利他、公利,排斥利己、私利。加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盛行军事共产主义,讲理想,讲奉献,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讲自我牺牲,忌讳讲物质待遇,尤其是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造成对于人们个人利益、物质生活的一种漠视乃至鄙视。阶级斗争长时间以暴力、战争形式进行,新中国建立后又持续扩大化,使问题更走向极端,即一度将阶级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阶级整体利益名义下,在社会总意志名义下,将个人淹没了,甚至可以说取消了。尤其是在社会自身被抽象化与定型化、阶级分野被固定化与人为地不断扩大化情况下,那些被视为“异己”的阶级和社会成员,基本权利都被无情剥夺。社会又一度为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即只要“义”不要“利”所支配。
由于物质利益、物质刺激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生产过程及产品自主权、支配权的有限要求,一概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程朱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又笼罩在中国大地上。
中国现今经济的迅猛而持续的发展,可以说,乃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在当代创造性的承续和利用。它的现代版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长时间被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然而,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私人利益、物质利益,将个人责任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挥人的生产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资金、资源、人力合理配置并不断及时调整方面,可以发挥国家行政权力所难以起到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所通行的是等价交换法则,所有交换者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因为所有交换者基础与条件很不相同,资本的所有者、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占有者在和仅仅占有自己劳动力的生产者根据契约关系进行等价交换时,结果绝不可能平等。同样是劳动力的所有者,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能够发挥其才智的环境和机会不同,在同资本进行等价交换时,结果也绝不可能相同。要对市场法则所造成的社会实际的巨大不平衡进行有效地协调,对市场法则的弊端进行有力地控制、限制,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利用国家权力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有效地将私利和公利、利己和利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社会共同富裕统筹兼顾。这就是“义”与“利”在现代条件下的紧密结合。
当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引下,在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互相竞争、互相制约的环境中,义与利、道与欲仍然会经常彼此错位,产生各种摩擦甚至冲突。最为严重的就是GDP崇拜,它会引导人们无节制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会导致利欲、物欲的恶性膨胀。它会导致一些人千方百计将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私人所有,或者为了牟取一己私利,不惜伤天害理地作伪制劣、坑害他人。尤为严重的是,基于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加上物欲无所不在的浸淫,权力被严重腐蚀,形成大范围的权力寻租、权力越位以及权力膨胀。结果,权力便成为不受社会监督与有效制约制衡的无限权力,成为拒绝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自我封闭的绝对权力。
中国的民族复兴,必须非常谨慎地解决好新的历史条件下义与利、道与欲,或经济人与道德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正确解决,正是中国发展能否得以持续、中华民族复兴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所在。
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
中华文明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中为大本,和为达道。
《礼记·中庸》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论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被定为本体论的核心概念,是对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全面性、本质性的把握。中,又是对宇宙万事万物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状态全面性、本质性的把握,它认识到,所有矛盾运动都源于宇宙本根,而它们无论怎样千差万别,总离不开这一宇宙本根。中,还是对宇宙总运动和总变化的全面性、本质性的把握。既然本体是“中”,那么宇宙总运动便绝不是既无始点又无终点的线型运动,宇宙总变化便绝不是同样既无始点又无终点的线型变化,因为在这种线型运动变化中不可能有中心、中点。中,被定为本体论的核心概念,是将宇宙的运动变化视为一个时空互相紧密结合的三维立体的或球形的整体,它既包括由中心点向四面八方发散的运动和变化,同时又包括紧紧环绕着中心点周而复始地进行的向中心回归运动和变化。《易经·泰卦·爻辞》已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爻辞》更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老子》第16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观复,就是观察万事万物周而复始的运动。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只有认识到万事万物周而复始的运动本是常态,方才能够避免妄作非为,顺应自然之理。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械主义的循环论,而正是敏锐地察觉到宇宙运动变化并非直线形的,而常常是圆形的、球形的,其中既有无数线形运动构成的复杂的网络,又有大量扇形展开及向四面八方辐射的球体运动。中,因此是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立体性的思维方式。思考任何问题,都能放在纵贯古今的时间维度、包含四面八方的空间维度之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是一种异常宏大的宇宙观,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观、历史观。在“中”这一本体中,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为一体,时间与空间结合为一体,自然与人结合为一体,个人与社会结合为一体,个人的身、心、理、气结合为一体。中,收放自如:集中,可以聚集于一人;发散,可以扩展到整个国家、整个人类、整个宇宙。它既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又是一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无所不在的、普遍的实践。
本体性的“中”在实践领域内集中的表现则是“和”,它承认差异的产生是合理的、必然的,同时更关注矛盾着的各方如何互相配合、互相联合、互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统一体。
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近代以来,受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性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全面挑战。“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味地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强调历史和万事万物都是线型的发展。它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产生过相当大的刺激作用,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中华民族复兴是和中国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将人引向了新的异化。例如:工业化带来劳动的解放,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人的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还会纵容、鼓励和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义与利严重失衡,道与欲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亦因此难以遏制;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同时使人与人之间以契约关系与货币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关系;城市化,使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但同时却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变得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追求;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如此等等,给丛林法则的横行打开了闸门。
丛林法则使社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极为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完全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中华民族继续复兴,并葬送先前已取得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当代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和”法则一直在同丛林法则进行着激烈地博弈,努力约束丛林法则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力度。回归“中和”宇宙观与实践论,在现时代全新环境中创造性地发展与丰富“中和”宇宙观与实践论,必定能够引导我们国家逐步实现人自身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普通人与权力掌控者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
中华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德施普也,天下文明。
德施普也,天下文明,俱出自《周易》第一卦《乾卦》。前者原文为:“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后者原文为:“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见,即显现之“现”。龙,孔颖达疏:“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原先是说:春天终于到了,阳光普照,田地中各种作物都沐浴在春风中,生气盎然,茁壮成长。劳动者们日夜辛劳,自强不息,遇有灾祸顿挫,也照旧坚持,绝不懈怠。普天之下都会万象更新而走向光明。人们亦将自强不息,不断努力,与时俱进。
“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强调的是要用道德使全社会普遍受到浸润,使天下趋向文明。在儒家那里,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就是要在万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兄弟”及“一家”关系。这是一种既坚守自身文化与文明特质又非常开放的天下观。
当中国进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时,面对的乃是由西方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所确定的一套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这一秩序中,霍布斯、斯宾塞所鼓吹的丛林法则以及洛克、亚当·斯密和边沁所鼓吹的自利至上、功利至上法则,占据着支配地位。孙中山已强烈批评“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而高度评价中国文化是感化人而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要人畏威的“王道的文化”。中国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反复探索,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发展和不断扩大世界联系,是中国加速完成工业革命历史性变革的需要。人类所需要的全球化,绝非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也绝不等同于全球资本主义化。“道德普也,天下文明”,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更是今日之中国在全球化新形势下,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终极目标。继承和发扬“德施普也,天下文明”这一核心价值,将有力推动建设国际政治新秩序建设。
吸取世界各种文明精华,走中国自己的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外来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可以极大地丰富自己,可以帮助自己避免重犯别人所曾犯过的各种错误,使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但这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主体。
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突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缺乏心理准备的中国人曾一度陷入迷茫,对自己的文明不再那么充满自信,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人们怀疑先前所做的一切,不断地批判中华文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试图全方位地找出先前各种差错,全面改弦更张。由于重点在找错,只想着前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便没有精力去思考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究竟做对了什么。
显然,找错是必须的,但如果只关注找错,又是不行的。因为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自己坚实的根柢。几代中国人曾非常热心、诚心地或师法西方,或师法苏俄,力图从他们那里寻得富国强兵的妙法良方。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成功与失败互相交错的反复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对中国发展路径的独立探索,对于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说来,简单地套用别国现成的模式是不行的。
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华民族只能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只能走中华文明自己的路。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在不断试错之后,人们做出了历史性抉择。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有效地克服了脱离或偏离中国实际、中华民族实际、中华文明实际的各种思想和做法之后,终于坚定不移、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结果。
责 编/郑韶武
Ten Lectures on Divers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Jiang Yihua
Abstra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farming civilization, supplemented by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forest farming civilization. As a diverse and plural civilization, it has been maintained with the help of traditional commerce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upgraded by modern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For a big country like China and a great civilization like Chinese civilization, simply copying existing models of other countries does not work.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all foreign civilizations must adapt to and integrat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diversit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