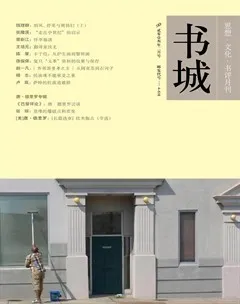萨特的抗战逍遥游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法国的抗德战争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巴黎以北七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Neuilly-Sous Clermont来了一双男女,在Commanderie街三十四号的一家杂货铺式的小旅舍落脚。二楼所有房间已经客满,只有阁楼空出一间只得一个床位的房间,气窗向街,没有卫生设备,这双男女还是把房间租下,等待另一间房空出之前,轮流睡觉。这双男女就是萨特与波伏娃。他俩原来生活在沦陷区巴黎,因着与加缪的关系,跟地下刊物《战斗报》一位工作人员有过一面之交,这个人刚好被德国人逮捕,他俩不想胜利在望的时候遭到任何闪失,匆匆忙忙躲到乡间去。
最初几天,萨特总不时从气窗往外探头探脑,看外间有什么可疑动静。他向旅舍主人德特雷(Detrée)夫妇宣称,他是个抵抗运动分子,德国人要抓他去枪毙!这对夫妇马上对他另眼相看,还倍加尊敬。其实从阁楼看不到什么地方去,这个瓦瑟区(Oise)没有德国兵,否则他们不会到这里来。这种神秘兮兮是想做给别人看,别人看不到,至少可以做给自己看。那时候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开始撤退,行军时不敢靠近乡村,只从远远的边缘地带走过。他俩在那里逗留了四个星期,在旅舍的公共地方写作,空闲时间双双到田野去散步,或者玩台球。到八月十一日,从广播电台得悉盟军已经到了沙特尔城(Chartres)的边缘,那么,通向巴黎的大路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既然他们自诩为抵抗分子,在战后论功行赏的时辰,又怎能不尽早露面?但匆匆赶回巴黎后,却不知道该跟谁联络,找哪些抗战成员,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些人。最后想起加缪,他仍然负责《战斗报》的编务,何不就登门拜访?加缪见他找上门,就请他写写巴黎沦陷期间的所见所闻,专题就叫《起义巴黎的街头漫步者》。
但加缪找错了人。须知萨特极少漫步街头,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嘴角叼一根烟,坐在“花神”(Flore)咖啡座上,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周围闹腾腾的生活与他无关。他可以在任何条件下给自己创造写作环境,这是他的本事。德军占领期间更少在街头走动,偶或与波伏娃散步,只选择没有危险性的小街小巷,永远不涉足可能发生事故的大街。战争末期巴黎人起义期间更不用说。但他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写道:“我只叙述我的所见。”又说:“我们知道指令:击倒一个德国人,夺走他的来福枪,以来福枪来夺取一把长枪,以长枪来夺取一辆汽车,以汽车来夺取一把自动机关枪或一辆坦克。在表示怀疑的抵抗运动的人当中,不只一人在耻笑,然而这个计划是在我眼前一点一滴地实现的。我的一个朋友,用一枝从古董商那里得来的马枪来参加战斗。”
文章一出,大伙哗然,不用太聪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萨特在书房里虚构的故事,而非报导一个活生生的起义的巴黎。筑街垒于巴黎人就像海狸筑堤,是长久以来的传统,妇女和孩子都可以介入,抗战时期也不例外。虽然没有发生街垒之战,但街垒可以阻挡军车。那时候巴黎有四百五十个街垒,但萨特的文章只字不提,根本不知道有这码事。他的所谓“我的所见”只是想像加道听途说,是从他所居住的酒店的窗子往外看到的一些动静。干巴巴的文字根本没有巴黎的形象、声音、动作,遑论反映巴黎人的思想与灵魂。
至于他那位英雄朋友,大家特别关心,究竟姓甚名谁?在哪一位古董商里得到马枪?这枝古董马枪使用什么子弹?古董子弹?如果是事实,都有迹可循,巴黎这类古董铺能够有多少间?马枪的神奇故事,就笑话般流传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及外省恢复了自由的城市。
在乱哄哄的战后时代,自封为抗战运动成员的人不少。萨特既然在《战斗报》上写起文章,尽管是战后的事,但白纸黑字,看起来比谁都更像个抵抗分子。他俩不遗余力,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都不忘记自吹自擂,自我吹捧为抗德战士,还说这段日子如何在和平时期为他们提供写作灵感。

但萨特和波伏娃曾否参加过抗战运动?做了些什么工作?有谁可以作证?历史学家约瑟夫(Gilbert Joseph)花了数年时间,去追踪他们的战时轨迹。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时间相去不太远,有些证人还活着,官方或私人所存的文字资料甚丰,经过仔细研究之后,他发现了另一个事实,萨特和波伏娃的所谓抗战分子角色,是他们处心积虑,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蓄意欺骗,且一骗到底。由于考虑到要绝对忠于事实,约瑟夫所根据的证人,文件等,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在众多的资料中经过仔细核对后,才写下了一部《如此温馨的沦陷期》(Une si douce Occupation),副题是《西蒙·波伏娃和萨特的1940-1944》。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德军入侵法国。主战派没有一个具实力、有威望的人出来支撑局面,而贝当元帅却在电台上向德方呼吁结束敌对状态。那些将领们,带着三数百兵,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大家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只是敌对状态,还号召结束,何必作无谓牺牲?萨特应召入伍后,编到弗朗索将军的部队里,只有两百人,装备不齐全,衣冠不整,武器落后,有的枪支是一八七四年制造的,十足漫画式的队伍。上头意向不明,到处是德国人,这队人马干脆躲到帕杜(Padoux)的森林里行军。不知怎的,萨特和另外两个队友老掉队。后来萨特走不动了,一瘸一拐的,一旦听见枪声或爆炸声,就跳起来加快脚步,三个塞满手稿的布挎包就在他腰间晃来晃去。他总有本事找到躲藏的地方,总是离前线最远。看见人家流鼻血就要作呕,对谁也不肯帮一把,对谁也一毛不拔。而在他的作品中,却提倡所有人对所有人负责,要互相帮助。后来他干脆把枪扔掉,逃进一间女子学校的地窖,里面已经塞满了人。六月二十一日,德军进入帕杜,这支部队成了德军的俘虏。藏在地窖里的萨特,跟其他人一起举起双手从地窖出来。那天刚好是他的三十五岁生日。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萨特先后发表了《恶心》、《墙》等作品,薄有名声只是两年以来的事。德军知道他们抓住了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也懂得以学识来标志自己的优越性,作为俘虏,待遇就比别人好,总是一路顺风。他把这一切记下来,说不定传奇就从这里开始呢!反抗情绪是没有的,反驳或指责更加没有。于他而言,他的三个布挎包要比法国的命运还重要。里面就装着他的《理性年代》和《自由之路》的第一部分,还有笔记簿,每天给这场仗记下些什么。在Haxo兵营的时候,他将自己孤立起来,找到自己的空间,每天疯狂地写作。从他给波伏娃的信中得知,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命运,还企图作出让步来使他的作品出版。一九四○年十月转到Trèves战俘营,更加被作为特殊人物优待,吃得饱,活得自在,还在五十五号的特别木棚里组织了“艺术家之屋”,负责集中营的文娱活动,可以得到纸和墨水的供应,以及微薄的薪金。他深知自己的分量,总设法显摆自己,标示出智力高人一等,不跟任何人表示亲切,要人家称他为“先生”。他可以跟波伏娃书信来往,她通过特别渠道付钱为他治病。他也找到了食物供应的特殊途径。“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世界不就绕着两片屁股转么?这就是一切。”他说。
有一天,集中营的副官Arndt来找他,他刚好不在,副官向周围的人打探:“他可就是一九三三年到过柏林的那个萨特?”事实的确如此,那时候他是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的寄宿生,专门研究海德格尔,就在那时候参加了“国家-社会党”(National-Socialiste)。有了这番经历,德国人对他越发另眼相看,不但准许他在集中营写作,还请他编写一个剧目,准备在圣诞节演出。他取材于圣经时代,写了剧本Bariona,该剧目对犹太人绝不温情,这无疑是向德国人表示了立场。至于具体内容,德国人要过问,要检查。每次为剧本的增删去见长官的时候,会一反平日作风,将自己修整得整齐清洁。
作为被特别优待的人,他拥有一间条件尚可的独立睡房,不用参加苦役。一来二去,他变得越来越机巧伶俐了,“抵抗”这个字眼从来不会从他嘴里出来。在集中营过了七个月,当一位跟他熟稔的囚犯设法逃跑时,他被安排去接受医生检查,然后去见集中营的头目。原来德方有意释放他,说让他回国“就医”。而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他写Bariona的报酬,一种交换,是向德国人屈服的回报。返回巴黎与波伏娃相聚后,大家取得一致口供:绝非德国人释放,而是越狱逃跑的,抗战英雄的招牌,不就打起来了?!
他跟日思夜想的波伏娃团聚后,过的却不是二人世界的日子。波伏娃一出道就依赖他的名声,以便打开出书的渠道,现在谁也离不开谁了。但他俩的情人关系,根据警察局的档案资料,大概持续了五六年,波伏娃自认是两三年,然后各人“自由活动”。自由的结果是:各人打自己学生的主意,成了不折不扣的道德败坏者。波伏娃是在沦陷期的巴黎开始第一份中学教职的。她是个双性恋者,将女学生带上床,如果萨特感兴趣,绝对给他方便。各人占有的人,都属对方所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家庭”,还有“家庭”以外的成员。“家庭”中可以说得出名字的就有:萨特的学生J.-L. Bost, 波伏娃的学生、俄国女子Olga K.,她的妹妹 Wanda K.,犹太女孩Bianca B.,出生于土耳其的俄裔女孩索罗基娜(N.Sorokine)。萨特要年轻的女孩,波伏娃要年轻的男孩,或女孩。各人租下最平价的酒店,重要的是安排好活动时间,不要同时碰上。尽管在战争时期,他们却风流靡烂得全无愧色,真凤真鸾,假凤虚鸾,总之是胡天胡地,昏天黑地。不是“歌啭玉春堂,舞摇金步莲”,却教人感到“恶心”!那个牛高马大的索罗基娜,可以给小个子萨特吃拳头或耳刮子,跟波伏娃也一样。胡天胡地中离不开争吵、打闹。他们做自己的丑事比关心国家命运更热心。外间风声越紧,他们越是退向自己的共同世界。
索罗基娜是索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已经跟男朋友Dupas同居,后来跟波伏娃搞上了。Dupas 向女孩子的母亲投诉,请她干预女儿的事,但一再劝阻无效,做母亲的决定对波伏娃起诉,理由是:“挑唆幼女堕落”。是年索罗基娜二十岁。波伏娃在她的《战争日记》中写道:“提起我,她的母亲就在她跟前歇斯底里地吵闹,将她赶出门,禁止她再来看我。”与此同时,另一位犹太女孩Bianca的母亲,也恼恨波伏娃跟她女儿的畸恋。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大学区校长向波伏娃任职的Camille Sée中学女校长Evrard提交了一封信:“我收到一封向法国国家检察官投诉哲学教师波伏娃小姐的信,指她唆使幼女淫乱堕落,我请你尽可能慎重地调查……”但经过多方面调查皆不得要领,都说她的课讲得不错,上完课就走,不参与学生的生活。但终于也有证人说,她经常在蒙巴纳斯的咖啡座,与一群少男或少女一起喝咖啡。Evrard直接找波伏娃谈话,她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却无意间泄漏出她与索罗基娜的关系。她说这个女孩子由于父母离异,父亲拒绝负责她的生活费用,母亲另有情人,她趁机给她提供日常生活。巴黎的检察官跟巴黎大学区同时着手调查这件事,录下了波伏娃的详细口供,她说索罗基娜也像其他同龄的女孩子那样挑逗她,但“我从来没有回应她的要求,相反,我将她引导到正常的性关系上……”后来萨特也被检察官调查,同样留下了详细口供,目前可以随时接受查询。坊间流传的萨特和波伏娃的令人恶心的丑闻,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可查,有官方文件提供证据。
标志他们抗战时期悠闲的巴黎生活的,还有没完没了的“花神”咖啡座上的露面。自从一九三八年萨特发表了《恶心》,刚踩进伽利玛的门槛,就拼命往大作家的队伍里钻。而“花神”咖啡座是知识界精英喜欢的聚会场所。在这个作家、艺术家、电影制片家、演员的经常性聚会场所,大家成了熟人,形成一种特殊气氛,见面时大家点头、握手,谈文学、艺术、生活,互相间就有了认同,产生优越感和满足感。如果座上认得你的人越多,就越有名气。萨特和波伏娃去到这种地方,马上觉得自在不过。跑到偏远的乡间去,将自己关起来写作?简直是个大傻瓜,有谁能第一眼就认出你?这里就不一样。他们放弃了以前经常光顾的咖啡座,改为在这里轮着约会他们的“家庭”成员。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巴黎大举逮捕抗战者和犹太人,这种地方消息最灵通,萨特和波伏娃不会不知道,但他们却漠不关心。当他们不在学校执教时,在咖啡座上写作的时间是,早上九时至十三时,再从十六时至二十时。“花神”成为他们半个住家。

尽管他们一再标榜自己的抗战身份,但萨特从集中营回来后几天,就跟Comoedia的主编R. Delange扯上了关系,准备在上头发表作品。这是投降派和德国纳粹合办的戏剧周刊。而他的《恶心》,也在沦陷期重版了。“人总是有时自由,有时被奴役的嘛!”他说。波伏娃则公开宣称:“没有任何东西使你想到德国人会失败。希特勒还没有遭受过任何挫折,伦敦被炸得一塌糊涂,纳粹军队可能很快登陆英国,美国袖手,苏联消极观望。”她所总结出的形势又怎会使他们积极抗战?听《新法兰西评论》的主编Paulhan老谈抵抗运动,萨特忽然觉得,抗德分子的招牌既然打出,就有必要意思意思,何不搞一个所谓抗战组织?他先给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与自由”。至于成员,现成不过,他们的“家庭”不也统共有五个人么?萨特是当然的领导,但这个领导没有什么工作好做,也没有什么指令好发。据波伏娃的说法,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情报,然后再发出去。但收集情报要钻进敌人内部,至少要靠近其周围,但他们有胆量走近敌人一步么?平日只是“一家子”讨论,“一家子”决定,有什么情报可发?发给谁?萨特后来还说,他曾经起草过一部宪法,准备将来把国家制度改革一下。草稿写了好几份,“我将它发给我周围的人,但可能是我丢失了,或者是我给的人丢失了。”这些草稿全都下落不明,更奇怪的是,也没有在任何人的记忆中留下印象。
但“社会主义与自由”这个队伍是要壮大的,希望在学校里发展成员。可恶的是,接触了几个人,都表示审慎,不肯跟他去抗战。而大假时间又到了。抗战不忘度假,他们决定骑自行车由北到南,直落地中海。重要的是选择非德军占领区,这样既安全,食物供应也不短缺。绕来绕去的千把公里的“长征”中,难免要过草地,看雪山。没有大渡桥横,不用攀什么铁索,但潺潺溪涧或小河倒在所难免。度假又不忘抗战,沿途不也可以招兵买马么?最初找到的两个人,一个是Kaan,真正的抗德战士,另一个是马赛人D.Mayer,社会主义者,但可恶的是两人都对他没有信心。不如到蓝色海岸去,找找纪德和马尔罗,他们是《新法兰西评论》的两大支柱。当时只薄有名气的他,多么渴望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一旦将他们罗致旗下,何止平起平坐?干脆就变成他手下的人!跟纪德谈了什么,双方都没有留下文字。但纪德后来对一位夫人Maria V.R.说:“萨特挺逗趣的呢,是一个有主意的旅行推销员,十分具颠覆性,且十分危险。”次日上门去找马尔罗,后者说,眼下任何行动都不会奏效,“就靠苏联的坦克和美国的飞机来赢得这场仗”。回程的时候经过Grenoble,上门找一位女共产党员柯列特,也没有下文。逍遥千里长征返回巴黎后,萨特心里不是味道。垃圾,垃圾,所有人都是垃圾!都不肯让他领导去搞社会主义!这个抗战分子他也不想做了!将“社会主义与自由”解散算了!可叹的是,连解散问题都不存在,因为这个组织根本是子虚乌有,只存在于他俩的想象中和口头中。其实,抗敌不一定要什么组织,只要方便一下参与抗战运动的人,帮一把受迫害者,就是参与了运动。但他们没有这种勇气,也没有这份心思,暗中助人一把,有谁知道?他们是别样心思别样情,重要的是利用这场仗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实现自己的宏图大计。
巴黎一恢复自由,他的收获季节就到了。德军走后才四天,萨特已经有本事使法国的自由电台接受他的广播剧《墙》。逃到巴黎北郊的小旅舍之前,他已经在一位演员的帮助下做好了录音。又抓紧时机钻营,得以在《自由法国》杂志上发表了《沦陷期的巴黎》。这本杂志是由他的死对头、与他针锋相对的哲学家阿隆(R. Aron)主持的,战时在伦敦出版,是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抗战刊物。反手间,又把他的《自由之路》第一、二卷交给了伽利玛。其实在战争末期,他的《理性年代》第一卷,《缓期》第二卷、《存在与虚无》和《苍蝇》都已经出版了。巴黎重获自由才三个星期,他的《关起门来》(Huis clos)就在VieuxColombier重新上演。可见萨特前面打的是抗战招牌,后面是私家园地的经营,是个人收获的果实累累,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已经捞了个满盘满钵。果然,战前他在文化界中小有名气,战后一摇身,已成为法国大名鼎鼎的作家,这与他的刻意而机巧的运作分不开。假冒的抗战分子不但蒙混过了关,还像真英雄般引人注目。于是,什么国家戏剧委员会委员、全国作家联合会委员、出版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一大堆头衔,都一股脑儿掉到他头上,还负责了一些司法附属机关的清理职业队伍的工作。他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一下子登上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界的舞台,还坐上了左派文人圈子的第一把交椅,成了个大堆头,日后的称王称霸就从这里开始。他所巧取豪夺得来的胜利大饼之大,使他战时所投靠的人,比如伽利玛出版社负责人Gaston、与德国纳粹合办戏剧周报的主编Delange等,现在都反过来要他这个“抵抗战士”来为他们说情,为他们澄清或开脱罪名。波伏娃的小说《他人之血》也出版了。在这部著作中,她非常精灵地肯定了他们的抵抗分子地位。萨特更一不做二不休,终生孜孜不倦,以机巧的宣传手腕,不放过任何机会以斗士自居。直至一九六二年,为了加入一个学会而填写自传表格时,他在“战争”这个栏目上写道:“积极参与抵抗运动,以及巴黎的街垒之战。”天哪,他是否知道,巴黎的确筑了不少街垒,但根本没有发生过街垒之战?
作为法国著名的左派知识人,萨特的一大本事是能说会道,善于宣传,将平凡的事物理论化、神秘化。作风上的粗鄙、挑衅,丑陋的外形所流露出的戏剧性和邪气,都引人注目,加上以捏造和想象树立起来的斗士形象,到头来果然欺骗了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有人就说出这样的话:“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
《如此温馨的沦陷期》的作者约瑟夫,本身是小说家,也是历史学家。经过多年的事实追踪,多方面的资料研究,还恐怕有所闪失,专程去拜访专门研究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诺格尔(Henri Noguères)。他的有关抵抗运动的著作,是无可争议的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资料。他问诺格尔:
—为什么不将萨特的名字写进你的作品里?
—因为萨特从来不是一个抗战分子。
—好好找一下,可能会找到哪怕小小的事实,他参与过的哪怕一丁点的小事?
—没有!
约瑟夫坚持说:
—还是找找看吧!
两个星期后,诺格尔写信给他说:“我维持原来的说法,我用了二十年时间来研究和编写法国的抵抗运动历史,我从来不曾碰上过萨特与波伏娃。”
诺格尔是对的。如果说胜利初期局面混乱,萨特浑水摸鱼,白白得了不少头衔,然则,经过一段时间梳理后,当国家给所有参加过抗战的人颁发勋章时,萨特没有入选,他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萨特从集中营回来得不光彩,但如果他从此闭门写作,去写他的什么《苍蝇》,什么《虚无》,谁也不能指责他。那个非常时期,做尽令人作呕的丑事后,还欺天地,欺人神,贪天下之功为己功,为自己戴上抗战分子的桂冠,大吹大擂,将名声吹大来谋私,来登上他的舞台。孜孜不倦的数十年行骗和假公济私,怎能不使人恶心!但历史从来就是这样:骗得了现在,骗不了未来;骗得了一代人,骗不了两代;骗得了一个人,骗不了众人;或者,骗得了众人,骗不了一个人,历史事实最后总会各归各位,恢复真相。“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世界不就绕着两片屁股转么?”不错,数十年的史实,任你怎样蒙混、欺骗,不就像贴在后面的两片屁股那么近便,那么一目了然么?是非黑白能够弄错到哪里去?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周兵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本书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当代西方史学的主流趋势—新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不同的方面总体分析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讨论“文化转向”在历史学中产生的深刻影响和重要变化;下编则将研究视线聚焦到彼得·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等五位颇具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身上,作为个案,通过讨论他们具体的理论与研究实践进一步说明新文化史的特点。全书语言流畅,基础扎实,是一本具有前沿性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