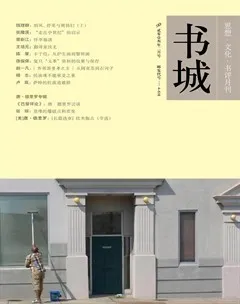民族魂不能承受之重
一、闻一多走极端
“湖畔诗人”之一的汪静之,风流才子,嗜写情诗,有诗云:“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五四”时颇出风头。到了九十多岁,还出了一本“抽屉诗集”《六美缘》,谈遇过的六个女人……
但闻一多鄙夷他,给其弟写信讲:“现在春又来了,我的诗料又来了,我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这些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无病呻吟的情诗”,指的正是汪静之的情诗。
那时闻一多正留学美国,青春年少。俗云: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写诗?笔者未能免俗,青春期也写过诗,但如同汪静之,只懂“暮春三月,男女互奔不禁”,“价值甚高”的爱国诗,真没想过,所以读闻氏此信,惭愧!
后来发现:闻一多虽以爱国诗著名,也写情诗的,只不过那些诗太铿锵,不自然,所以没人读。对闻一多来讲,作诗近乎公事,写信才是私情。比如,他信里骂妻子:“你死啦!不给我回信!”梁实秋调侃他有艳遇么?他泪奔:“到美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很本真呀,但“一诗脸就变”,慷慨激昂的爱国腔。
闻一多是清华学生。清华是留洋预备班,但他自称为坚守中国文化的“东方老憨”: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爱国谁反对?但写诗毕竟不是打仗,不就写首诗么,这么声色俱厉,太夸张了。他的爱国激情实在太突出,以致朱自清称他“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闻一多为何如此极端?后来才明白他是受了晚清国粹派的影响。那时一批知识分子担心国家将亡,大力宣传“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文化救国”。这一招叫“文化民族主义”,倒不是国粹派自己想出来的,学自日本,日本则抄自欧洲。闻一多青年时,“文化救国”风靡一时,“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全盘接受了。一九二五年三月,他给梁实秋写信,说自己正倡导“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他的“爱国诗”高于“爱情诗”云云,正来自这个“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闻一多还加入过一个“国家主义”政治团体大江会,是一员干将。这个大江会,是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当时德国纳粹是在野党,獠牙未露,世界各国粉丝不少)。
闻一多与“国家主义”的关联,此处当一标本,意在说明民族国家与世界诗歌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诗人”背后的“政治”,乃是二百多年世界诗歌的基础,不弄懂它,近代世界诗歌史便一笔糊涂账。
二、国家搭台·诗人唱戏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三日,法国大革命爆发。起义者势如破竹,次日便攻占了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狱,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传遍欧洲。人间天堂的大门,仿佛敞开了。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晚年回忆:“幸福呵,活在那个黎明,年轻人如进天堂!”
但事与愿违。
很快,浪漫的法兰西变成了嗜血的巨无霸: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塞纳河中,浮尸滔滔。直到五年后,断头无数的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断头台,才告一段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吓坏了整个欧洲。那是二百年前的“欧洲之春”,其残酷,其血腥,其混乱,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就相形见拙了。
这“欧洲之春”的一个结果,是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啥是“民族国家”?简单说,就是“民族”与“国家”的合一。“民族”这词,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少数民族”的“民族”(ethnic group),一层意思是“中华民族”的“民族”(nation,有人译为“国族”),此处指后者。
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没啥民族国家,只有“王朝国家”,是“王朝”与“国家”的合一。国王不是“民族”的“公仆”,而是“民族”的“主子”。你要读《战争与和平》就会发现:俄国宫廷,一人一口“阳春白雪”的法语,“下里巴人”的俄语,贵族是不屑说的,而许多俄国官员,居然是普鲁士人。同时代的普鲁士军队,八分之一是外国人。为何?因为那时的俄罗斯与普鲁士为国王私有,国王爱雇谁就雇谁,外国人孤立无援,只能靠国王,干活更卖命。元朝爱用外国人(包括马可·波罗)当中国官,也是这道理。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举国抛弃旧君主,迎来新君主。这个新君主,赫然是荷兰国王。一百年后,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则是德国人。更绝的,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他借政治婚姻,继承了大片领土,但管辖的诸民族都不吱声。为何?因为当时的国家,没民族啥事,只要国王摆平其他国王就成。这种事,现在能发生?绝无可能。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除了“民主、自由、博爱”,法国大革命还催生了一个“主权在民”信念,认定国家是“全国人之公产”,推出了民族自决原则。“民族=国家”传遍欧洲,成了各国都遵守的“国际规则”。由此,原先的封建君主,或被推翻,如法国的路易十六,或渐变为“民族的代表”,如俄国沙皇。这种政治“游戏规则”的变换,如同秦始皇废除封建、中央集权,超级政治风暴来的,所以一七八九年以后,旧欧洲也就荡然无存了。
民族国家,不是谁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势利使人争”,争出来的。放眼望去,整个地球如同一个大市场,充满了资源,如何获取?如何开发?如何分配?各个政治集团就得竞争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从村落升级到部落,升级到酋邦,升级到王朝国家,最后争出了民族国家。
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如不同类型的“公司”。因为国民参与程度高,后者人心齐,市场宽,物力、人力与思想流动畅通,前者哪能比?王朝国家PK民族国家,如同螳臂挡车,灭亡势所必然。所以,英法等早期民族国家,横扫欧洲封建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西班牙等,所向披靡,并向全世界扩张。泰山压顶,其他国家走投无路,要么自取灭亡,要么向敌人学习,“变法图强”,转变为民族国家。你不见,《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已在路上?
民族国家纷纷蜂起,乃二百多年来人类政治演化的大奇观。
或许你会问:这一切,跟诗人有何关系?
答曰:有关系,而且是大关系!谁都知道,人力是国力之本,但关键在怎么管理。“粗放式管理”的国家,竞争力弱;“精密式管理”的国家,竞争力强。任何变法图强,都意在变“粗放式管理”为“精密式管理”。商鞅变法,人力、物力统统用于耕战,不许浪费,这是古代的的“精密式管理”。民族国家,发展商业,开设工厂,训练部队,加强教育,这是现代“精密式管理”。这个“精密式管理”,教育系统极其重要。没军校,士兵哪来?没商校,会计哪来?没技校,工人哪来?没医校,医生哪来?……这些只是制造“技术人员”,还需要重要的一环—制造“国家信仰”:培养爱国思想,培养民族认同,凝聚人心,使“国家”成为仅次于甚至超越上帝的“神”。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的民族国家,先有民族,后有国家;有的民族国家,则先有国家,再有民族。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安德森,生于中国,后来去了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走的国家多了,他惊讶地发现:有些东南亚国家,原先不是一个国家,是被欧洲殖民者硬拽到一起的,但殖民者被赶走后,那些“殖民机构”不但没散伙,反倒自认为从古到今就是一个国家,编出一部部有声有色、热情洋溢的“国家史”来。
于是,安德森恍然大悟:“想象”乃是建设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甲乙丙丁,素未谋面,八竿子也打不着,为何认为彼此属于同一群体?想象黏合他们之故也。民族国家想象,谁创造?谁编撰?谁维护?这事儿,跟诗人就拉上了关系。培育国家信仰,靠干巴巴的口号,那不成,得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激动人心、情感感天动地,“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就需要文学想象了。由此,创造民族文学,便成了民族国家兴起时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有条件要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
于是,一种新型的诗人—“民族诗人”(最大牌的,叫“民族魂”)—就在人类史里粉墨登场了……
三、“疯拜伦”风生水起·“小拜伦”水涨船高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出殡之日,有人为他披一面锦旗,大书“民族魂”三字。这人真懂鲁迅:当民族魂,确是鲁迅的一生志向。
鲁迅大闻一多十八岁,也受国粹派的影响(老师章太炎便是国粹派大将),只不过“文化救国”的主张,他缩小成“文学救国”。一九○七年,鲁迅写了一篇《摩罗诗力说》,那时他还没热心白话文,模仿章太炎用古语写文章,咋难懂咋来,所以要读懂它,得费老鼻子力气。不过,《摩罗诗力说》的主旨倒不难懂,那就是歌颂民族魂,认为一个国家没了民族魂,如同没了心灵,毫无希望。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创造了民族魂;鲁迅则颠倒过来,认为民族魂是“因”,民族国家是“果”,大声歌颂一批叫“摩罗诗派”的民族魂。“摩罗”意为“恶魔”,这派恶魔诗人,就是现在说的“浪漫主义”。欧洲民族国家崛起前后,浪漫主义声势最浩大,从法国卢梭开始,一路汹涌澎湃,摧枯拉朽,前后达一个多世纪。除了卢梭,德国的歌德与席勒,英国的雪莱与拜伦,俄国的普希金,法国的雨果,美国的爱默生与惠特曼,都是风云人物。
浪漫主义之所以声势显赫,至今不坠,一大原因是跟民族国家联系紧密。浪漫主义有一个浪漫想法,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影响所及,民族国家都煞有介事,造出了“法兰西精神”、“西班牙魂”、“大和魂”、“俄罗斯理念”、“德意志精神”……好似人类不是同一物种,彼此倒如同狗儿、马儿与驴儿。由此,浪漫主义被认为是民族国家诞生的“因”,而不是“果”。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这么看。罗素是西方大哲,但这话“倒果为因”,我不以为然,是民族国家捧红了“浪漫主义”,而非“浪漫主义”催生了民族国家!罗素也好,鲁迅也好,脑子里还是十九世纪的“英雄史观”。直到二十世纪,这类思想才被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平民史观”打了个落花流水。
我的理解,浪漫主义之于民族国家,是它流行之时,正赶上民族国家崛起,需要虎皮,于是被拿去“乔装打扮”了。时代这东西,向来蛮不讲理,乱点鸳鸯谱,“说你行,不行也行”,如果它赶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死对头),也照用不误。政治与经济,大道理也。文化,小道理也。大道理管不住小道理,有这种道理么?
鲁迅最仰慕的民族魂,不是别人,正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摩罗诗力说》赞美拜伦“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列为“摩罗诗派”之首。鲁迅这话,不完全符合史实。拜伦实为浪漫主义的小字辈,在英国浪漫主义里也只是第二波(第一波是华兹华斯、科勒律治)。他之著名,是因为风头太盛,被历史“乱点鸳鸯谱”,成了民族魂的“第一版”。
一般来讲,民族魂多是爱国的浪漫主义者。拜伦是浪漫主义者,却不爱国。实际上,他讨厌大英帝国讨厌得要死,崇拜的是敌国的拿破仑。拿破仑横扫欧洲之时,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平了英国,诗人前辈华兹华斯闻此,忧心如焚,拜伦却漠不关心,后来听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却说:“我真难过死了!”
所以别奇怪,当日拜伦在英国,受尽白眼,再加上行为不检,风传乱伦,声名狼藉。他的诗,恶评如潮,就算在现在的英国,不以为然的人还很多。就诗论诗,他的诗浅显直露,单调浮夸,确实不怎么好,有人甚至讥之为“中学生作文”。英国大批评家约翰逊就注意到:拜伦论英国诗,不提莎士比亚,反倒对不咋样的普伯赞不绝口。为何?约翰逊讲:因为他自知斗不过莎士比亚,所以不提,普伯他可以战而胜之,于是大声歌颂之。
这是在英国,在欧洲就截然相反了。拜伦的声名如日中天,如雷贯耳,粉丝铺天盖地,压倒了所有的浪漫主义者。
诗人如莎士比亚、杜甫,是“人以诗传”,拜伦则不同,是“诗以人传”,他的名声之所以登“疯”造极,是因为驰援争取独立的希腊。希腊是欧洲文化两大源头之一,欧洲知识分子的“圣地”,当时被土耳其占领。驰援希腊,是小文青梦寐以求的伟业,一如基督徒想拯救耶路撒冷。拜伦驰援希腊,功未成而身死,噩耗传来,欧洲大震,识与不识,尽为之哀。小时读李白诗《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虽不好武,也热血沸腾不已。欧洲小文青之仰慕拜伦,你也就推想可知了。
那时拜伦就是诗歌,诗歌就是拜伦!就连浪漫主义老前辈如歌德,也五体投地,专门在《浮士德》里歌颂拜伦,说他是希腊文化之子,并安慰世人不要太悲伤:大地必将再造这样的英雄,绵绵不绝……歌德七十多岁了,出名的自私自利,但他哀悼拜伦,出诸至诚,可见拜伦之得人心。歌德大师尚且如此,同代小年轻如普希金,隔代小年轻如鲁迅,就更不用说了。
拜伦,欧洲的超级“韩寒”!多少年轻才俊仰慕之余,舞文弄墨,也就模仿或者抄袭之,所以拜伦一死,“小拜伦”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这些“盗版诗人”,搁在今日,再风光也就是一海子,但他们的时代,正值民族国家崛起,民族魂缺货,也就水涨船高,一个个都山寨成了该国的民族魂了!
例5b3160fa72bc53abe23ecb096da7f886如,“匈牙利的拜伦”是谁?裴多菲,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我们这儿太有名了。“波兰的拜伦”是谁?密茨凯维支。此人在中国名气不扬,但他的至交“俄罗斯的拜伦”,就没人不知道了,那就是普希金!你听听果戈理怎么赞美他:“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
普希金活着时,已是俄国文青的偶像,也是沙皇政府严密监视的危险分子(沙皇还觊觎他老婆,但未能得手),负责监视他的上级伏隆卓夫,接二连三地给沙皇送监视报告,里面对普希金嗤之以鼻,说他“不过是拜伦的一个浅薄的模仿者”。
果戈理的话对,还是伏隆卓夫的话对?
照我看,都对。普希金确实是俄罗斯的民族魂,也确实是拜伦的山寨版。他的史诗《奥涅金》,毫无疑问地模仿拜伦的史诗《唐璜》。他能胜过老师拜伦么?难,最多打个平手。然而,拜伦在英国诗坛里都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这“三座大山”的对手,更遑论跟欧洲诗坛的荷马、但丁、歌德抗衡了。所以他的弟子普希金再牛,也只限于俄罗斯。但是,普希金不够牛,俄罗斯民族可是牛气冲天的。今日世界,敢顶牛美国的,不正是俄罗斯这头北极熊么?一百七十八年前,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预言百年后,两个庞然大物将平分世界,一是美国,一是俄国。庞然大物的民族魂,能不牛么?所以普希金殁后不到五十年,水涨船高,已成了一尊“俄罗斯神”,小说家屠格涅夫誉之为“伟大导师”。
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民族国家,才是制造民族魂的操盘手。民族魂纷纷问世,实为民族国家“造神运动”的结果。之所以造神,意在铸造民族国家的“新人”。民族国家不但需要新制度、新科技,而且需要“新文化”、“新人”(国民)。明治维新硬把只认府君的“封建臣民”改造成独尊天皇的“现代国民”,便是著名的例子。
正是“造神运动”与“造人运动”交相辉映,交相促进,才创造了二百多年来世界文坛波澜壮阔的大篇章。
四、从“帝王师”到“民族魂”
一位以叛逆著称的新诗人,晚年回归传统,引“我辈岂是蓬蒿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赞美李白,说他有“独立人格”,实为中国诗人的范儿……
李白喜欢,这话却不能苟同。他引的诗,“我辈岂是蓬蒿人”在前,当时李白闲居在家,一日山中归来,听说唐玄宗召他去长安,大喜,“呼童烹鸡酌白酒”,全家喜气洋洋,李白则“起舞落日争光辉”,乐到离家入京时,还志得意满地大嚷: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用《儒林外史》翻译,意为:“我是范进,我中举了!”这是哪门子“独立人格”? 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源自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讲李白到长安后的事儿。据说一次他喝多了,醉眼蒙胧,唐玄宗派人来叫,他不理不睬!杜甫写进诗里,津津乐道。这故事像段子,就算是真的,也如同跟主人撒娇,谈不上什么“独立人格”。
唐代,男人都想当“高级公务员”(高级是“官”,低级是“吏”,更低级是“胥”)。入仕,正途是考进士。李白想考,《李太白集》里就有诗赋考试的习作。但可能因他是胡人或别的缘故,按规定不能考,放弃了。当吏是偏途,得慢慢升迁。据说李白也试过,也放弃了,最后选择了“帝王师”这条路。这路更不好走,人满坑满谷,李白被召,是走了关系的结果。所以,李白是大诗人不假,但硬要说他有“独立人格”,那就是“屎着佛头”了。他无职无权,又想他功名利禄,又想他“独立人格”,这太难为李白。
一次,读黑格尔《历史哲学》,讲中国:人人在政府面前平等,有才者都能被政府征用。以为赞扬我们,眉开眼笑,往下一看,说中国官僚专制,没有独立人格,又说中国人狡猾、虚伪、互相欺骗……这就种族歧视了,难道希特勒之前的德国人不欺骗,都人格独立?黑格尔自己,晚年成了普鲁士的御用哲学家,把专制的普鲁士吹得天花乱坠,有啥资格蔑视咱们?实际上,民族国家兴起前,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最高级的御用文人都是“帝王师”,实为豪门清客。
帝王师,帝王之师;民族魂,民族之魂,差别一目了然。为何俄国选普希金当民族魂,不选之前的诗人?为何日本选夏目漱石,不选写《源氏物语》的紫式部?为何我们选鲁迅,不选李白?道理清清楚楚:因为“走进新时代”了,民族魂太远,跟民族国家就扯不上关系了。因此,各国的民族魂,选择面很小:古代的,不成;太差的,不成;太晚的,等不及。算来算去,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个。像俄国,民族魂只能在普希金、莱蒙托夫里选,不选普希金,估计就是莱蒙托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居上,但毕竟生得晚,赶不上趟了。有点儿中头彩的味道,但别笑,历史有严肃的一面,也有幽默的一面,一中彩成千古风流人物,不奇怪。
或许你会问:普希金,既然被沙皇视为危险分子,为何还树他当民族魂?这不自相矛盾吗?
答曰:不矛盾。历史是各派拉拉扯扯的结果,不是谁自个儿说了算。就是庞然大物如沙皇,也只是众多政治集团里的一个而已。《道德经》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由此推论,“圣人”再威风,也如同“百姓”,只是“天地”的“刍狗”罢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圣人、大哲、英雄、君子、平民、小人、恶棍,都在网中无处逃遁,不由自主。
普希金有一首名诗《寄西伯利亚》:
爱情和友谊将会穿过幽暗的铁门,向你们传送,一如我的自由的高歌传到了你们苦役的洞中。沉重的枷锁将被打掉,牢狱会崩塌—而在门口,自由将欢欣地把你们拥抱,弟兄们把利剑交到你们手。
(查良铮译)
这诗,献给他的朋友们—流放西伯利亚的俄国十二月党人。
拿破仑战争时,俄军大败法军,杀进欧洲,一批军官诧然发现:欧洲国家比自己民主繁荣多了,自己国家原来是独裁专制的野蛮帝国,为欧洲所不齿。这批军官幡然醒悟,回国后掀起民主运动,于一八二五年发起兵变,是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事虽不成,却开了俄国革命之先声,从此俄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激进青年铤而走险,暗杀权贵成为一时潮流。一八八一年,他们在数次失败后,暗杀得手,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事轰动全球,舆论一面倒地同情暗杀者,连晚清小说《孽海花》,也长篇累牍歌颂刺杀沙皇的女党人,心折于他们争取民主的义烈。
普希金未参与“十二月党人起义”,但彼此精神是共鸣的,后世视之为俄国民主运动代言人。阻挠普希金当民族魂,沙皇未必不想,但他也只是“天地”的一只“刍狗”罢了,虽然手下貔貅百万,铁甲千里,不也战战兢兢,身死名裂,为天下笑?大批激进知识分子要视普希金为民族魂,沙皇无可奈何,也只能默认。
一八三五年,托克维尔这样写道:
我们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前进。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民主,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这个“天地”或曰“不可抗拒的运动”是啥,如此强大?
托克维尔去世那年,达尔文一语道破之—“生存竞争”。答案很简单:民主政治最能凝聚人心,焕发整个国民的潜能,它不但不是国家无用的装饰,反倒是国际竞争的利器。实际上,正因为生存竞争激烈,才逼迫各个民族国家不断民主化,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认同民主,这是民族魂不同于帝王师的大关键。
五、雪莱是叛国贼么?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闻一多在美国得知后,激动地连声说:“这个人如何可以死!这个人如何可以死!”赶写了一首一百五十多行的长诗《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悼念之,将孙中山称为“救星”、“圣人”、“耶稣”。中国人则是要向孙中山忏悔的“不肖的儿女”、“背恩的奴隶”、“龌龊的虮虱”、“饕餮的鸱枭”,“罪孽深重,万死不容”:
我们虽是不肖的儿女,背恩的奴隶—
我们自身鄙吝反而猜疑你的恩惠,自身愚蠢因之妒嫉你的聪明;但是神明宽厚的主将啊!请你宽赦我们,请你饶恕我们,让我们流出忏悔的血泪洗你心上的伤痕……
这是悼念缔造民国的孙中山,还是悼念《一九八四》的老大哥?
从晚清起,求民主便是中国浩浩荡荡的潮流,立宪派与革命党彼此攻讦,却都主张开议院、申民权。大闻一多八十岁的湖南老乡郭嵩焘,五十八岁,不会外语,但一到法国,马上知道“巴力门”(parliament,议院)重要。大闻一多五十多岁的黄遵宪,一九○五年去世时,遗言为“太平世必在民主国”。孙中山的一大功绩,正是创立民国。闻一多的好友如吴景超、潘光旦等,熟悉民主制度,后来是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干将。闻一多跟他们朝夕相处,又受了九年欧美教育,留洋三年,居然不懂“以民为主”与“为民做主”的区别,满脑子中国“圣人”与欧洲“耶稣”,这就让人纳闷了。二十七岁的闻一多,虽然知道国家主义,但关于民主政治,他还得补课。
闻一多这类想法,当时是有代表性的。学者李泽厚说现代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忙着拯救民族危亡,启蒙这一头没顾上。正确。然而“先救亡,后启蒙”,几乎是后起民族国家(包括德国、俄国、日本等)的必经之路,轮到我们时,已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了。世界各国搞民族国家,不是赶时髦,而是生存竞争逼出来的,所以先行的都是俾斯麦式的铁血政治,民主制度建设是后话。这种“先救亡,后启蒙”的“局”,当然会影响它们的民族诗人。
闻一多写诗,最早学英国浪漫主义。英国浪漫主义三巨头之一的雪莱,是他的一个偶像。这个雪莱,发表过《告爱尔兰人民书》,鼓动祖国殖民的爱尔兰人起来斗争,争取民族独立,“英奸”来的。他这么做,不是被爱尔兰人收买,而是到爱尔兰首府都柏林旅行,发现“都柏林的穷人确实是最不幸最悲惨的了。在他们那狭小的街上,仿佛有成千人在一起蜷伏着—简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愤激于自己祖国的残暴,遂挺身而出,作《爱尔兰人之歌》代之呼号:
英雄们何在?他们死得英豪,他们不是在荒原血泊中卧倒,就是任自己的阴魂凌驾着风暴—
“同胞们,复仇啊!”这样向我们呼号。
这就丝毫不管民族利益,完全诉诸人道主义了。
原来,民族国家理念暗含一个悖论:作为民族国家,它“民族至上”;但作为民主制度,它又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人类至上”,超越了民族。但“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不是啥时都一致的,发生冲突时,当局者必须抉择。当时的大英帝国,为了一己利益,到处殖民扩张,鞭笞天下,横行霸道。雪莱目睹的爱尔兰,其实还不是最惨的时候,三十三年后,爱尔兰大饥荒,近在一旁的英国坐视不管,任其饿死近百万人,那才真真惨无人道。在爱尔兰问题上,无需“救亡”的英国人雪莱,选择的不是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而是超越民族的人道主义:
我现在写的,不仅仅考虑着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而且考虑着全人类的解放问题;全人类的解放是全面的、无条件的,它将包括无论什么民族、国籍或信仰的每一个人,它将拥有所有能思想、能感受者……(《告爱尔兰人民书》)
雪莱诨号“疯子”,愤激起来,敢痛骂自家国王是“一个老而疯、昏庸、可鄙,快死的东西”,王侯是“庸碌一族的渣滓”!
他大声宣称:
但愿自由人能把这名字:“帝王”践踏为纤尘!不然,就写在土里,好使这污迹在这名誉之页上有如蛇蝎的足迹,将被风的呼吸所抹去,被平沙从后面覆盖!
不止雪莱如此,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几乎无不如此,拜伦怎么呼唤?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还在飘扬,像是猛烈的雷雨对风冲击!闻一多五体投地、视为“艺术底忠臣”的济慈,也这样大声疾呼:谁也达不到那个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为此日日夜夜不安的人们!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是敞开胸襟向全人类大声疾呼的,狂歌怒号,排山倒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那都太小了,容纳不住他们狂放不羁的灵魂。雪莱的《西风颂》,把人间的革命与宇宙的更新融为一体,他的呼喊是朝向整个宇宙的:
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
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音乐
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甜蜜。呵,但愿你给予我
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这样声调高亢的诗,他们的弟子—落后国家的民族魂,如普希金、裴多菲、闻一多等,很难写出来。他们的声音太弱,太苦了。诗人也是人,有限,你不能要求他们摆脱祖国的土壤。
于是,我们俯瞰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可以看见:有一股潮流曰“国族化”(即“民族国家化”),朝向民族利益;有一股潮流曰“民主化”,朝向人道主义与普世价值。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两股潮流各有强弱,但互相激荡,互相转化:没有民族国家的人道主义,空话,没有国家撑腰,谁保护你的民主权利?没有人道主义的民族国家,则奥斯维辛集中营与南京大屠杀是合理的,因为德国与日本如此残暴,正出诸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所以,雨果在长篇小说《九三年》里大声疾呼:“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民族魂,正置身于两股潮流之间。
幻影公众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 林牧茵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本书是李普曼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是《公众舆论》一书的姊妹篇。作者阐述了如下观点:建立在民众广泛参政基础上的传统民主只是一个神话,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圣的公众形象无异于幻影。公众无法真正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权,他们必须走下圣坛,去做他们该做的事。自一九二五年出版后,本书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持续不衰。评论认为:“《幻影公众》与《公众舆论》一样,将成为美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现代经典著作。单凭从其与众不同的文字角度看,它也值得被一遍遍阅读。”